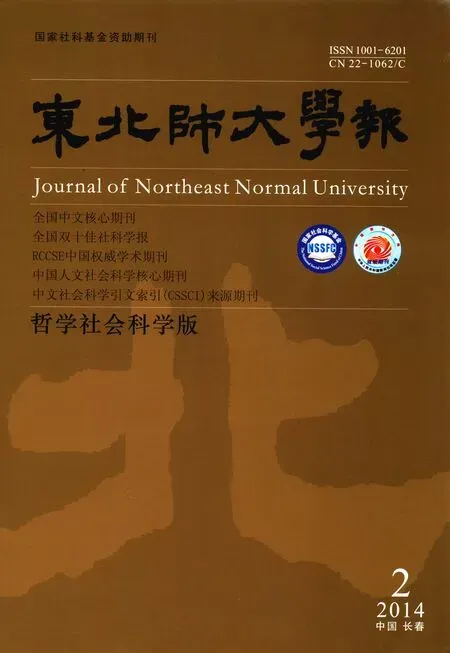中国传统“文治”精神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所,北京100000)
中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具有鲜明的“文治”思想传统和政治特色。“文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内蕴宏深,若一言以蔽之,可概括为:经世以“文”,化成天下。
一、上贞天道:文治之精神源头
《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37“上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的精神本源地位。“上天”作为“天道法则”的终极来源,贯穿在历代国人的文化血脉中。“贞天道”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根基。故治国安邦必“贞天道”,如此方可“立人极”。
“道之显者谓之文。”[1]37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语境中,文、道、治内蕴会通,从而共同开掘出中国传统“文治”精神的形上境域与学理品格。在中国古典文论语境中,“文”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人文理念的表达,它几乎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2]9!中国古人正是通过“文”来通达天命的。“文”的神圣意境成就其本体论的宏大内涵,从而世事万物皆由“文”展开其思想脉动。
从发生学维度而言,中国之“文”源自于对天地万物特征的临摹描绘,它是对天地万物进行高度视觉概括和意识概括之后的符号化呈示,在构形示意上具有本体呈现性质。《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3]。伏羲氏在俯仰天地之间了悟了人间万象,并将天道、人伦之理以八卦卦象这一象形符号显明于世。在古代先哲的意识深处,“文”被赋予了与天地并生的形上特征,从而使其具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昭示天意的宗教神启的内在意蕴,“文”于是升腾为一种统摄万事万物的精神意念。举凡人类社会中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现象、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都可以“文”来指称。正如明朝的宋濂在《文原》中说的那样,“故凡有人的一切弥纶范围之具,囿乎文,非文之外别有其他也”。总之,古人正是由对“天文”宇宙自然规律的观察理解与把握而演化出人文之“文”即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2]14。然而“道心惟微”,惟有以“文”总天下之义理,方可“建大中而承天心”[4],天下才可安顿。
在中国先贤圣哲看来,经国安邦的理想模式是经世以“文”,或者说以“文”为本。古之“文”有“文教”之文、“文道”之文、“文野”之文等多维要义。在中国传统“文治”语境中,政与学、道与文、治与化互为一体,相辅相成,从而形成道、学、化相互勾连的逻辑理路,建立起中国传统“文治”政治以学术立国、以道义立国、以文明立国的主体架构。
二、学术立国:文治之思想理论灵魂
早在儒家重要经典《礼记·学记》中便明确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国君民”即为政治;“教学为先”强调了“教学”的前提性作用,已经反映出先秦儒家学术立国的思想。清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总结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宋代的张载,更是把学对政的作用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有为学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这种高度重视思想学术的传统政治理念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特别是汉代以后,这种理念不仅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简单继承,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如汉初君臣就经常讨论秦亡之教训。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然立国未及三代便遭败亡。秦亡于暴政,史家早有定论,但其暴政更体现为一种“文化暴行”。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厉行文化专制,践踏学术,“使其政权既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又丧失了激活创新新文化、新制度的文化原动力”,“秦王朝在新的思想文化构建上的苍白无力,这正是秦王朝短命的根本原因”[6]。“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7],以“势”治天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8]。“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占”,皆非治国之道,秦王朝“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9]。正是基于亡秦之鉴,汉代才高度尊崇载道之学术(主要是儒学)。在此基础上,中国又逐渐确立了以学人参政的文官制度,而且一直延续下来。以当代观念视之,学术思想力确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一个学术思想力薄弱的国家难以长期稳固强大。古人学术立国的思想启示我们,今后还须全面提升整个社会的思想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蓄精神动能。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学术立国的思想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其“学术”说到底,主要是道德伦理之学,而非广义的学术,更不能与“科学”混为一谈,特别是因儒学长期定于一尊,因而也严重抑制了中国的思想活力,限制了学术研究领域,影响了中国的学术发展,未能引领中国产生各门近代科学,这是最大的遗憾。
三、道义立国:文治之道德伦理核心
中国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10],“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11],“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12]。这种观念,早在殷商末期就已出现,到春秋战国时已经形成。先秦早期道义立国的政治理念,在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逐渐被道德伦理化,从而使道义原则进一步演变为政治道德准则。孔子提出“德治”,孟子力倡“仁政”。“德治”、“仁政”,皆为政治的道义原则,且与个人伦理相关。孟子提出仁、义、礼、智的“四端说”,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认为,仁政的基础在于“仁心”,为政者所以应该施行仁政,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自然地将个人的“仁心”、“仁爱”伦理延伸扩展为政治的“仁政”主张,并且把仁、义、礼、智四种人格理想与为君者能否“保四海”联系起来,从而成为政治伦理。孟子将这种伦理的功能无限放大,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13]。而和仁义背道而驰,实施暴政的人,就是残贼仁义之人,即使是天子,也应受到诛伐,“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诸一夫纣,未闻弑君也。’”[14]。孟子的主张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古代道义立国的思想。
这种道义立国的思想启示我们,政治权力只有以道义为根基才能取得人们的认同,从而建构自身的政治正当性。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在东方的中国社会,政治正义或说政治道义问题都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正义与道义虽然在语义内涵上略有不同,但都有着共通的精神底蕴,这就是对社会公正与政治正当性的追问。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政治正义问题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政治价值取向,那么在东方的中国社会,政治道义问题则是决定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问题。
当然,我们在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道义立国精神的重大思想价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存在着重要缺陷:第一,由于单方面过度强调了道德的作用,因而比较忽视国家的法制建设,虽然传统政治文化不是完全排斥法,有时还与礼连带而讲“礼法”,但毕竟比较欠缺法制精神。第二,虽有民本思想,但缺少早期民主思想的基因。这两点与古希腊、古罗马传统政治文化具有较大的差异。
四、文明立国:文治之礼义秩序规范
恩格斯指出,文明是个历史概念,文明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广义的文明包括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中国文明立国思想显然有保持自己“进步状态”的强烈追求,因而历史上经常有“华夷之辨”、“文野之分”,甚至一直到近代,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中国人仍称西方人为“西夷”,可见中国人的文明优越感。实际上,中国也确以世界文明古国著称,而且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早已中断,而唯有中国传统文明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是世界上唯一绵延未绝的文明类型。
作为精神文明,不仅包括思想、信仰、学术层面,也包括礼乐文化方面。这些都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在儒教文明中也占有极重要地位。中国号称“文明古国”、“礼义之邦”,就侧重指中国礼乐文化的发达。长期以来,中国人也正是以此为最大的自豪,因而有时所谓“文明”乃特指礼乐文化而言,正如著名礼学家杨向奎先生说的那样,“‘礼’代表文明”[15]。现在,学界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方面的著述甚多,而对“礼”的方面则比较忽视,研究更显不够。
儒家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德治”、“仁政”,但仅此显然难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儒家也不是全然不讲刑罚,不过“德主刑辅”而已。但这仍然不够,故儒家在重“德”的同时也重“礼”,将其作为重德轻法的补救之道,因而又形成所谓“礼治”。实际就是要通过礼乐制度建立起尊卑、上下、亲疏、长幼等一套人际秩序及若干节义规范,以防止混乱和争夺,因此许多礼本身就是典章制度,以致从“隆礼”的荀子演化出后来的法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经常“礼乐”并提,实际古代“乐”也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谈“礼”自然包括“乐”,也含诗与舞。
中国礼的起源甚早,早在夏、商即有“夏礼”、“殷礼”,孔子尚“能言之”,周礼则更为发达,孔子曾一再表示对周礼的赞赏,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16]。后来虽经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历代对礼又多有损益,对礼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但都没有舍弃礼乐文明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古人认识到礼与治的关系太重大了。孔子就大声疾呼“克己复礼”,提出:“不知礼,无以立也。”[17]“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8]孟子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19]荀子说:“礼者政之輓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20]《左传》说,“礼,国之幹也”[21],“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2]。古人显然是将礼作为立国之本了。所以《礼记》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23]明初,连草莽出身的太祖朱元璋也谕示群臣说,“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并将此语编入《大明太祖高皇帝宝训》。
中国文明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对当代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首先,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和、作为一种进步状态的宏观文明观来说,我们必须保持一种相对更加先进的状态。中华文明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可是在封建社会后期逐渐封闭和衰落了。在近代,中国“被广泛用作落后、僵化、反对进步”的象征,而不被“视为文明的国际关系中的一名伙伴”[24],世界列强无不打着开化中国的旗帜,大肆鼓噪侵略中国的歪理邪说。身处强国林立、争夺不休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对此,我们必须长期保持高度的警醒,再也不能故步自封,使中华文明因凝滞而萎缩,而是应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开放的态度,努力发扬光大自己文明的精华,积极吸收其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
其次,从狭义上说,中国作为“礼义之邦”的礼乐文明,也有诸多可资借鉴的价值。作为古之礼仪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多被废弃,没必要再行复古,但作为“礼意”(制礼作乐的立意),我们则可从中获得重要启发。笔者认为,古人之“礼意”主要有二,一是求和谐,二是行教化。诚然,渊源于宗法关系的古代礼乐是欲以此构建理顺各种等级秩序,但求秩序本身就是求和谐,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所以孔子明确说“礼之用,和为贵”[25],可谓一语道破实质。荀子也讲:“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新起也。”[26]此语更为深刻,礼就是要消解“争”与“乱”,因而须有度量分界等礼义规范,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尤其可贵的是,荀子还试图通过礼义来调节人欲与物质资源之间的冲突,提出不能让人欲穷尽物质资源,这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对当代人类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的礼乐文明对当代中国最具启示意义的当属“礼义”(礼乐之道德大义)。古人“缘情制礼”,同时也“礼以义起”。《礼记》说,“故礼者,义之实也”,“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故古代经常“礼义”并称。而且与一般道德准则相比,中国古人特别是士人对礼义更加秉持十分敬畏的态度,非礼不义,便被视为“无耻”,便是只“喻于利”的“小人”甚至败坏节操的坏人。中国古人对礼义内涵的各种具体界定现在可能许多已经过时,不尽可取,但礼义精神还是需要发扬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人更需要一些礼义规范的自我约束。现在,中国人确实已把古人尊礼重义的“君子”之风丢失殆尽,世道人心乱象纷纷而又治理乏策,我们确实很需要在全面严明法制的同时尽力以礼义廉耻大义对人加以引导教育和自我约束节制,并逐渐形成全社会的良好风尚。
五、化成天下:文治之终极旨归
所谓“化”,意指归化、教化、进化(古人提出“据乱世”——“小康世”——“大同世”之“三世”进化说);成者,谓化民成俗,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化成天下,“化”为根本,也是难点。具体说,该如何“化”呢?古人没有集中的论述。如进行归纳,主要有以下五种途径:一曰行德政。先秦典籍多处记载周文王以仁善立国,积蓄善德而归化天下,故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7]。孔子主张德礼并用,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归民,也可以化民,他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8]。二曰尊学术。前文已多加论述。三曰兴学校。中国很早便形成了兴学化民的传统,正如《礼记·学记》所说,“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通过学校教育,使“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四曰广教化。礼乐是实施教化的重要途径。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9]除了礼,古人似乎更重视乐的教化作用。《乐记》说,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30]。五曰上作则。正人正己,成己成物,是重要的儒家思想传统。孔子提出,正己才能正人,修己才能安人,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1]。孟子也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32]因而统治者必须先正己,即以身作则,才能平治天下。
中国古人化成天下的主张及其化成之法,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归化”的意义上说,用现代政治术语表述,“归化”相当于“认同”。“认同”不仅指一个社会共同体成员对某一政权的接受和认可,也是对一定信仰及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是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是国家内聚力的根源。从“教化”的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各种教化之方对当代也多有借鉴价值。如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何才能真正内化为全民的共识乃至信仰,升华为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十分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数代人的长期努力才能完成。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教化思想中汲取很多营养。至于古人“三世”进化的理想,应该说不仅对中国,对人类也是一大思想贡献,仍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征程中,中国传统“文治”精神一方面确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另一方面这种“文治”精神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形成一定的历史延续的惯性力量,需要我们正视这种现实,然后因势利导,在此基础上再以兼容并包的胸怀,吸收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进行价值观的重新整合和广泛教化,从而配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率先实现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伟大更生。
[1]王弼.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2]刘勰.文心雕龙·原道[M].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易·系辞下[M]//中华儒学通典.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37.
[4]班固.汉书:卷八十五[M]//简体字本二十六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213.
[5]张载.张载集·拾遗·近思录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1978:376.
[6]雷依群.重新认识秦亡汉兴[N].光明日报,2003-08-26(B3).
[7]王夫之.读 通鉴论:中册[M].北京:中华书 局,1975:413.
[8]左传·庄公十一年[M]//中华儒学通典.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437.
[9]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M]//简体字本二十六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3192.
[10]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19.
[11]荀子·君道[M]//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0.
[12]墨子·天志下[M]//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5.
[13]孟子·公孙丑上[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53.
[14]孟子·梁惠王下[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33.
[15]杨向奎.吴越文化新探:序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
[16]论语·八佾[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64.
[17]论语·尧曰[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10.
[18]论语·颜渊[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40.
[19]孟子·公孙丑上[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52.
[20]荀子·大略[M]//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95.
[21]左传·禧公十一年[M]//中华儒学通典.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456.
[22]左传·隐公十一年[M]//中华儒学通典.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422.
[23]礼记·哀公问[M]//中华儒学通典.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384.
[24][俄]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28.
[25]论语·学而[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51.
[26]荀子·礼论[M]//四库全书荟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42.
[27]论语·季氏[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80.
[28]论语·为政[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56.
[29]论语·泰伯[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07.
[30]孟子·尽心上[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417.
[31]论语·子路[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50.
[32]孟子·离娄上[M]//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