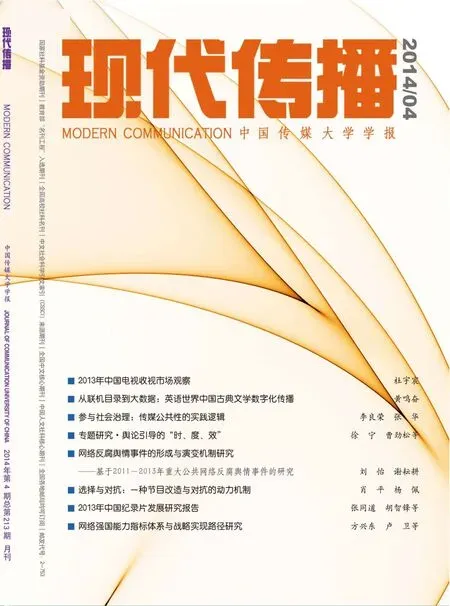新记《大公报》的科学传播特点及策略研究
——以《科学周刊》《科学副刊》为例
■ 王金福
新记《大公报》的科学传播特点及策略研究
——以《科学周刊》《科学副刊》为例
■ 王金福
新记《大公报》的《科学周刊》《科学副刊》(以下简称科学类副刊)以“普及科学”为主旨,详实记录了20世纪20—30年代科学传播的内容和特点,是研究近代综合类报纸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关于《大公报》副刊的研究文章很多,角度各异,但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为此,笔者尝试以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为例,探寻我国近代史上综合性报纸在科学传播方面的概况,分析其传播特点和传播策略,以期为探究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一些研究基础,为当下报业的科学传播提供经验或借鉴。
一、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的总体概况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主要以《科学周刊》《科学副刊》为主,两个副刊的创办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29.1.9—1930.5.28),由清华大学的夏坚白主编,刊名《科学周刊》,出版65期;第二个时期(1933.3.3—1934.9.14),由“二二社”和“三三社”合办,由北洋工学院的雷孝实主编,刊名《科学周刊》,出版80期;第三个时期(1936.7.19—1937.7.25),由《大公报》自办,刊名《科学副刊》,共出版29期。①
科学类副刊,虽根据不同时期需要,由不同单位主办,但三个时期的科学类副刊的创办均是新记《大公报》“普及科学”理念的具体体现,具有时间和内容上的连续性,均担负着民众启蒙的责任,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载体。②三个时期科学类副刊以新闻消息、连续报道、科学译文、开设专栏等方式,积极推介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阵地之一。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所刊载的内容涉及物理、化学、电子、天文、冶金、航空、地质、水利、矿产等学科,刊载内容丰富多样,为当时国内同行翘楚。正如大公报人陈纪滢所说:“大公报开辟各种副刊,是全国所有报纸最成功的一家,直到今天似乎没有一家报刊堪与媲美。”
二、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科学传播的特点
1.内容丰富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所报道的科学知识涵盖了自然科学的很多门类,为大众全面了解科学知识提供了便捷途径。同时,科学类副刊还大量刊登西方科学理论的翻译文章,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思想同步引入中国。以1929年夏坚白主编的《科学周刊》为例,该副刊每期设有一个固定栏目“科学珍闻”,介绍最新的科学发现与应用,如《胃中摄影箱》(1929年5月1日)、《紫外光养猪》(1929年5月15日)等等,所刊载的文章,以新奇取胜。1933年3月3日创刊、由雷孝实主编的《科学周刊》除了设有“科学珍闻”外,还设有“科学杂闻”“杂俎”“国内科学新闻”“外国科学新闻”栏目,介绍国内外的最新科学发现与研究成果。《大公报》自办《科学副刊》则设有“科学拾零”“科学新闻”“科学知识”“科学进步”“科学珍闻”等栏目,介绍科学发展动态。作为综合性报纸,《大公报》对科学知识的传播可谓不遗余力。
2.形式灵活
新记《大公报》时期正值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民众对西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认识到借助西学对民族振兴和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基于此,在版面安排上,科学文章图文结合,编排生动活泼、文字浅显易懂,方便受众理解。
科学类副刊特别注重受众的科学知识需要,并根据读者需要开设专栏。以《科学周刊》为例,该刊用较大篇幅开设《读者问答》和《科学珍闻》两个专栏,《读者问答》每一期选取读者提出的涉及科学知识的3-4个问题予以回答,是一种典型的引发读者兴趣的科普形式。这一形式极大激发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拉近了编者与受众间的关系,形成了编辑和受众互动的传播模式,有效扩大了科学类报道在受众间的影响力,实现了通过大众媒体向广泛民众传递科学知识的目的。
3.专家著述
新记《大公报》时期,特别注重科学报道,深知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以求让大众“多一门常识”,“多一分应付环境之能力。”③这些办刊理念为推动科学传播、增进社会对科学的兴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三个时期的科学类副刊均不惜版面大篇幅、系统地介绍各门科学。其中,在1929—1934这5年间,两度约请高校的专业人士担任主编,编辑出版《科学周刊》,“凡科学新闻、论著,不惜以显著地位予以刊登”。1936年7月,大公报在经营和编辑业务紧张的情况下,依然自办《科学副刊》,并以可观的稿酬约请专家撰述论文。
新记《大公报》时期的科学类副刊积极充当专家学者思想的媒介,通过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请出实验室与研究室,转化为通俗的科学,灌输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使民众养成崇尚科学的心理,增进国人的科学修养。1936年7月—1937年7月,一年间就有翁文灏、任鸿隽、秉志、顾毓琇、郭永怀等知名学者在《科学副刊》刊发文章,表达思想观点。④
科学类副刊“通过问题的解答,帮助人们澄清错误观念,养成从科学角度观察看待周围熟知事物的良好习惯”。“通过科学类副刊,科学家与研究者走出实验室和研究室,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的科学知识,传播给普通民众。”“激发社会民众的科学研究兴趣,正是科学类副刊大力宣传科学学术团体活动的原因所在。”“科学类副刊,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还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阐释高深的科学学理,帮助人们梳理正确的科学观。”⑤
三、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的科学传播策略
1.秉持“以普及科学为主”
“以普及普通科学知识为主”是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共同的价值取向。1929年1月9日《科学周刊》“发刊词”写到:“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以后建设事业百端待举,但最重要的是增进我们国力。要不遗余力地提倡物质文明——要自己创造物质文明,就非从根本上下手,我们要提倡科学。”1936年7月《大公报》自办《科学副刊》,其编辑方针是:“在灌输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因势利导,俾养成人民崇好科学之心理,于潜移默化之中,增进国人之科学修养,以补社会教育之不足,系为大众着想,非为专家而设。”⑥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不遗余力地提倡科学、信仰科学,不是急功近利式的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是要学习西方人信仰真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2.充分发挥科学团体和专家学者优势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在办刊方面,充分发挥科学团体和专家学者优势。一方面,科学类副刊大力宣传科学家的精英团体,扩大科研机构在社会的影响,鼓励科学家参与国事;另一方面,积极调动科学家积极性,利用《大公报》科学类副刊推进社会科学化,为社会服务。
新记《大公报》的领导团队深知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929年到1934年两度约请社外专业人士担任科学类副刊主编,并力邀李书田、张含英、李书华、任鸿隽、严济慈等专家学者为副刊撰稿。为鼓励科学家积极参与科学知识传播,大公报还设立科学奖金,鼓励科学事业。1937年5月,数学家王熙强、化学家刘福远、动物学家倪达书、植物学家梁其瑾、气象学家魏元恒等分别获得“大公报科学奖金”。新记《大公报》就是通过对科学团体和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宣传,以期引起社会关注,鼓励民众去认知了解科学。
3.注重编辑和受众互动
为提高大众定读性和参与度,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特别注重编辑和受众互动。通过开辟固定栏目、读者来信等形式,刊载大量涉及科学小常识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夏坚白主编《科学周刊》时,开辟有“科学小问题”“答读者问”等栏目,通过读者提问或编辑设问,然后再进行解答的方式,解读科学常识、普及科学知识。比如,《雨雪是怎样形成的》《刮脸为什么用胰子》等等。科学类副刊就是通过生活中具体现象告诉大众“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同时,为满足民众的猎奇心理,报社还约请科学界专家学者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论文和科学常识,刊载最新科研成果。如1933年12月15日《科学周刊》刊载内容,既有科普类文章《宝石之研究》,也有翻译国外科学家所著科学之文章,如《无线电机之线圈——计算、制造及应用》,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将专业知识以浅显的文字和图画展示给读者。这些颇具实用价值的文章,对于唤起公众对科学常识的兴趣,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所刊载文章,注重大众性和知识性。副刊把受众定位为普通大众,刊载内容除了少量学术性的长篇宏论外,多数为语言通俗的科学普及性文章,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从撰稿群体来看,科学类副刊联系凝聚了一批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处于科学前沿、擅长理论思维、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和写作能力,保证了科学类副刊的稿源和稿件的“新闻性、趣味性、可读性”。
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的传播策略也屡有创新,通过一介传播、二介传播甚或三介传播的方式,以答读者问、设立科学奖金、与科研机构联合等方式,拓展副刊的影响力。同时,副刊针对普通大众的需要,按照普通人的认知程度和兴趣进行知识链接,并对链接的科学材料进行文学化、大众化的处理。
综上,新记《大公报》科学类副刊践行“普及科学”理念,通过细化栏目、图表结合、知识问答、专家约稿、翻译外电等方式,介绍科学知识、普及科学理念,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为当代纸质大众媒体在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注释:
① 杨晶、王大明:《〈大公报〉在现代中国科学传播方面的作用初探》,《第十一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2007年版,第395 -406页。
② 王文彬:《中国报纸的副刊》,中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106页。
③ 李书田:《休刊辞》,《大公报·科学周刊》,1934年9月13日。
④ 贾晓慧:《〈大公报〉视角下的科学化运动》,《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3期。
⑤ 李秀云:《大公报专刊研究(1927-1937)》,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121页。
⑥ 《发刊旨趣》,《大公报·科学副刊》,1936年7月11日。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