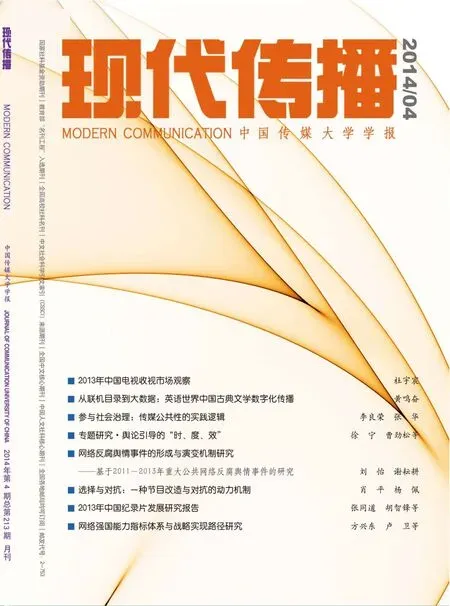电视传播中的仪式复兴及反思
——兼论湖南卫视成人礼晚会
■ 谢 莹
电视传播中的仪式复兴及反思
——兼论湖南卫视成人礼晚会
■ 谢 莹
为积极响应共青团中央关于深入开展18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的号召,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卫视与中国青年报社共同打造了一档“五四”特别节目——成人礼晚会。晚会根据电视媒介的传播特色和受众特点,对仪式的整体构造进行了重组。2009年至今,该节目连续五年成为同时段4—24岁观众群的收视冠军,为这一仪式的推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通过梳理成人礼与电视及现代生活的因果脉络,来寻觅传统仪式与现代媒介文化的可能交集,并对其社会功能及文化意涵进行读解。
一、社会变迁与成人礼的回归
在少年步入青年的角色过渡之际,由于新旧角色的差异,个人认知的局限,个体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激烈的冲突,成人仪式的举行可以帮助个体确定对成人这一生命阶段的认知,消除过渡时期的不适应感。所以,在成人礼兴起的原始社会,人们往往采取隔离或囚禁的方式让孩子们接受生命的考验,感应自然界神秘的力量,消除因身体第二性征的出现所带来的恐慌。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纪念生理成熟的成人仪式演变为一种社会身份与社会责任的确认,如我国的冠礼、及笄礼,它们意在对青年进行宗法伦理道德教育。进入近代社会后,“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策略使许多传统仪式包括成人礼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果说“仪式的兴衰是一次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①,那么成人礼的回归则是基于对当代青年认同危机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传统仪式的教育功能重新认识的结果。而成人礼晚会则是仪式复兴在媒介生产领域中的一种表征,是策划者在对青少年文化与电视媒介文化之间关系透彻领悟后的创新之举。
在一个发展缓慢的古老社会中,传统成人礼利用简单的手段就能起到缓解过渡压力、帮助青年角色适应的作用。可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信息时代,技术与文化形态的飞速变化给社会心理带来了强烈的震荡,身份危机、信仰缺失、媒介沉溺等青少年问题层出不穷,支持成人仪式权威性的社会文化心理已经大大减弱。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这样解释当今世界的社会心理与信仰危机,“如若追溯这一信仰危机的缘由的话,它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已不存在比年轻一代本身更能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长者。”②由长者组织仪式将上一代的宗教信仰及道德规范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化延续方式在现代社会已很难再发挥作用,这样,如今的成人礼必须通过仪式的创新,建构更丰富的象征体系来寻求青年的文化认同。
青年文化与大众文化紧密相关,“大众文化从来不加掩饰的愉悦性、商业性对当代青年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③电视是大众文化的载体,因此电视与成人礼的结合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20世纪下半叶,“媒介事件”作为一种新颖的电视样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更为成人礼晚会提供了现实依据。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休·卡茨在《历史的现场直播:媒介事件》一书中,将这些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又称为“电视仪式”“节日电视”或“文化表演”,它带领观众进入影像空间见证、体验历史的现场直播,从中感受到一种参与式的仪式感,这其中就包括了过渡仪式的现场直播。成人礼晚会独特的召集方式、有序的编排模式、固定的播出时间促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介事件”,使我们不必一厢情愿地执意恢复古礼,而是可以借助电视节目唤醒人们的共同记忆与团结之情,为青少年的人生转折提供强大的心灵支撑。
二、晚会与文化认同的确立
成人礼晚会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电视仪式,为了更好的延续成人礼文化认同的功能,在晚会的叙事体系中巧妙地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官方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晚会从青少年流行文化那里汲取灵感,对其进行包装、复制、宣传,迎合青少年消费者的趣味,仪式中的严格程序被观众的集体狂欢所代替。原始社会的成人礼是一种部落仪式,包括因部落而异的肢解行为(如割礼、纹身、穿孔等等)、图腾仪式、背诵神话等程序。中国古代冠礼则是一种家庭仪式,由家族中受人尊重的长者为成年男子加冠三次,缁布冠、皮弁、爵弁,循序渐进。而成人礼晚会却是跨越地域举国狂欢的大party,除演播厅主会场外,还设立地标性的分会场,推及全国观众规模约1亿多人。承担教育者角色的长者被各行各业青春偶像级的“致礼嘉宾”所代替,如著名教育人士俞敏洪、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冬奥会冠军王濛、歌手李宇春、人气作家韩寒、清华才女蒋方舟等。同时,成年礼中“赎罪—洁净—奉献”“苦行—磨砺—考验”这些所谓的“试炼”行为被歌舞表演与故事讲述所代替,每年晚会的主打节目劲歌热舞几乎都由快男超女、日韩明星、港台明星出演,将青少年的偶像崇拜演绎到极致。而“校园社团”表演、“QQ诗朗诵”“千人行为艺术秀”等节目也无一不在凸显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所有这些都为成人礼的电视传播打上了青少年亚文化的烙印,它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种“文化的共同体”,让青少年在消费流行文化的同时,个体的自我一致性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统一。
另一方面,成人礼晚会又是社会主流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的载体,为青年提供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成人仪式教育活动自复兴以来,先后被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中,成人礼晚会由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卫视、中国青年报社共同主办,可见这不仅是一种媒介行为,更是一种官方行为。出于提高爱国热情的考虑,晚会的播出时间是五四青年节这样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分会场的选择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地方,如烈士陵园和青少年教育基地等。每台晚会不仅叙事主题迎合当年国家的重大议题与事件,而且流程都依循“个人成长的故事”—“感恩父母的故事”—“保家卫国的故事”—“集体面向国旗宣誓”这样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层层递进的叙事脉络。2010年成人礼加入与世博会联动的环节,将年轻人的青春梦想和国家的腾飞结合。2013年成人礼晚会主题为“对话梦想”,便是映照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晚会最后,由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手执五星红旗行进至舞台中央,全场同学庄严宣读誓词:“今天,面对国旗,我庄严宣誓,我已长大成人,永远做祖国忠诚的儿女……”通过这样一种程序的安排,民族、国家等象征符号被巧妙地编织进人生故事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个人生活信念上升到国家民族的认同,塑造了一个关于民族与国家的“想象共同体”。
但是,对于成人礼晚会这种创新形式,我们仍需要反思的是,将娱乐性始终放在首位的电视晚会到底能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产生多大的效应?而且在一个文化冲突、文化悖论始终存在的现代社会,一台孤立的晚会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仪式功能?
三、仪式的反思与延续
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曾将过渡仪式分为隔离、过渡、聚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与日常的社会生活分离,第二个阶段是仪式的正在进行时,第三个阶段则是再次整合进入社会。在传统的成人礼中,这三个部分构成了整个仪式的基本结构,在连续而完整的过程中将仪式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如隔离阶段,原始社会中的孩子们抛弃过去的生活,在丛林中信守着某些饮食、衣着、行为的禁忌,伴随着身体与精神的弱化,渐渐失去童年的记忆,为重获新生做准备。中国的冠礼,受冠之前,受冠者就需要不断地学习各种礼仪及乐舞为进入整个社群生活做准备。《礼记·内则》篇曾言:“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十有五年而笄。”无论男女,都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拥有一定能力后才行成年礼。在成人礼晚会制作播出前,孩子们通过热线报名、导演组挑选、收看宣传片等一系列特定的组织方式来参与或收看节目,这种参与资格的获得无需通过考验与学习,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一件幸运或好玩的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隔离期的缺失,使得成人礼晚会失去的不仅仅是神秘,还有严肃性。同样缺失的还有仪式的聚合阶段。原始社会的成年人参加完仪式后拥有了永久性的身体标志,成为真正的部落勇士出门狩猎及参与战斗;冠礼结束后,成年男子在穿戴方式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拥有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但是成人礼晚会结束后,青年们重回日常生活,照旧以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最后的冲刺,短暂的集体狂欢与他们枯燥的日常生活并非是自然衔接的,而是相互冲突与隔绝的,仪式上的宣誓激情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他们很快就会被一系列随之而来的人生问题所困扰,自然难以实现成人仪式应有的效应。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更为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文化冲突与悖论更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青年人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会更加困难。青少年文化的特点本来是激情洋溢,活力四射,充满了反抗性和颠覆性。可是今天的青少年要么躲进流行文化的消费中,对父辈文化消极应付,要么就是利用官方话语为自己谋利或度过尴尬。有学者这样评价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犬儒主义和分裂人格已经达到不再有任何分裂感的程度”④。因此,尽管成人仪式的兴起源自于对未成年人的一种理想化的蒙昧状态的假定,但与此形成悖论的是,在他们参加成人仪式之前,由成年人所构造的环境早已消解了这种“天真烂漫”。未成年人所置身的社会环境被各种社会资本全面入侵,而且恰恰因为电视媒体的耳濡目染,他们早已识破了电视节目和成人世界的“鬼把戏”。正如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的,“因为电视的出现,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开始变得模糊”。⑤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儿童对成人的好奇被愤世嫉俗与狂妄自大所取代。这正是现代未成年人的尴尬,他们虽非成人却无童年。成人礼作为一种过渡仪式也是一次尴尬的过渡,集体的狂欢以及对官方文化的认同不过是他们配合节目播出的一次集体表演。
总之,在工具化的教育制度与纷繁复杂的文化政治生活下,成人礼晚会精心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意识”可能最终会被个人化思维所取代。因此,若要将成人礼晚会的仪式功能最大化,还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连接晚会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使仪式所确认的信仰与身份更好地延续。这样看来,电视节目传播仪式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形式的创新,更应是理念的创新,而这种理念应该反映我们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状态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理解。
注释:
①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② [美]M·米德著:《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购问题的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③ 胡疆锋:《中国青年文化的当代版图——从“青年文化消失论”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
④ 陶东风:《两代人还是两种人?——关于青年与青年文化的随想》,《学习博览》,2012年第9期。
⑤ [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作者系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