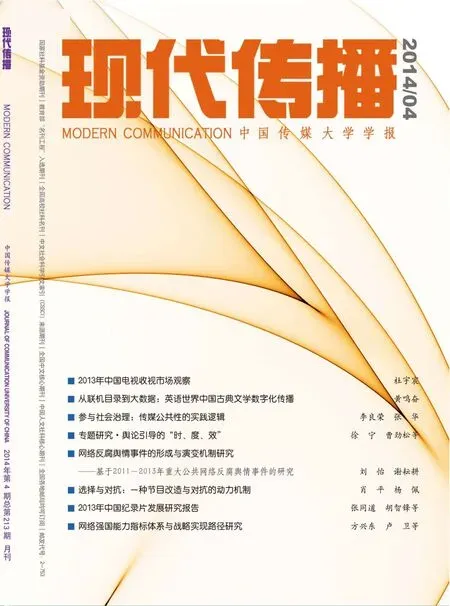早期红楼电影与海派文化
■ 何卫国
20世纪初,上海已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我国电影的肇始地。自1923年张石川创办明星公司始,上海诞生了大量的电影公司。据统计,1925年前后,中国成立了175家电影制片公司,其中上海141家,而真正有过出品的几乎全在上海。中国早期电影对上海的依赖性可见一斑。
我国1949年以前的红楼电影几乎都产自上海。红楼电影的摄制与整个中国电影的轨迹一样,是从拍摄“国粹”“国剧”京剧开始的。最早的红楼影像是1924年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摄制的京剧《黛玉葬花》片段,是作为系列短片中的一个片段拍摄,因此不算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电影。①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红楼电影是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摄制的《红楼梦》(简称复旦版《红楼梦》)。此外还有1927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摄制的《红楼梦》(简称孔雀版《红楼梦》)、1936年上海 (一说“香港”)大华影业公司摄制的《黛玉葬花》、1939年上海新华影片公司摄制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1944年上海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摄制的《红楼梦》 (简称周璇版《红楼梦》)。
我国早期电影的诞生与流变,离不开海派文化这一“文化母体”。②海派文化作为上海近代以来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上海本土吴越文化与由租界带来的西方文化在上海这一特定历史空间相互渗透交融的必然结果。上海特殊的社会形态与地域人文背景造就了海派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海派文化滋养了早期红楼电影,而早期红楼影像又历史性地成为海派文化的视听表征。当然,作为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红楼电影不可能像现实题材那样鲜活地呈现旧上海印象,但从这些斑驳的影像中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海派文化的身影。因此,在上海地域文化与早期红楼电影之间,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与红楼电影的“敢为风气先”
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取代北京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通商口岸,其文化以多元化与开放性著称。上海不仅对外开放,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对内开放,吸纳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劳工等各种人,成为新旧文化、中西文化汇聚之所。基于这一特殊的地缘优势,上海的文学、电影、绘画、建筑等艺术不仅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地域文化要粹,还大胆吸收西洋优秀文化,勇于标新立异、敢开风气之先,呈现出海派文化多元性的开放特征。上海电影独领风骚的开拓作用贯穿于我国电影发展史。国产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动画美术片《纸人捣乱记》、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武汉战争》、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立体宽银幕电影《魔术师的奇遇》等,无不脱胎于上海。
这一文化特征也影响了早期红楼电影的改编。上海不但开创了红楼电影传播之先河,而且在改编中体现了鲜明的开放意识与创新精神。第一部公映的红楼电影 (复旦版),尤其体现了这一海派文化的特征。
复旦版《红楼梦》首开以时装拍摄《红楼梦》的先河。众所周知,《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虽然其故事发生的年代“失落无考”,但大体在明清朝是可以肯定的。其中的背景与人物传达的都是“传统中国”的印象,改编成电影与戏剧,自然是古装戏。但我国的第一部红楼电影却是时装剧。复旦版的改编者认为:“红楼梦说部,脍炙人口,几于妇稚皆知,特是书空灵玄奥,什九都系寓言……斯书第一迷离恍惚处,即于年代为不可考……故本公司对于服装一层,宁可景从时流,脱以古式相炫,反遗蛇足之诮耳。”③编剧徐碧波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是书对于妇女之足,绝对的弗有涉及,于是索隐者据之即为专述旗人之证。又不及于时代与年月,令人不可捉摸。惟其如此,苟摄制影片而演为时装,初亦无所抵触,倘必欲加以古代衣冠,予且请问须服何朝装束为宜?至此,恐提议《红楼梦》影片必须古装者亦且结舌矣。”④看过试映的观众有的以为:“银幕中人俱作时世妆,间有鸭头巧翦一梳云者,别有一种致趣。”⑤有的则说:“剧情离奇动人已是可取,何必斤斤于服装问题呢?难道穿上时装就不能表演剧情了么?所以古装和时装没有大关系的。”⑥从复旦版的宣传特刊来看,主创人员与评论家认为《红楼梦》一书始终未示明年代,穿时装是可行的。“时装”在当时及以后都曾受到严厉指斥,但就其开放的心态而言,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非常大胆的。
复旦版在刘姥姥这一角色上也体现了鲜明的超前意识。首先,由男演员扮演刘姥姥。在红楼戏乃至红楼电影中以女演员饰演贾宝玉是传统的做法,袁美云、徐玉兰都是以饰演宝玉著称的女明星。但复旦版以富有喜剧表演经验的男明星周空空饰演刘姥姥,而且大获成功,这在之前之后的红楼戏和红楼电影中是极少见的。其次,整部影片“以刘姥姥入梦始,以刘姥姥出梦终”。梦中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成为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以刘姥姥的视角贯彻整部《红楼梦》电影,这需要不拘泥于原著的改编意识。纵观红楼改编史,这种视角仍不失为独特。
二、海派文化的世俗化与红楼电影中的宝黛爱情故事
海派文化作为一种都市文化,具有世俗化的显著特征。因此,海派小说、戏曲、电影等,也更贴近社会生活和市民情趣,注重娱乐化与休闲性。最突出体现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盛行。“鸳鸯蝴蝶派”这一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⑦这种“消闲”的文学作品满足了以移民为主体的上海市民的消费需求,其电影衍生品也促进了上海本土电影的发展。上海“国产影运动”中的大部分影片都以“鸳鸯蝴蝶派”小说为蓝本, “从1921年到1931这一时期,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六百五十部故事长片,其中绝大部分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⑧男女情爱故事历来是“鸳鸯蝴蝶派”的拿手好戏,所谓“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⑨。“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电影也主要讲述男女情爱故事,往往以“现代男女三角关系”表现都市市民爱情、婚姻生活中的“第三者插足”现象等。
鸳鸯蝴蝶派情爱小说的盛行虽然与上海移民阶层“消闲”阅读需求有关,但与传统吴越地区对情感戏的偏爱关系尤甚。海派文化的本土根源在吴越文化,吴越之民自古就有喜欢爱情婚姻题材故事的传统。宋元南戏、明清传奇诸多作品都可佐证。 “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市民爱情、婚姻生活中的“第三者插足”故事模式虽然有别于“才子遇佳人”的传统叙事母题,但其实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才子佳人故事。才子佳人小说是我国明末清初一大小说类型,虽然《红楼梦》作者借贾母之口对其口诛笔伐,但《红楼梦》仍然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抛开其深刻的思想性,其实同样是才子佳人故事。此点,对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而言,更是如此。电影作为影像艺术,较小说而言,本身就是大众审美艺术。以“鸳鸯蝴蝶派”的审美风格来看《红楼梦》,我们很容易过滤掉小说中的家族悲剧与人生悲剧,而“独具慧眼”地选择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纵观早期红楼电影,基本上都是围绕《红楼梦》中的情爱故事而展开。如复旦版虽然突出梦幻意识,但这种“人生如梦”的感觉却来自情爱的幻灭。影片表现的两大重心——王熙凤三计害三命 (贾瑞、尤二姐和林黛玉)及宝黛爱情悲剧的曲折发展都体现了编剧对情爱故事的偏爱;孔雀版虽然注重全本改编,也以元妃省亲开篇,强化贾府兴衰之主题,但其核心仍然是宝黛爱情故事;《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同样以王熙凤、贾琏、尤二姐“三角”情感纠葛为中心;周璇版《红楼梦》也以宝黛爱情为中心,因此虽然获得成功,但也不免招致“剧情过于简单,老是处在三角恋爱的圈子中”的批评。⑩
好故事还需要情节的巧妙安排。当时上海的文学、戏剧、电影都或多或少受到“情节剧”的影响。“情节剧”是最早源于法国以歌舞为主的一种舞台样式,大多以善恶二元对立的高度戏剧冲突为结构模式。较之西方观众,中国观众更适应这一情节模式。因为我国传统小说与戏曲本身就崇尚善恶、忠奸二元对立的故事模式。早期的上海电影,也多以情节剧的样式呈现,二元对立的夸张情节与价值判断成为电影的基本样式。这种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同样影响早期红楼电影的改编。与其他古典小说比较,《红楼梦》是一部诗性小说,它不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取胜,而是以细腻深刻的人情描摹见长。书中无大奸大恶之人,宝黛之悲剧乃“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这正是《红楼梦》的卓绝之处。相对而言,在宝黛爱情故事中,后四十回备受争议的“黛死钗嫁”情节无疑最富戏剧冲突。因此,早期四部以宝黛爱情为中心的红楼电影,几乎都选择了“黛死钗嫁”,后来家喻户晓的1962年越剧《红楼梦》电影同样选择了这一情节。黛玉与宝钗,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双峰并峙,二人无论是容貌与才情,作者都不愿分出高下。而早期红楼电影却几乎都是扬黛抑钗,何故?营造善恶二元对立的戏剧冲突模式是重要原因。除宝黛爱情故事外,王熙凤与“红楼二尤”的故事是《红楼梦》中相对独立且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即选取这一节改编摄制,开创了“红楼二尤”电影摄制之先河。其字幕注明:“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系全书中富有戏剧性之一节”。1951年上海“国泰”的《红楼二尤》、1963年上海“海燕”的《尤三姐》虽然浸染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色彩,但改编思路仍大体一致。
三、海派文化的个性化与红楼电影的反封建婚姻主题
“五四”前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东渐,反对旧礼教、旧政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上海作为东方国际化大都市,遂成为西方人文思潮的传播重地,从而使海派文化彰显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其突出表现在“强调个体的自由独立、表现人性的丰厚复杂、突出人生的世俗况味等方面”。上海文学则突出地表现要求摆脱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束缚、强调个体自由独立的主题。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幻灭》、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都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束缚个体自由独立的当属封建婚姻制度对自由婚姻的阻碍、对人性的禁锢。“《红楼梦》一书,叙人婚姻事,不祥者为多,盖明专制结婚之必无良果也。”“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书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妇,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从这一视角来看,真正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不是宝钗,也不是贾母、王熙凤等人,而是封建婚姻制度。
男女爱情与夫妇制度绝不发生关系,但相沿既久,无论二女争一男,二男争一女,苟不能与情敌争此纯洁之爱情,遂不得不假力于夫妇制度,而以种种卑劣之手段为夺婿逼嫁之举,以快其私欲于一时。……反是,因有夫妇制度,而所谓金钱也,势力也,门楣也,礼俗也,父母之命也,媒妁之言也,均起而为男男女女相争相护之焦点。有真爱情者乃转而无幸,是岂人之所堪受耶?
在这股时代思潮下,1949年以前的红楼电影,基本上以宝黛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突出宝黛的自由爱情与封建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封建家长对青年儿女自由爱情的扼杀。
孔雀版导演程树仁是我国第一代修习电影的留学生,从小爱读《红楼梦》。拍摄《红楼梦》之前,他仔细研读了胡适有关《红楼梦》的考证文章。写出剧本后,又请当时十余位新旧红学家审核,征求意见后“方敢制为电影”。由于复旦版抢先搬上银幕,发行商要求将影片改名为《石头记》,程树仁不肯委曲求全。为此,他对《红楼梦》片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红楼梦》最能体现他的影片剧旨:
吾人既用无数精神及许多金钱来摄制《红楼梦》,自当于万事之先,为《红楼梦》认定一个高尚之剧旨。第《红楼梦》作意,诸说互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余意以此彼,致使看客堕入五里雾中而无直接发生爽快之了解者。是为影剧所最忌。立意虽佳,不足取也。甚至牵强附会,怪诞不经之神怪迷信,吾辈俱受过高等教育,自矢为中华民国之新国民者,岂更有为之阐扬之理耶?由此观之,胡适谓为作者曹雪芹自述身世之说诚可认为《红楼梦》最高尚最有价值之剧旨矣。且曹雪芹自叙亦云“欲将已往所赖……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今欲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影此影彼,是大背曹雪芹于困苦艰难之中费尽心血著此《红楼梦》以述己警世之一番苦心孤诣也。
程树仁接受的是胡适等新红学的研究成果,而对索引派的“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影此影彼”颇为反感。作为“受过高等教育,自矢为中华民国之新国民”,程树仁虽认同胡适之“曹雪芹自述身世之说”,但并不拘泥于曹雪芹之身世,而是有感于曹雪芹费尽心血十年著书之“苦心孤诣”,以此警世与救世。具体则落实在“采用《红楼梦》中宝黛故事,以惊醒迷信旧婚姻制度之父母,提创婚姻自主,其亦改良社会之急图欤!”为突出这一主题,程树仁在改编中增加了一现实人物“曾友笛”干涉女儿婚姻最终悔悟之事。
读《红楼梦》本事,不禁感慨于吾国婚姻旧制,首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两端,而遂遗误青年男女终身幸福者,不知凡几。……吾友程树仁,有鉴于斯,编演《红楼梦》一剧,采用《红楼梦》中宝黛故事,以惊醒迷信旧婚姻制度之父母,提创婚姻自主,其亦改良社会之急图欤!其剧情为曾友笛恶其女俊英与王昌林自由恋爱,遂将昌林驱逐外出,后将俊英禁锢室内。旋因梦《红楼梦》中宝玉迫于贾母贾政之命,错成金玉姻缘。黛玉得此消息,一病不起,宝玉亦因情场失败,遁迹空门之一段故事,遂打消其把持婚姻之意旨,卒使昌林俊英成就美满姻缘。其穿插之得法,用意之深刻,迥非普通电影剧所可望其项背。”
周璇版《红楼梦》编导卜万苍在“剧旨”说明中也强调:“《红楼梦》一书,实写宝玉之多情,黛玉之薄命,正所以对旧式婚姻制度,作一当头棒喝也。”
四、海派文化的商业性与红楼电影的宣传特刊
海派文化具有典型的商业特征。“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的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己。”
早期上海电影就有浓厚的商业意识,比如成立电影公司、启用明星制、展开成熟的影片宣传活动等。就影片宣传而言,当时,上海著名的报刊、杂志多有电影副刊或电影专栏。“《时报》《晨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各大报俱增办电影副刊”。电影报道也是上海著名杂志《良友画报》 《摄影画报》《时代画报》等的重要内容,长城画片公司、太平洋影片公司、友联影片公司和上海新民影片公司都是《良友画报》的主要广告客户。上海红楼电影都非常注重在报刊、杂志上为影片作宣传。比如,孔雀版《红楼梦》在该公司摄制的《孔雀东南飞》后,即广泛宣传其《红楼梦》拍摄意图:
于十月十七日登《申报》封面广告,宣布开始摄制《红楼梦》。十二月三日《孔雀东南飞》片成,……其中亦曾宣传孔雀公司正在进行摄制《红楼梦》。本年一月一日,本公司为孔雀东华戏院开幕事登《申报》封面广告,其中亦曾提及《红楼梦》已在进行摄制之中。数月以后,对于《红楼梦》剧本已有最后之改正,乃于三月十二十三日两日登申新两报封面广告聘请女演员,十九二十两日又登申新两报封面广告征求女学生加入表演。
当时上海还出现了大量专门的电影刊物。从1921年到1949年,上海共出版各类电影期刊207种。其中,1920年代出版的十几种电影“特刊”是此时期电影刊物的特殊品种,这些刊物都各自属于某家电影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作为刊物名。它们几乎都是一种办刊模式,即每当公司出品一部新片,就出刊一期,并标出“某某影片号”或“某某影片特刊”。
为了配合影片的播映,复旦版、孔雀版、周璇版《红楼梦》都专门发行了特刊。
复旦版为《复旦特刊·红楼梦再生缘合刊》,《红楼梦》内容占九成,主要涉及电影《红楼梦》的编创说明、演职员表、字幕等,沪上作家及其他文化界名人笔谈《红楼梦》影片及小说原著诸问题,《红楼梦》电影试映后有关报章所刊载的“评词”。《红楼梦特刊》文章的作者,除少量影片编创人员及新闻记者外,大多是沪上的文化名人,其中有些还是知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该刊共发行了两万册,这应当是个不小的数字,由此亦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如此制作精美、内容丰富、发行量大的影片特刊,即使与当代电影的平面媒体宣传比较,也毫不逊色。
孔雀版则为《红楼梦专号》,包括了该公司摄制的《孔雀东南飞》影片说明,但篇幅较少,主要是《红楼梦》内容。较之复旦版,孔雀版专号更是篇幅宏大,竟厚达100多页。其商业色彩也更为浓厚,封二即是一大幅惠民奶粉广告,封三为导演程树仁主编的《中华影业年鉴》广告,特刊后部分内容主要是美国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及其电影海报。电影特刊封面右上角打上“古装稗史香艳巨片”的宣传标语,右下角还印上英文名《The Red Chamber Dream》。针对复旦版的“本片是近代装,非老戏式之古装”的广告语,孔雀版针锋相对地刊出广告:“本片乃古装香艳巨片,非时装可比。”孔雀版《红楼梦专号》不但有演职员简介、 《红楼梦铜图十六幅》(剧照),还有《胡适红楼梦考证撮要》《红楼梦本事》《红楼梦字幕》《导演红楼梦之一番用心》《红楼梦评语一束》《红楼梦英文本事》,其中《导演红楼梦之一番用心》竟长达80页篇幅。而文后还有“尚有古装红楼梦批评多篇留下期登载”字样。从孔雀版专号可看出主创人员严肃认真的态度与影片的精美程度。
笔者所见的周璇版《红楼梦》宣传杂志有《华影新片特刊—— 〈红楼梦〉》与《红楼梦人物素描》。《华影新片特刊—— 〈红楼梦〉》封面为周璇扮演的林黛玉与袁美云扮演的贾宝玉,封二为各角色剧照及导演、演职员表,宣传广告大概是“钢铁阵容!煌煌巨制!”(前三字残缺,笔者从《光荣之页》中查阅后补上。)杂志内容分别介绍了《红楼梦》剧情与“剧旨”、红楼故事片段与剧照、“红楼花絮”“红楼梦处女镜头”“卜万苍现身说法”“摄影场上”等内容,还附有影片的全部对白以及歌曲《梨香曲》与《悲秋》《尾声》。特刊中还有“富丽堂皇古装稗官巨制” “耗资千万元,摄制近一年”的广告字眼。《红楼梦人物素描》有主要人物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袭人等的人物素描、解说词及剧照,次要人物焦大、焙茗、傻大姐等也有素描与解说词,有的也附有剧照。宣传册子中还有影片摄制中的“花花絮絮”、胡兰成对林黛玉的评价、《梨香曲》、剧情与剧旨等。
有学者认为从1925年到1927年,上海的电影期刊主要由电影公司特刊一统天下。复旦版与孔雀版特刊正出自此时。1944年周璇版也同样发行了电影特刊,而且还不只一期,只不过从形式上已与二十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此外,还有学者认为1920年代电影公司特刊整体上质量不高,选编上往往一味迎合小市民低级庸俗的趣味,有些庸俗不堪。笔者见到的这几份红楼特刊则完全不同,虽然也有一些商业广告与影片的商业宣传,但整体上学术性很高,这或许得益于《红楼梦》本身的高雅旨趣吧。
1949年后,在新的电影政策的指导与中央电影局的管理下,上海电影的地域色彩日益弱化。1951年摄制《红楼二尤》、1962版越剧《红楼梦》与1963版京剧《尤三姐》虽然仍有部分海派文化的遗影,但主要体现了新时期的文化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虽然出品过多版越剧电影《红楼梦》,但并无新的建树。上海与《红楼梦》的电影情缘,主要定格在民国的特定时空中。
注释:
① 参见梅兰芳:《我的电影生活》,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2页。
② 张振华:《海派电影文化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③ 《红楼梦影片开幕词》,《复旦特刊· 〈红楼梦〉〈再生缘〉合刊》,复旦影片公司1927年版,第2页。
④ 碧波:《红楼杂碎》,《复旦特刊· 〈红楼梦〉〈再生缘〉合刊》,复旦影片公司1927年版,第26页。
⑤ 郑逸梅:《观红楼梦试片记》,《复旦特刊· 〈红楼梦〉〈再生缘〉合刊》,复旦影片公司1927年版,第49页。
⑥ 范佩萸:《红楼梦小说与电影不同之点》,《复旦特刊· 〈红楼梦〉〈再生缘〉合刊》,复旦影片公司1927年版,第41页。
⑦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7页。
⑧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⑨ 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转引自《文学界 (专辑版)》,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