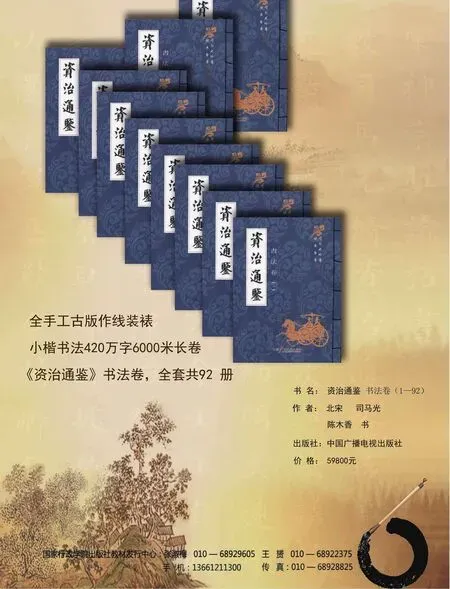大将军的严父情怀儿子眼中的粟裕大将
■ 本刊记者 熊 芳
大将军的严父情怀儿子眼中的粟裕大将
■ 本刊记者 熊 芳
在人民军队灿若星河的将军方阵中,粟裕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有人这样概括他一生的功绩:“一心为民,两让司令,三次先遣,四过长江,五总前委,六次负伤,七战七捷,八省征尘,九死一生,十大将之首。”然而他却说:“我只是沧海一粟啊!”在战争年代,粟裕统率千军万马,以赫赫战功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为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本刊记者专门来到京西八大处,与粟裕长子、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粟戎生中将,共同追忆开国第一大将的传奇人生和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
言传身教做严师
1942年粟戎生在战火硝烟中降生,故取名戎生。
粟戎生对记者回忆说,枪林弹雨之中,爸爸没有奢望能见到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同时也寄希望于后代。因此,他引导我一步步走上了戎马生涯。
在粟戎生的记忆中,粟裕喜欢保存四样东西:枪、地图、指北针和望远镜。比如,一个非常旧陋的硬壳指北针,只比五分硬币略大一些,他也当宝贝收着。在这四样东西里,粟裕最喜欢的是枪和地图。粟戎生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在部队制作了一种用“的确良”布料印制的华北地区交通图,很精致耐用。我多领了一张给他,他特别高兴,看了又看,很珍惜地收进他的书柜。在粟裕的办公室和住房内,最主要的装饰品就是地图。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他就挂那里的地图。粟戎生动情地说,爸爸爱枪,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情感寄托,也反映他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时刻注视着现代战争和国家的安危。
粟裕共育有三个子女,长子粟戎生、次子粟寒生、女儿粟惠宁。他将三个子女都送到部队锻炼,用最典型的军人教育方式——吃苦、耐劳、严肃、顽强、勇敢训练他们,这是粟裕教子的十字秘笈。“爸爸常常这样鼓励我们说,年轻人不要贪恋小家庭,只想着坐机关。”就是这样,粟裕利用做父亲的“特权”,坚持把子女下放到最艰苦的环境中接受锻炼。
粟戎生回忆说,从他幼年开始,到当学员、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在不同时期他都铭记着父亲对他的严格要求。从哈军工毕业之后,他先是被分配到抗美援越的云南一线,从战士到排长一干就是四年,上千次的战斗警报,频繁地移防,绝大多数时间他都睡在帐篷里,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家里依然摆放着军用帐篷的原因。
艰苦的军旅岁月把粟戎生磨炼成一名具有坚毅性格的军人。他当了连长之后,父亲又教他如何带兵作战,包括如何研究地形地图这些事情,父亲都会一招一式地指点他,把自己在长年战争生涯中的宝贵作战经验传授给儿子,父子之间的谈话也总是离不开军事话题。
在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中,粟戎生常常把爸爸的教诲记在心中,当作座右铭。爸爸的一言一行,既风趣,又有军人特有的气质。他曾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他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要熬很长时间,要耐受。当兵要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紧张。”过去他看到我们动作磨蹭,就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不行。”他特别不满意我们边说话,边慢慢腾腾地吃饭。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武昌叶挺部队教导队,要求非常严,连吃饭都很紧张,一个个都是狼吞虎咽。教导队长官有时故意在饭中掺头发和沙子,你要挑拣就吃不饱。”他还说过:“在战争环境中,各种条件很艰苦,从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要能适应战争条件。平时就要吃苦。”说到这,他动情地讲到:南昌起义、潮汕失败、转战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后来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有时好几天吃不上什么东西。打了土豪,才吃顿饱饭。有东西就吃,没吃的,行军打仗也能熬上几天。负荷很重,全靠两条腿,有时一天跑一百多里路,还连续打几仗。行装很简单,每人一床夹被,冬天在里面塞上稻草睡觉,出发时把稻草倒掉,行军中下雨,就披在身上当雨衣。他要求我在部队的东西要少,要符合战备要求,一举一动都要有高度的战斗警惕性。
当兵后,有一次我休假期间睡觉时衣服鞋子放置很乱,父亲看到后就严肃地批评我,说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速度整装上岗,就是在放假期间也要这样。他自己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晚,先把衣服叠得便于穿着,而后衣服鞋袜都放在固定的地方。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兵,他很注意自己的军人姿态。按照军人着装规定,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裤腰里。只要穿上军装就扣好风纪扣,从没敞开过。就是在爸爸病重期间,当时他已经偏瘫,别人协助他穿衣服,他仍然这样要求。
爸爸平常在衣、食、住、行、着装打扮上严格要求,并不是他僵化古板,那是一个老军人在长期战斗生活中养成的个性,是他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完美的统一。爸爸的一举一动,既对我是严师、楷模,又对每一个人是良师。
艰苦朴素立表率
在粟戎生看来,父亲虽然有赫赫战功,但他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严于律己,低调做人。
1949年7月的一天,第三野战军机关由上海移防到了南京。粟裕奉中央命令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为了工作方便,组织上决定,凡担任地方工作的同志,每人做套便衣。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对爸爸说:“你可是百万人口的一市之长,应该做套毛料便衣。”他一听,立即说道:“不行,为什么要做毛料的呢?做套布的不行吗?刚进城就讲究穿戴不好嘛!要脱离群众的。人民群众不是看我这个市长衣服穿得好不好,而是看我工作做得好不好,看我是不是为他们服务。请你们还是从工作上关心我吧。”他谢绝了后勤部长的好意,并对大家讲,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保持的品德。
根据我爸爸的意思,给他做了一件蓝灰卡其布的便衣。他就穿着这套中山装同南京人民见面了,显得朴素大方,平易近人。后来,他到市委办公,到工厂、学校、商店调查研究,都穿着这套便衣,一直穿到北京,变成了灰白色,快要磨透了,还是舍不得丢掉。他的衬衣则要穿到打补丁,汗衫破得像鱼网,才换一下。
解放后发给他一双军用短靴,他很喜爱,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的部队要现代化了,着装应该改进,体现出军人的威严,穿靴子有好处,一是精神,二是保护脚趾。”他日常都穿这双军用皮靴,晚上公务员想帮他擦擦,他不同意,都是自己用布把皮靴擦拭得干干净净。七八年过去了,皮靴换了两次底,皮面裂口了,也缝补过好几个地方,两边松紧口坏了好几次。穿到这种程度,仍擦得干干净净。换装时,想给他领双新的,他也不肯。工作人员对他说:“首长,你干吗那样节省?”他说:“你这个小鬼,我穿得衣冠楚楚,干部、战士就会敬而远之的。更何况节俭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本色。”
在外出期间,每当碰到摄影记者,粟裕总是躲在后面。他自己不抽烟,但有干部战士到他宿舍时,他总要请他们抽烟喝茶,不抽烟的吃糖果,到了开饭的时候就留下一起用餐。下部队或去其他单位时,被哨兵拦住了,就自己下车,通报姓名和工作单位,还怕战士听不懂湖南话,常常摘下军帽,把帽子里的名字亮给战士看。他时刻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应该有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这一品质也时刻激励着我们这些子女。
他当总参谋长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车。他说:“为什么要换呢?官做大了就应该坐更好的车吗?这是什么思想?”车子没有换成,还挨了一顿批。为了体验生活,了解民情,粟裕还常常乘公共汽车或坐三轮车到农贸市场了解行情、民意。工作人员提醒他说,这样做太不安全了!他说:“那有什么关系?人家外国总理夹起公文包坐公共汽车上班。怎么我们就不行,难道我们的身体就比人家宝贵?”
战友情怀树威望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好兵?这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军事科学和管理科学。针对如何带好兵的问题,粟戎生回忆说,爸爸教育我要熟悉战士,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让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要关心战士,要完全信任他们,他们才能完全信任你。做到这点,最重要的,是要身先士卒,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战士们也会坚信你,和你一道杀开出路。
记得爸爸曾给我们讲过在井冈山时期的一个故事。那时,红军初创,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比起国民党军队的物质待遇,要差很多。但是,国民党军队逃兵很多,而红军却很巩固,战斗力也很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废止肉刑,建立了三大民主,红军部队像个革命大家庭,干部战士之间情同手足。不仅干部关心战士,战士也关心干部。有时,战士分到一点“伙食尾子”,就自动地把钱凑起来打顿“牙祭”。当时,爸爸任连队的指导员,战士打“牙祭”的时候,都想着他,一定要拉他去和战士们一块儿吃。吃什么呢?因为钱太少,买不起什么好东西,也就是买一些油炸豆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有说有笑,十分欢快,什么环境的艰苦、斗争的残酷,全都不在话下。爸爸在讲述往事时,目光闪烁,神情活跃,完全沉浸在团结友爱的战友感情之中。
爸爸常说:打仗就要死人,我们的战士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作为指挥员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在作战的重要时刻,为了夺取胜利,我们是不怕牺牲的,但不应该的牺牲,哪怕是一个人,也要避免。爸爸的这番话,使我很受教育。常听到一些叔叔们谈起,在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地方,爸爸都要亲自勘察地形、布置检查岗哨警戒、作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他带领下的部队,在突来的紧急情况下,很少受到损失。特别是他亲自选定驻地、亲自布置警戒的首脑机关和后方单位,在敌人千方百计想偷袭的情况下,没有一次遭受损失。这不仅反映了爸爸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其实更反映了爸爸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对每个战士的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感情。
全国解放后,爸爸对战士们一直都怀着特殊的感情,每逢佳节,都要给值班的警卫战士们送点食物或请吃一顿饭,以示慰问。如果节日正在外地,他从不忘记打个长途电话回家,交代在家的同志,去买几斤肉给警卫班同志送去,让他们加个菜,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有了爸爸的榜样,我努力按战斗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习惯后,再苦再紧张也不觉得枯燥、乏味。后来,我向他汇报在云南某地空导弹部队当兵四年的体会,爸爸很满意,说:“当兵嘛,就需要这样的艰苦锻炼。”
爸爸常对我说:“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逐级取得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爸爸让我从小进住宿学校,又经过五年的军事院校生活,我已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我当了一年战士,以后又当班长、技师、排长。在这期间,经历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一千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
只要可能,父亲也尽力让我到第一线去,踏着先烈的血迹继续战斗。这我理解,也欣然前往。从南陲到北疆,各方面条件更加艰苦。但爸爸那首深沉、激昂的《老兵乐》响在我耳边:“半世生涯戎马间,征骑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击鼓,枪弹呼啸若琴弹。”这铿锵的诗句,是爸爸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是鼓励我驰骋战场,杀敌立功,为国尽忠的战鼓。诗,对于诗人来说,是感情长河的流溢。诗对爸爸来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他的肝胆情怀。后来我才理解,爸爸这样做不仅仅是对我的严格要求,而且以此作为对他自己的极大安慰。
采访即将结束,粟戎生将军动情地对记者说,如果没有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高尚的革命风范、优秀的政治品德,我爸爸是很难做到这样的。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老军人身上那种在曲折经历中不断升华的高度的责任感。他不仅关心我个人的成长,更关注我们的军队能在和平时期继承发扬光荣传统,永远保持我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献给第一线的交警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