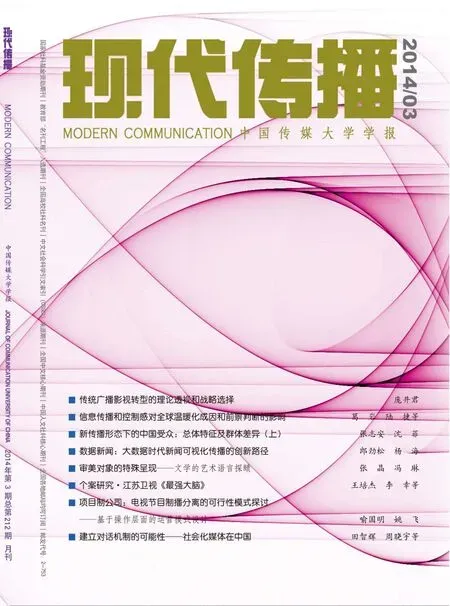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总体特征及群体差异(上)
■ 张志安 沈菲
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总体特征及群体差异(上)
■ 张志安 沈菲
本文依据来自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37279个样本的统计分析,试图整体描绘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特征。文章首先简要描述了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受众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状况、媒体认知和评价;继而,对城镇和农村受众、省市县受众、不同地区受众、不同年龄受众、不同性别受众、不同教育程度受众、不同收入受众的群体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受众的整体特征包括:媒体选择以电视为主,网络、报纸、广播、杂志为辅;使用动机以信息娱乐为主,创造表达意愿不强;期待媒体维护正义、解决问题,信任传统媒体多于网络媒体。此外,我国受众媒体使用和认知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
媒体使用;媒体认知;总体特征;群体差异
受众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个体,是媒体生态的产物,受众的媒体接触行为以及对媒体的认知和态度是各种社会力量综合、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社会环境来讲,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城乡二元结构、行政级别主导的政治规律和自然地理环境差异造成了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等多种社会问题。
从媒体生态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视产业化和集团化改革,虽极大地增加了电视频道的数量、丰富了电视节目的类型,却主要倚靠各类娱乐节目吸引观众来赢取收视率,高质量的新闻和评论类节目并不多见;与此同时,报业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了都市报和精英报的兴起,吸引了大批有责任感的媒体人以舆论监督开民智、鼓民力,但相对严苛的管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闻媒体的话语空间和公共功能。21世纪初,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逐渐普及,拓宽了我国受众获取信息、人际交流和寻求娱乐的渠道,打破了以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为主的传统媒体生态圈。从门户网站到网络论坛,从博客到微博等社交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形式被部分消解,受众有机会参与到信息的采集、制作、发布和传播等过程中,互联网上的热门议题也经常反哺传统媒体,网络在国家与公众之间开拓了一片非官方性质的社会话语空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信息资源的多样性,培育了公共空间人际沟通的素养。
身处新媒体环境中的中国受众呈现出怎样的新特点?本文将从传统媒体使用状况、新媒体使用状况、媒体认知和评价以及不同群体受众的内部差异等角度入手,分析新传播形态下中国受众的最新特征。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大众传媒》的子课题——《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数据库。该调查由第三方调查公司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简称CSM媒介研究)于2010年7月15日到10月23日执行。样本目标总体为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所有城镇、农村家庭户中的18岁以上的常住人口。调查采取了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多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完成1110份问卷为目标。抽样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标样本总量为34410。按照这个抽样设计,CSM媒介研究结合其历年执行的经验,在抽样操作中对各地样本量作了上调,因此,实际完成问卷总量为37279。本次调查采用了访员入户面访的形式,完成一份问卷平均耗时约61分钟。这个计算排除了那些耗时记录低于20分钟或高于150分钟的样本(n=125,占总样本的0.3%)。该调研项目采用世界民意研究协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推荐的访问成功率的计算方式,计算得出成功率为:(1)省会城市为62%;(2)非省会城市各地为69%。
自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等在北京开展中国大陆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迄今,30多年时间里,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受众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和进步。我们搜集了过去30年一些较大规模的受众调查和研究发现,整理如下(详见表1):

表1 我国受众研究项目梳理①

(续表)
从调查主体来看,上述调查主要由新闻院校、新闻媒体和政府或企业机构以及从事电视收视率调查和观众分析的央视-索福瑞等负责实施。从调查特点来看,受众调查日趋频繁及系统化,抽样方式更加科学,并且近几年的受众调查对新媒体的关注逐步增强。不过,过去30年受众研究和调查存在三个不足之处:第一,上述调查大都以某一类媒体或某一家媒体为中心定义受众,或者考察某一相面或某一类型的受众,缺乏对受众的整合考察;第二,调查的基本目标是描述受托媒体的目标/可能受众(比如央视所展开的电视观众调查,核心关注还是央视的目标/可能观众),而非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形成对受众的理论概括或归纳;第三,多数调查集中在某一地域,或集中于受众的某一类行为。也就是说,过往的受众研究仍然是片断式的,缺乏对于受众的整合性理解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经验研究,无法形成对全国受众的描述。基于新传媒技术的环境,《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调查试图以“受众-用户-公众整合”为视角进行全国受众调查和研究。因此,基于该项目数据的分析,使本调查报告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此报告的样本目标总体为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所有城镇、农村家庭户中的18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覆盖范围非常广。其次,此报告调查的内容包括受众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状况、媒体认知及评价,并进行不同类型的群体差异比较,因此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新传播形态下中国受众的总体特征和群体差异。我们将首先描述新媒体环境下中国受众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使用状况、媒体认知和评价。继而,对城镇和农村受众、省市县受众、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受众、不同年龄受众、不同性别受众、不同教育程度受众、不同收入受众的群体差异进行比较。最后,就新传播形态下中国受众的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性分析。
一、传统媒体使用状况
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认为大众媒体的普及是区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重要依据②。传统社会个体依赖于家庭成员间的沟通获取信息,眼界局限于自身周遭的环境;通过接触大众媒体,个人能够了解本地以外的人和事,培养“移情作用”,接触多元价值观,摆脱传统的束缚,导致社会整体趋于“现代”。尽管勒纳的现代化学说带有浓烈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并简单地将传统与现代对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社会的大众传播技术与媒体使用行为,蕴含和体现着大众偏好、信息流动、政治格局等方方面面。
我们试图从硬件设备拥有和媒体接触两个维度切入,考察中国受众传统媒体的使用状况,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四点主要发现:
第一,从硬件设备看,电视接近全面普及,全国平均每户拥有电视机1.35台,没有电视机的家庭仅为1.9%;而收音机的拥有率约平均每户0.35台,远远低于电视机。第二,我国受众当下接触四大传统媒体频率的排序依次为:电视(每周平均6.29天)、报纸(每周平均1.06天)、广播(每周平均0.77天)和杂志(每月平均1.07天)。第三,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来看,我国受众接触传统媒体的两大主要动机是获取新闻(尤其是本地新闻)和寻求娱乐休闲。第四,就媒体市场而言,电视与杂志的市场份额相对集中,但广播和报纸地域性较强,市场份额分散。综上,我国当下的传统媒体生态可大致概括为:1.电视继续保持强势;2.报业和平面阅读快速萎靡;3.广播逐渐衰落和杂志的休闲生活化。考虑到绝大多数受众对本地新闻和娱乐内容的关注,在市场化大潮下谋求生存的传统媒体,其对娱乐功能的日益强化似乎会成大势所趋。
二、新媒体使用状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媒体生态的原有秩序和信息传播模式,重塑了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的特征。我国自1987年9月与外界建立网络互联、发出第一份跨国电子邮件迄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拨号上网、宽带上网到无线上网的技术转变。截止2013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③,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同样是1987年,我国内地第一个模拟移动电话通信网络在广州市开通。从模拟到数字到3G和4G网络,移动电话用户在2013年1月已达11.22亿④,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⑤,约占手机用户的34.6%。而到2013年年底,手机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亿,手机已经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我国受众如何以及为何使用新媒体?关于受众使用新媒体的频率、场所和动机以及新媒体使用与日常生活(如网络交往行为)的关系,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以下五点主要发现:
第一,2010年,全国受众平均每周的上网天数为1.48天(非网民计为0天)。活跃网民的比率约在27%左右,其中有17%的人口每周7天都会使用互联网。平均而言,活跃网民每天平均花2.92小时上网。
第二,就具体网络使用来看,频率最高的行为是“使用QQ、MSN、Skype等聊天工具”“浏览新闻”“使用搜索引擎”“在线收听、观看或下载各类视频音频”和“网上玩游戏”,频率最低的行为是“使用翻墙软件”和“制作博客或上传视频、音频”。
第三,网民在网上经常交往的对象首先是“同事或同学”和“原本就认识的熟人、朋友”;其次是“家人或亲戚”;与“从未见过面的网友”在网上交流的频率介于“极少”和“较少”之间。
第四,网络使用动机排名靠前的选项依次是:“了解报刊、电视、电台上看不到的话题和观点”“获得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内幕信息”“保持自己的社交圈”;排名最后的两个选项是“结交不同背景的人”“针对各种现象、问题发表评论或参与讨论”。
第五,约有72.5%⑥的受众拥有手机,在手机的各项功能中,使用最频繁功能是:“接听和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彩信”“使用实用工具”(如GPS、查字典、使用计算器、设置闹钟等)和“娱乐”(如拍照、摄像、听音乐、游戏等),使用手机进行上网互联的频率并不高。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网络的开放性是其最具生命力的特征之一⑦。新媒体拓宽了受众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渠道,打破了既有的传统媒体生态。如果将使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综合比较的话,我国受众当下接触媒体频率的排序依次为:电视(每周平均6.29天)、互联网(每周1.48天)、报纸(每周平均1.06天)、广播(每周平均0.77天)和杂志(每月平均1.07天)。可见,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已经超越了除电视外的所有传统媒体。
网民对于互联网可以帮助“了解报刊、电视、电台上看不到的话题和观点”和“获得一些平常不容易看到的内幕信息”等看法的强烈认同,直接反映了互联网信息的流通较传统媒体相比更自由的现状。不过,互联网对公民的潜在“赋权”作用也受到社会和文化力量的一定牵制。首先,我国虽然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但互联网的使用率和渗透率远不及电视,平均每周接触频率只比报纸稍高一些;而手机依然是通讯工具,移动互联网功能的使用率还比较低。其次,受众对“接收信息”和“休闲娱乐”类功能的使用频率远远大于“创造”与“表达”类的使用。调查发现,我国网民使用互联网最不频繁的活动是“制作博客或上传视频、音频”,使用互联网的动机排名最后的是“针对各种现象、问题发表评论或参与讨论”。最后,互联网的技术特征打破了地域限制,能让陌生人通过网络沟通,增强个体之间的联系,形成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也就是社会学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所说的社会资本。可是,对我国绝大多数网民来说,在网上主要跟熟人交往,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巩固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作用。相比虚拟的网络世界和陌生的网友,网民更在意的是现实中的亲朋好友和家庭。
综上可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开拓了信息获取、娱乐休闲、言论表达和个体交往的空间与方式,但就当下中国网民而言,新媒体使用的信息和娱乐功能,远远大于言论表达和个体交往的功能。
三、媒体认知与评价
媒体政治经济学家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梅铎(Graham Murdock)⑧在论述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时强调,现代社会媒体机构所生产的是“特殊的产品”,这种产品能够极大地影响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世界。因此,媒体与其消费者(即受众)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社会信息的流动和媒体产品的特征:一方面,受众对媒体产品有一种期待,甚至认为媒体有不可懈怠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受众自身的素质与涵养、偏好与品味间接影响着媒体产品的生产。
关于受众对媒体表现的评价以及媒体素养(包括受众对媒体可信度的评价、受众对媒体功能的认知以及接触新闻报道时所采取的策略),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以下四点主要发现:
第一,全国受众对不同媒体可信度的评价(1-10分量表)从高到低分别为:电视(7.50)、报纸(6.62)、广播(6.37)、网络(5.47)和杂志(5.39)。受众对不同地域的新闻,即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的可信度评价比较接近,无明显的大幅度差异,均值都在7.7左右。但是,受众普遍认为国内媒体的可信度要高于海外媒体(6.66),其中,中央级媒体的可信度最高(8.16),其次是本地媒体(7.23)。就消息源的可信度来看,受众认为专家学者、记者、编辑、主持人的可信度最高(均为7.17),其次是党政官员(6.68)、普通百姓(6.55)和民间评论人士(6.21)。
第二,受众认为媒体最重要功能(1-5分量表)的前五项分别是:“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4.59)、“替普通老百姓说话”(4.58)、“主持正义,维护公共利益”(4.51)、“及时准确地提供消息”(4.48)、“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4.46),而“提供娱乐”(3.98)位居最末。
第三,受众认为传统媒体在“及时准确地提供消息”“传播新知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替普通老百姓说话”“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主持正义,维护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互联网。同时,他们认为,互联网在“批评监督政府和官员”“批评监督商业机构和商人”“反映各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提供娱乐”等方面的表现则要优于传统媒体。
第四,受众在接触新闻报道时,比较倾向于“和周围的人讨论某个新闻报道的内容”。相对较少采取的行动包括“验证新闻报道”“比较同题报道”和“挖掘新闻隐含意义”。
综上可见,舆论监督、为百姓解决问题和维护公义被受众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体功能,而且受众通常认为媒体的行政级别越高,可信度也就越强。从新旧媒体可信度的对比来看,虽然互联网用户从2005到2011差不多翻了四倍,但民众对于网络的可信度评价并未显著提高,这可能与“网络谣言”“网络水军”和“网络公关”等现象有关。不过,互联网在批评监督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传统媒体。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处理以人际交流为主要形式,接触新闻后的分享意愿相对强烈。此外,尽管受众有判断新闻是否真实的主动意识,但采取深度的验证、比较和挖掘隐含意义的受众则不多。
本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和大众传媒》(项目编号:211XK03)的研究成果。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感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硕士生罗媚协助整理。部分内容参见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当代传播》,2001年第1期;中国记协新闻调研中心:《媒体信息接收率与有效性》,《新闻记者》,2003年第2期;崔保国、王世蓉:《中日两国青年媒体使用现状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7年第10期等。
② Daniel Lerner(1964).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Glencoe:Free Press.
③ 数据来源:《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1/P020140116395418429515.pdf。
④ 数据来源:《2013年1月通信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47/15215231.html。
⑤ 数据来源:《中国手机网民上网行为研究报告》,https://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ydhlwbg/201211/P020121116518463145828.pdf。
⑥ 本研究的手机普及率数据,与国家工信部的《2011年11月通信业主要主表完成情况》高度吻合,详见: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47/14394809.html。该报告指出,2011年移动电话用户合计97533.5万户,除以13.4亿的人口,手机普及率在72.8%左右。同时,《人民网》在2011年12月27日的新闻中提到“2011年我国电话普及率94部/百人,手机73部/百人”,见http://tc.people.com.cn/GB/16731256.html。
⑦ Castells,M(2001).The Internet Galaxy: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Business,and Socie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⑧ Golding,P.&Murdock,G.(2000).Culture,Communications,and Political Economy.In James Curran&Michael Gurevitch(Eds).Mass Media and Society.NY:Edward Arnold,pp.70-92.
(作者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菲系香港城市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