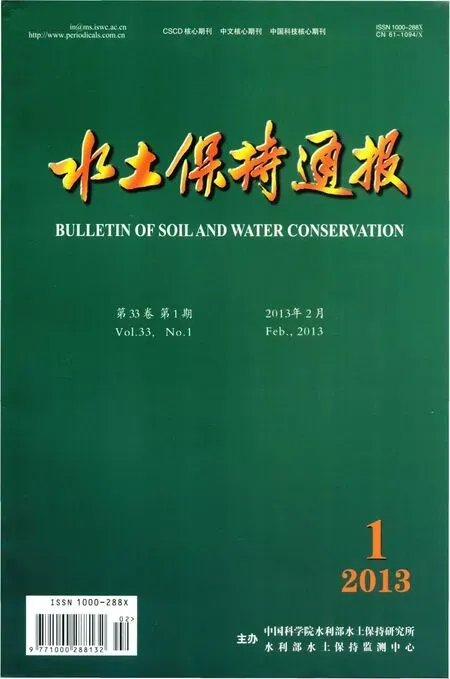武威市绿洲区耕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估
金淑婷,石培基,李 博,潘竟虎,魏 伟
(西北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渐增加,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问题的出现,众多学者日益意识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是人类社会不可替代的物质财富,但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数量和质量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来满足更多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已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2]。目前,专家学者对耕地资源集约利用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基于单个区域耕地集约利用潜力研究[3],耕地集约利用理论和标准研究[4-5],耕地集约利用驱动力研究[6],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规律研究[7],耕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研究[8]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耕地集约利用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大都是从单一耕地要素出发研究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本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把实际应用中从单一耕地要素来研究耕地集约度转化为现实可以接受的、考虑到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的持续性及人的主观支付意愿的综合耕地集约度,并以武威市为例,为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进一步在资源合理配置中的应用提供途径。包括:(1)寻求在实际应用中从单一耕地本身角度出发,能够反映区域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估算方法;(2)提出把单一以耕地为主的集约度转换为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和耕地生产利用持续性的现实集约度的综合估算方法。
1 研究区概况
武威绿洲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段,南依祁连山,北靠内蒙古,东南与兰州市、白银市接壤,西北和金昌、张掖毗邻,地理坐标为 36°29′—39°27′N,101°49′—104°43′E,海拔1 367~3 045m,地处黄土、蒙新、青藏3大高原交汇地带,地形复杂,南高北低。境内有灌溉绿洲、荒漠、高山草地、祁连山天然水源涵养林带及沙漠、浅山地带,形成山地—绿洲—沙漠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景观生态系统。总面积33 238km2,其中耕地面积1.88×105hm2,草地面积2.37×106hm2,可利用草地面积1.62×106hm2。境内有大小河流8条,年均径流量1.43×109m3,年日照时数在2 200~3 030h,年均气温7.8℃,无霜期85~165d,年均降水量60~610mm,年蒸发量1 400~3 040mm,是典型的内陆型干旱气候。武威市现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3县1区,其中天祝位于石羊河流域上游,凉州、古浪位于中游,民勤位于下游,共占石羊河流域面积的72.92%。2009年常住人口191.83万人,聚居汉、藏、回、蒙等38个民族。近年来,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的不断扩张、土地沙漠化加剧等原因,使得土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耕地,为了避免此矛盾继续加深,武威市的耕地集约利用势在必行。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武威市统计年鉴(2000—2010年)、武威60年(1949—2009年)、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公报(2001—2010年)以及实地调查资料。其中武威市2007,2008,2009年建设用地面积是在其1996—2006年建设用地面积基础上进行灰色预测而得到的。鉴于指标之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之间的屏蔽效应,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将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具体如式(1)所示:

式中:Xij′——指标的标准化值;Xij——第i项指标的第j项观测值;min(Xij)——第i项指标的第j项观测值中的最小值;max(Xij)——第i项指标的第j项观测值中的最大值。这样处理后的数据范围在0~1。
2.2 传统的耕地集约利用集约度估算模型
2.2.1 耕地集约利用PSR框架模型 PSR(pressures-state-responses)模型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部门发展的一项反映可持续发展机理的概念框架[9]。本文根据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以及PSR模型链式因果关系,结合武威绿洲的实际情况,对耕地的PSR因素实行界定,其三者在耕地集约利用中的关系见图1。

图1 耕地集约利用的PSR框架
2.2.2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权重的确定 根据对耕地集约利用的PSR因素分析界定,参考国内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结合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压力—状态—响应各部分内在链式结构,以耕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为准则和目标,并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统计的误差等因素,建立适合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PSR指标体系框架(表1)。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指标信度分析,结果表明,未标准化指标的Cronbach′s Aipha值仅有0.092,而标准化指标的Cronbach′s Aipha却达到0.710,根据学者DeVellis[10]对可信度的分类,可知该指标体系能够相当好地反映耕地集约利用情况。为了能够客观反映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情况,应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使评价真实、客观、科学。因此本文采用熵值法[11]对指标权重进行赋值(见表1)。
2.2.3 传统以耕地为主的耕地集约利用PSR评价模型的建立 对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响应系统3系统,分别从不同侧重面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3个系统具有较强的逻辑因果关系,为耕地集约利用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基于以上认识,根据耕地集约利用及PSR模型的特点,建立耕地集约利用三维模型,X轴表示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的压力系统,Y轴表示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的状态系统,Z轴表示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的响应系统,3者的共同作用决定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因此,耕地集约利用可以认为是直角坐标系下的一个矢量()对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响应系统3个矢量)的几何和。根据矢量运算法则

矢量模等于

式中:│F│——耕地集约利用的评价分值。基于矢量运算的基本法则而构建的平方根综合评价模型,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过程中一般通过构造乘算模型或者加算模型获取最后的评价结果,而平方根模型为一个矢量模型,可以反映受到多个不同方向力作用下评价对象的状态和结果[12]。由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高低受到多方面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利用矢量评价模型更能说明耕地集约利用的实际情况,具体计算见下式:

其中:

式中:F——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综合得分;fx,fy,fz——压力系统、状态系统、响应系统的综合得分;w1j,w2j,w3j——3个系统各指标的权重。

表1 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
2.3 耕地集约利用综合集约度估算方法
耕地集约利用首先是相对于传统的粗放用地模式而言的;其次,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最后,耕地集约利用是人的主观支付意愿的表现,因此必须考虑人的主观支付意愿。人的支付意愿是评估非市场物品和耕地集约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之一,是耕地集约利用评估的重要参数,与人对耕地集约利用认知程度有关,是动态变化的。某一区域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集约度是指在其相应的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各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以及特定人群对耕地集约利用支付意愿的综合测度。
2.3.1 耕地集约利用压力—状态—响应协调度分析
在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中,其核心不仅仅在于耕地集约利用各具体评价指标值及综合评价值的高低,还在于耕地集约利用中压力—状态—响应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评价,只有当其各部分影响因素高度协调,耕地集约利用才能表现出较高水平。协调度是度量系统或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14],就本研究而言,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协调度是指支持PSR评价系统的各子系统在区域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
本研究对于协调度计算公式借鉴刘承良等[15]的基于效益理论和平衡理论所构造的模型:

式中:HC——系统的协调度;P——压力系统的发展水平,即fx;S——状态系统的发展水平,即fy;R——响应系统的发展水平,即fz;k——调整系数,一般取k=6。
协调度等级划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协调度等级划分
2.3.2 耕地集约利用认知性分析 耕地集约利用认知系数是衡量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认知水平,即人对耕地集约利用支付意愿的标准系数。皮尔生长曲线模型[16]是用来反映因变量P随时间t变化趋势的模型,人对耕地集约利用支付意愿的特点也反映了相似的动态过程,即处于较低发展阶段时,人很难对耕地集约利用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对耕地的支付意愿就比较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对耕地集约利用有了新的认知,进而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支付意愿也随之提高;而后继续发展,耕地集约利用趋于饱和。因此,利用简化的皮尔生长曲线模型来描述这一特点,皮尔生长曲线模型公式为:

式中:It——事物发展特性的参数,即当前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认识程度;L——It的最大化(L=1);a,b——常数,通常取值1;e——自然对数;t——时间。曲线拐点为t=ln(a/b),这时It=0.5L,曲线对拐点对称。
把代表发展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的倒数与发展阶段相对应起来得:

式中:Ent——第t年的恩格尔系数,即农村与城镇第t年的加权恩格尔系数。
2.3.3 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集约度评价模型 根据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可知,耕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而这种持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主观认知水平;(2)耕地集约利用内部各种因素的协调性。只有当人对耕地集约利用有较高的认识以及内部各因素相互协调发展,耕地集约利用才会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在对武威绿洲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时采用综合集约度,即:

式中:φt——t阶段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F——t阶段传统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综合得分;It——t阶段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认知程度。根据式(8)计算得到的综合指数,耕地集约度可划分为10个等级(表3)。

表3 集约度等级划分
3 结果与分析
3.1 协调度分析
利用式(5)得出2000—2009年武威市耕地利用的压力—状态—响应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度指数和等级归类(表4)。
由表4可知,协调度指数表现出波动性,变幅在0.022 0~0.814 1,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1个阶段2000—2003年,协调度呈波动趋势。武威市地处内陆干旱区,气候干燥,降水量少,人口密度大,再加上耕地利用过程中对耕地的保护力度不够,耕地肥力严重流失和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本已脆弱的耕地资源不堪重负,而此阶段由于人们在耕地利用过程中对响应措施的投入处于一种徘徊期,从而使耕地利用协调度呈现波动。第2阶段2004—2007年,协调度基本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伴随着2004年中国加大对农产品和耕地持续保护力度,实行农业税减免措施,武威市作为农业大市,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在耕地利用过程中的响应措施加大,耕地压力趋于平稳,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第3阶段2008—2009年,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此阶段由于中国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刺激农民对耕地投入的增加,加之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耕地生产利用协调度急剧下降。总体上说,武威市耕地利用过程中压力—状态—响应协调度处于不理想的波动阶段。

表4 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PSR复合系统协调度
3.2 认知水平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口总数采用综合加权平均法[16]来确定Ent(表5),结果显示武威市综合恩格尔系数(Ent)浮动在41.50~36.49。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制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武威市2000—2009年总体上处于小康阶段,除2005—2006年陡然下降外,基本上表现出比较平稳的发展趋势。
通过分析发现武威市是以农业人口为主,且通过计算得出2009年农村人口对Ent的贡献率占到58%。由于2006年农业生产资料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收入相对于食品消费出现大幅度增加,导致出现Ent陡然下降的趋势。通过利用式(6)计算武威市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认知水平,发现农业收入的提高会极大刺激农民去重视农业生产,从而提高人对耕地集约利用的支付意愿。

表5 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认知系数
3.3 综合集约度测算
利用式(8)得出武威市2000—2009年耕地利用动态集约度等级归类(表6)。从表6可以看出,与传统静态集约度相比,武威市动态集约度呈现出与协调度相类似的波动趋势,变幅在0.121 6~0.500 3,其最高值和最低值与协调度吻合,出现在2007年和2003年,而传统集约度却表现出随时间序列不断提高的状况,其最高值0.373 7出现在2009年。原因在于:综合集约度考虑到持续性和人的支付意愿,2007年耕地集约利用压力—状态—响应3系统的协调性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反观2009年,虽然状态系统和响应系统分别达到最高值,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压力系统不断减小的趋势以及耕地利用的持续性和人的认知水平,因此造成耕地传统集约度提高,综合集约度反而下降。从总体上讲,不论是传统集约利用还是综合集约利用都表明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表6 武威市耕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
4 结论
(1)从传统耕地集约利用指数来看,2000—2009年武威市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虽有些波动,但总体上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而反观综合耕地集约利用指数,却呈现出巨大的波动。虽然2004—2009年武威市的响应措施持续加强,耕地压力出现下降,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以及后期对农业的保障措施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可能将导致农民出现再一次撂荒潮,从而使武威市耕地面临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加,耕地集约利用又将长期处于粗放阶段。
(2)本文从人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观认知水平以及土地集约利用持续性的角度考虑,进一步探讨了对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水平的评价。与传统评价方法比较,本文所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更加偏重于耕地集约利用的持续性以及人的主观认知水平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保障。以武威市为例,其动态集约度最高水平是2007年,说明2000—2009年10a间,2007年的土地利用的抗风险能力较高,因而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而在不考虑人的主观因素及土地集约利用的持续性时,其土地利用集约度最高是2009年,此结论与武威绿洲耕地集约利用实际情况不相吻合。
(3)耕地集约利用是人们在对耕地进行生产过程中的一种行为表现,其水平的高低必然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以往的研究只注重耕地本身的研究,忽略了人的主观因素,不免有其局限性。本研究在借鉴以往传统PSR模型优点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人的主观因素和耕地集约利用过程中内部矛盾的协调性来建立新的耕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模型,不仅有助于决策者根据耕地利用过程中压力、状态、响应的表现结果采取相应措施,而且还有助于决策者协调其内部各种矛盾,从而实现耕地集约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4)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是一个已经兴起的、综合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当今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准确认识与评价耕地集约利用,已经是资源科学、土壤科学、经济科学、地理科学等所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综合评估方法仅是初步的探索。在实际评价过程中,本文注重耕地利用的可持续性与人对耕地认知的动态性,而忽略对自然因素的考虑,将所评价区域的耕地划分为同一等级,难免会与实际出现偏差。另外,本文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偏重于耕地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耕地的生态效益。因此,建立具有以土壤学、资源学、经济学、地理学等为基础的综合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模型仍需进一步研究。
[1]朱天明,杨桂山,万荣荣.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国内外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2009,29(6):977-983.
[2]孙男男,郑华伟,张兰,等.耕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1):90-94.
[3]刘巧芹,连季婷,黄艳梅,等.石家庄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1,27(2):61-64.
[4]吴泽斌,刘卫东,罗文斌,等.我国耕地保护的绩效评价及其省际差异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9,24(10):1785-1793.
[5]徐梦洁,葛向东,张永勤,等.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J].土壤学报,2001,38(3):275-284.
[6]赵宏波,宋戈,孙丽娜.河南省耕地集约利用的驱动力分析[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729-732.
[7]张琳,张凤荣,吕贻忠,等.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规律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08,41(12):4127-4133.
[8]刘玉,薛剑,潘瑜春.环渤海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分异研究[J].2012,33(1):86-89.
[9]朱一中,曹裕.基于PSR模型的广东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差异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8):1375-1380.
[10]DeVellis R F.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M].2版.魏勇刚,席仲恩,龙长权,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30-51.
[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387-398.
[12]班茂盛,方创琳,刘晓丽,等.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区土地利用绩效综合评价[J].地理学报,2008,63(2):175-184.
[13]冯浩,吴普特.黄土高原国家攻关试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分析与评价[J].水土保持通报,1998,18(6):54-57.
[14]王辉,郭玲玲,宋丽.辽宁省14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定量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4):463-470.
[15]刘承良,熊剑平,龚晓琴,等.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性评价[J].经济地理,2009,29(10):1650-1654.
[16]粟晓玲,康绍忠,佟玲.内陆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估算方法与应用:以甘肃省河西走廊石羊河流域为例[J].生态学报,2006,26(6):201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