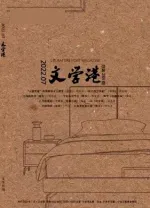母亲的牡蛎
戴巧珍
牡蛎在我们家乡西店叫蛎黄。这个软体生物内柔外刚,爱煞了世间人。我常拿它与母亲相比。
它的壳像一个放大了的指甲背,或者说像一面缩小了的蒲扇。拿一把尖利的蛎刀对准它的壳顶撬开了,它淡蓝色的肉体泛着银色的光芒,掬着一汪汁水,打着褶皱的裙边在水波里微微荡漾。用蛎刀把牡蛎的筋割断了,拿起蛎壳连水带肉往嘴里倾倒,一阵让舌尖打颤的鲜味在嘴里漾开来,冲击你身上的每个细胞,让人忍不住皱眉、啧嘴,深深地赞叹。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就有这样的细节描写:十八世纪高贵的法国妇女举止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除了美食,据说它还滋阴补阳,连《本草纲目》都载着。它的壳经火焙成灰,是绝好的砌墙材料,可与石灰媲美。
我们家就在海边,海涛声常常入了我的梦,海鸥常常立在我家的屋檐上。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农田承包到户之后,我们家也从队里承包了一些牡蛎养殖。可是,父亲一直病着,早把家里戳出了个花钱的大窟窿,仅靠这点收入远远不够。母亲打算扩大牡蛎养殖。这个决定让她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
母亲长相姣好,人称“白洋袜”,因为有一次她入田插秧,雪白的双腿让过路人误以为穿着白洋袜。没有出嫁之前,一直是外婆的掌上明珠。但她为了爱情,为了儿女,她毅然决然地变了。而牡蛎的生存能力酷似我母亲。据说,牡蛎产卵大都在大潮汛期间进行。海潮汹涌,牡蛎迎潮而上,勇敢地生儿育女。在合适的水温下受精卵不到一天即发育成幼虫,幼虫一直在海水里游呵游,二十天左右,柔软的幼虫居然长成了硬硬的外壳。这个时候,生存的智慧,促使它们找到附着的海边石头——涨潮时浸入水中,退潮时凸出水面。有海水浸润时,可尽情的吸收水中的浮生物等营养,与游过的鱼虾嬉戏欢闹;凸出水面时,可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观赏日月星辰花开花落。
牡蛎有多好的依靠呵,柔弱的母亲真想有一个依靠——她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牡蛎身上。
扩大生产就得花大价钱买蛎石。蛎石是从奉化买的。母亲舍不得租拖拉机的钱,就与病弱的父亲一趟一趟用手拉车运输。母亲在前面拉,父亲在后面推。早上三四点出发,回来往往已是后半夜了。这样的运输每年得持续半个月。可以这样说,每一块蛎石,都沾上了父母的心血汗水。
可与运蛎石相比,养牡蛎、收牡蛎的艰辛丝毫不逊色。
冬季收蛎时,每晚午夜刚过,天地滴水成冰,母亲搓了两个饭团子,与父亲一起撑着竹排出发去海里。他们要在天亮之前乘着涨潮把大海深处的蛎石运到海滩边上。然后顾不上喝口热水,一扁担一扁担地把蛎石运到蛎棚里堆成一座高山。而这些,其他妇女是不用做的。
之后,父亲可以回家休息,而母亲则要挑蛎肉。几年下来,母亲练成了一副好手艺。抓一块蛎石在条凳上,手起刀落,蛎壳打开,蛎肉就如跳水的运动员一样翻飞着落入旁边的蛎肉桶中。随着高山般的蛎石从母亲身体的一侧到另一侧,母亲一天的苦役方才告一段落。
蛎棚是简陋的稻草棚,冬日的海风常常像凄厉的饿鬼一般眦着嘹牙啸叫着扑向母亲。特别遭罪的是母亲的那双手。自从开始养蛎,她原先细嫩白皙的手就像一坨破肉一样,一个冬天滴滴嗒嗒地往下掉皮肉和血珠子。那些寒风却变本加厉地撕咬这些伤口和裸露的肌肤,母亲的手背会像发酵的馒头一样肿胀起来,变得清亮、透明,皮下的血管清晰可见,仿佛一碰即可化为一摊脓水。我经常为母亲的手流泪,为母亲的手祈祷。
可是母亲咬着牙坚持,一年一年的,我从没听她叫一声苦。每到收蛎卖蛎季节,母亲用肿胀得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头数着大小不一的票子,想到这些票子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它们可以让丈夫的医药费有了着落,孩子的学费无忧,买谷种、庄稼秧子的费用有了保障,她脸上就漾出欣慰的、让我终生难忘的笑容。
收成好时,一季有三五百元的收入,这笔钱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观的。可是,这些钱却没有完全利惠于我们。看看我们每年过年的菜:海鲜除了蛎肉,鱼虾极少上桌,猪鸡鸭肉虽是有的,却是一丁点。与村里一般人家比,十分的寒酸。家里孩子仅我们姐弟俩,可是从没见大人给过压岁钱。过年的新衣裳轮流做,得了今年就没有明年的。我穿小的衣裳有时候就直接让弟弟穿。
养牡蛎得来的钱呢?看着我们疑惑的目光,母亲说:“细水长流!现在把蛎石投放得多一些,到时候养蛎得来的钱就多了,我们家就有好日子过了!”母亲说这话时,两眼灼灼有光如火炬,父亲笑着点头,我和弟弟的心都被她的宏伟梦想点燃了,我们乖巧得不向母亲要钱买一根棒棒糖,却从此都不怕困难,年年把我们的学习奖状贴在墙上。
就这样,每年养蛎纯收入的三分之二,全买了蛎石。一年,二年,三年,四年,蛎石一年年增多,养蛎赚的钱越来越多,可我家的生活水平依然老样。
然而在一九九二年的冬天,积劳成疾的母亲躺到了病床上,而此时,我们家在海田上的蛎石数量达到了我们刚承包时的十倍,成为全村之最。这些沉重腥咸、大小不一、被母亲的手温一年年暖过、而今仍在盼望主人的石头是母亲历年的心血见证,但母亲却已没有力气再侍弄它们。它们像失去依靠的孩子一样先是流落到父亲的兄弟那里。后来,伯父也嫌养蛎太苦,把它们放弃了。母亲送宝贝一样转送他人,又几易其主。到九十年代中期,村里已无几人还从事这苦营生。忽有一日,村里剩下的铁杆蛎迷竟石破天惊地使用了废弃的汽车轮胎来养蛎。据说这种轮胎牡蛎不仅运输方便,产量还很高。
母亲心肝一样的光溜溜的石头最终沉没于大海,而母亲坎坷跌宕的养蛎生涯也永远地沉隐于岁月深处。
唯一让母亲欣慰的是:母亲与父亲彼此珍惜,用蛎石砌成了爱的堡垒;儿女成才,我与弟弟都学习成绩优秀,长大后各自有了幸福的事业和家庭。
选自《早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