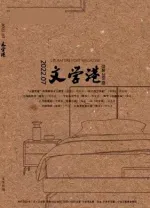匹马北方(组诗)
叶舟
抄 经
在苍茫的纸上,
掩好寺门
扶住花草 喂饱鸣禽;
然后,一个人端坐世上
闻墨听茶
饮经酌史。
风吹时,用一颗心
镇住纸角;
一杆笔,来自
终身积攒的苍苔——
有的花白
有的皲裂
仿佛一场走失良久的泪水;
墨是另一种奇迹,乌鸦带来的
翅影与污点
需要用秘密的诵念
将黑夜褪尽。
偶尔,打开窗牖,
一匹枣红马引首向西;
人世灿烂
市声沸腾
——而弧形的天空,仿若一卷
刚刚录毕的《心经》。
指 证
最深的一段河流,就在那儿;
在那儿,一段
最深的黄河
带着高原的烈日、滚石和神仙
匹马走过
形单影只;
黄河最深的一段,埋伏着
心事、爱和脚印
像一个人从失败中
站起;
最深的黄河的一段,比历史
警觉,
比时间迅疾,
比天空深沉;
万物花开的季节,在那儿
鳞甲烁闪
波光潋滟
一段百转千回的最深的河流
破冰怒醒,收拾残局;
黄河,最深的一段,就在那里,
深埋尊严
默然前行;
拐弯时,黄河碰见了我,
一怔,
就把最深的一段,留在了那里。
菩萨低眉
低眉的一刹,唯有豹子敬谢不敏,
一吐为快,道出雪线以及山顶上的一切;
那时,寺门外有人澡雪,
用一生的热情,浣洗一叶白桦树封皮;
不是经书,乃是一碗灯,
羔羊用浑身的脂肪,喊破了黎明;
夜色沉积,如果恰好有婴儿啼哭,
这繁复的来历一定不能究问;
磨坊保存着一支谣曲,父女俩相依为命,
粮食是陈年的,命运也不外如此;
鸣禽和鱼,来自敦煌与阳关以西,
马背上的事情,仿佛闪电之下的根须;
差不多吧,当石窟静谧,世事浇漓
这露水的早上,挂着一件仙鹤的蓑衣;
三里外,停着一只石鼓,此刻谁还在空虚,
谁就看不见,那菩萨低眉的一刹——
天梯山石窟
我知道,这一切并非没有原因。
带着草木上山
露水的早晨,一角湖水中
麇集着豹群、鹰部落、大象、佛陀
与油灯;
这么久了,丝绸之路上
土匪剪径
坏消息不断
一个僧侣暂无音讯;
我真的知道,这一切并非
没有原因——
中午时,我在山顶晒经,
一阵狂风,
令天空失色,字迹隐匿,
即便石窟内供养着今生今世,
一幅壁画
也难以诉说庄严和秘密;
傍晚,我在山下驻足,
等一个人前来
朝贡,点香;
可银河灿烂,繁星奔走
一种怀腹的伤感,开始
半夜鸡叫
马不停蹄。
——这一切,并非没有原因。
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草木闪避
月光凛冽
会有一尊象牙佛驱散鸟群
仰天沐浴;
黄昏垂降,适当的时候
去请教一把旧粮食
一挂马车,一枚始终不肯
堕落的橡树叶
去了解字母的沟回,伤口中
的天使;
这里的雪,有时候像冰
更可能是火;
傍晚拈香,适当的时候,千万
不要迷信木鱼,
也许它的黑板上,有一面坡地
金戈铁马
风吹草低;
清朝时,这里罂粟满地,熏香四溢
过了袁世凯的阶段
银元烂坑
举目无亲;适当的时候
一匹豹子前来议和,
左手高山,右手流水
沾染了天堂中的坏脾气,像一根
铁钉,需要榔头
去叮咛;
午夜,有一只碗继续空着
盛下泪水、哽咽
和四季
仿若世界上最小的心脏,白发横生
在适当的时候,
打翻油灯。
姿 势
我知道,敦煌
还在那里
趺坐;
——像一口倔强的青铜之钟
敛声不语
冥想天下。
夜半时,她偷偷起身
将油灯喂进石窟,
仙女们过剩,而象群和虎豹
坐在课堂上
将佛的语录逐页背诵;
黎明前,一些湿润的壁画
会破土萌芽;
门前的绳子上,小风倾诉
一些透明的露珠
充满生死。
我知道,整个白天
母亲仍在那里
趺坐;
——她中风初愈,像一尊菩萨
心肠火热
化险为夷。
下山时,与一位红衣僧侣
诵经后,我和你
吹灭油灯
推门而出;
一刹那,碰上了今年的
头一场暴风雪。
其实,佛陀也坐在山顶,
扪心问天;
读着这一本比眼泪烫、比梅花绚烂的
毛边经书;
桑烟缭绕,好像几个披头散发
的观音
悲深愿重,骑在天上;
你开始劈柴,
身体内的野兽,摧枯拉朽
板斧挥舞;
——草原上的穷亲戚们饥寒难料
音讯阻绝;
我在剖开的一堆圆木中间,看见了
布施的火种。
是的!我这就走了,连夜
替你捎柴下山,
摸回人间
道声平安。
填 表
好吧,就用这一份表格
归纳自己,
A4 单页 独此一份
复印无效,
将短暂的生平与热情
整理存档
告慰历史。
姓名 籍贯 性别
年龄 二寸免冠彩照 学历
任职资格 职称 工种 兼任岗位
聘用时间 工龄 上一年度考核等次
失误、失职及惩处记载 获奖励情况
著作 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
创造发明及成果 继续教育起止
本人签名 登记人签字
百分比 定量计分 满分值
凡此种种
我都耳熟能详,
将自己切割 瓦解 支离
化整为零
肥瘦搭配
分摊于不同的区间,笑若春风
像一本塑封的
情人节菜单。
只是,在“信仰”这一窗口
我埋下头去——
拭尘
擦火
点灯,
双手供养给头顶的天空
内心洞明,只字不语。
天山上的大象
这个白色巨人:它是经书里跑出来的
手执横笛,骑跃山梁
带着秘密的温度,以及
优雅的使命——
它吹奏,或者宣谕
仿佛自己的脊背上,坐着一位热泪长流的
唐朝僧侣。
它静穆,含着野心与隐忍
在苍凉的北方
刀枪入库,塑身为窟
一再拾取了战栗、美和天空的密语。
它低首,在接近终章的一刻
敛下鲜花、马灯、颂唱和奶桶
广洒佛雨
知人善用。
在迁徙的路上,一匹引颈向西的大象
匿名逐来,矗立山巅。
那个露水的早上,我史诗般的哈萨克阿妈
背起毡帐
踮脚,抚了抚天山的额顶。
让我说
菩萨就坐在那里——
坐在白桦林
葡萄枝头
一条溪水的左岸
甚至一匹失家的羊尾巴上;
云鬓发白
系着旧围裙;
有时候是母亲,有时是妻子
总之
像我的菩萨妹妹!
在天山深处伐木,我对这一派苍凉暮色知足常乐;
对自己
也肃然起敬。
——神奇的“阿拉丁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