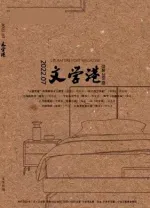借酒杯,浇块垒
郑炀和
徐海蛟的《见字如晤》是一本以历史人物为审美对象的散文集,这些人物都是有才识、有性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不同凡庸之辈,但他们的命运又一律崎岖和悲剧。作者说,这文稿里藏着“我对天地间那些坚韧生命的敬畏,张扬着我的悲悯,洒落着我的疼惜”。在我看来,作者是惺惺相惜,借着这样的生命,承担对自我世界的塑造。
人,活在世上,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还有点理想、有点个性、有点审美、有点不甘平庸,那么就像物理上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受到的反弹会更多些。粗糙的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美好而有更多的眷顾,只会更多磨难,甚至容纳不下。但美好的生命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和无理、粗暴、丑陋的世界不妥协,这种不妥协很多时候不是以抗争的姿态出现,而是坚守。就像瞿秋白,虽然自认是历史的错误把他推到了政坛,但被捕后,他坚定地回答劝降者:“人不能否定自己的历史,就像鸟爱惜自己的翅膀一样。”没有豪言壮语,但他视死如归的坦荡征服了对手。这已不是能用所谓“高尚的情操”来赞美了,是一种境界。遗憾的是这样的生命都快被时间湮没了,所以作者有意去把他们从历史深处拉出来,让他们的光芒给自己和迷茫的现实一点光亮。
徐海蛟的写作是非常自觉的。他在序言中已指出,这次写作是“用笔将时光背面的结重新解开,让鲜活的面孔和心跳重回人间”。让一个个历史人物“重新微笑、说话、恼怒、愤慨,重新心绪绵长、患得患失”。这是一次挑战。历史散文的写作,如果没有个人富有见地的“历史理解”以及理解之后的精神照亮,那么就会沦为历史转述,陷入一堆史料中。显然,徐海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写历史人物,最可怕的是落入考究和学术研讨的癖好里去,那样写出来的人就缺乏血肉和灵魂,只是个遥远时代的木偶。”所以他“舍弃了对宏大历史的迷恋”,“找到一个具有暗示意义的事件和一个重要的时间作为切入点,在细节的重塑中,完成对一个人心灵脉络的梳理,或者对一个人耳目一新的定义”。
确实,在《见字如晤》中,作者努力在这样做。譬如写韩非,题目是《舌头的灾难》,抓住韩非结巴这件小事,引出因结巴失宠于秦王,让李斯得着陷害的机会,造成了人生的悲剧。一代高人竟因这样的小事造成这样的命运,令人不胜唏嘘。《秋白,1935》把1935年瞿秋白被自己的组织抛弃,被国民党部队抓获这个时间点作为切入口,写出了作为文人的革命者的悲剧和他坦荡的儒雅的坚定的精神气质。作者意识到散文这种文体相对于小说的局限性,不允许交代很多的事件,不允许细水长流,要在那么小的篇幅表现一个人的命运和精神,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徐海蛟在事件的选择上非常用心,有的是大事件,譬如决定李陵命运的浚稽山之战,有的是小事件,譬如韩非的结巴,无论大事件还是小事件,所有的采用标准就是是否关乎心灵关乎命运关乎精神。人物的命运各有不同,但通过这些事件,都指向了作者思索的问题——生存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对人类来说,怎样的生存是最合理的呢?徐海蛟在本书的跋中写道:“生命的终极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来,要这样纠缠不清?我们又能通过怎样的方式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地存在过?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了。但我想一个个体生命,他的存在就是他全部的价值和意义,他的那一段旅途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光荣的历史,就像一棵树,它成长、绽放绿荫、最后落叶飘零,它尽情做完这一切,它的光荣就写进了自己的年轮。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来说,能做的也无非是尽情绽放生命的绿意,把那过程酣畅淋漓地呈现给时间,就印证了存在的意义,获得了存在的价值,这些价值像我们头顶闪烁的星辰,虽然微小,最终会汇入人类生命的洪流,成为深远而博大的星空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徐海蛟的回答是否因为阅读了这些人的生命而感悟,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个集子确实是他“个人化的心灵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徐海蛟的这一组历史散文将“过去的死去的事实变成了现在的活生生的思想”(爱默生语),这些人物不再是“遥远时代的木偶”,而是他在理解中渴望与之对话的人物。这也是文学和历史的差异了,历史中的人物是面镜子,文学中的历史人物是“我们熟悉的师长朋友老邻居”。
要把这些历史转换成文学,也就是说把历史深处的人物消除漫长的时间隔阂,“仿佛从未走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徐海蛟自己说:“我尝试用各样的手法来完成一本散文集的叙述,有小说的匠心,也掺杂着诗歌的轻灵;有回忆和戏说,也有假设和暗含心思的虚构。”这是徐海蛟的优势,也是他的成功之处,他把小说、诗歌的方法糅合进了散文。因为用了小说的手法,所以有情节化的叙述,使得整个叙述过程有张有弛,有起有伏,既引人入胜,又扣人心弦,特别是写李斯、韩非、李陵的几篇,很有命运感;因为用了小说的手法,所以细节描写很动人,基本实现了作者的企图——“通过文字铺成的道路,让走失的人找到回归的方式。让他们在一个早晨醒来,重新微笑、说话、恼怒、愤慨,重新心绪绵长、患得患失”。我们可以看《秋白,1935》中的两段细节描写,瞿秋白独有的气质跃然纸上。
喝完最后一口酒,他起立掸去身上尘土,好像想到了什么,回头对军法处处长余冰说:“我有两个要求,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点就是不能打我的头。”
队伍离开中山公园,向刑场走去,瞿秋白一边往前走,一边突然有了唱歌的心情,于是他就开始唱了,先唱《红军歌》,再唱《国际歌》,他一遍又一遍,旁若无人地唱,高亢低回,慷慨动情,通往刑场的路,绿意逐渐葱茏,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间漏下来,斑驳有致,瞿秋白竟然看出了几分诗意。这哪里是赴死呢?分明是回家,唱到最后,他觉得浑身上下多了一股说不出的劲。
关于文中的诗意,我认为既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气质。徐海蛟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确实,前些年的诗人情结,对我的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都有着深刻影响。诗歌的历练能够让一个作者的语言变得精确,有直抵核心的力量。而融入诗歌气质的叙述,往往要比从未接触过诗歌的叙述轻灵,更简洁有力,寥寥数语就可达到目的。就像面对一堵墙,没有功夫的人,要靠攀爬,手脚并用,模样别扭,而武艺高强的人,轻轻一跃就过去了。诗歌给我语言上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它让我学会了如何翻越那些叙述中的障碍,不再绕来绕去,也不再为了讲明白一个事物,而用很大的力,累得汗流浃背,却也得不到既定效果。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诗歌阅读和练习,并未让我写出多少好诗来,倒是给我的叙述注入了许多跟诗有关的气质。”“诗歌是好的,它的好不仅在于让你拥有诗意的气质,有时它甚至是一个写作者的底气。”我想,这种底气来自于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写和想达到同步。读徐海蛟的作品,很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个人精微的感觉,独特的心灵敏感,以及细节的准确力量都因为语言的及物能力而顺畅地完成。但因为过于流畅,诗意有滑向空泛的危险,特别是在散文中,过多的诗意对以真实为生命的散文,有时是种伤害。散文和诗歌是有本质不同的,散文有时不需要那么轻灵,更需要拙一点,老实一点,不然会让人感觉质感不强。《见字如晤》中有这个小缺点。
作为散文中的“我”,和小说中的“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跳到前台说话的,呈现一个赤裸裸的“我”,而后者是带着面具的“我”。所以散文中的“我”的性情、思想都是一目了然的,当然,“我”的思想也由此决定了作品的深度和高度。徐海蛟在文中的评论,其实都是他从自己生活得来的感受和感悟,他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我依然没有足够心智去参悟全部的秘密,但我相信这会是一本好书,比以往任何一本都要好的书,在别人的命运里我融入了自己的悲喜,同样,在别人的命运里,你或许一不小心也会读到你的疼痛和快意”。是的,徐海蛟的人生路虽然说不上崎岖,但也几起波折,特别是对一个敏感、细腻、富有诗人气质的人来说,现实的生活似乎比常人更多几分纠结、不平和冲突,进而有更多关于生命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思索。这种思索其实是无解的,所有的答案都是一种励志式的自我安慰和为支撑自己找的理由,反而消解了思索的深刻性。而作者常常以回到“日常”作为生命的真正意义,譬如,《鼠样人生》中,李斯要被押上刑场了,作者有这样两段抒情的议论:
还能再牵着一只狗到郊外打一回猎吗?那只朴实的狗总是那么温顺,不声不响地走在他的身旁,然后飞快地蹿出去,呼哧呼哧地叼着一只被他一箭射中的野兔回来。还能再走一走故乡的黄泥路吗?闻一闻春天的油菜花,或者躲在冬日墙根,就着稻草干燥的香味,懒洋洋地抽一袋旱烟,看斜阳将时日一点一点拉长。还能再听一听上蔡人的口音吗?邻里的唠叨,老婆缝补的一双布鞋,还有为一场赌局赢来一吊钱后的那份开心。是啊,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尘世的生活如此温暖。
可是他已回不去了,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提心吊胆地活着。他身处高位,可高处不胜寒;他享受荣华,可永远咀嚼不到粗茶淡饭的清香;他广厦千间,可再没有像在上蔡的稻草铺睡得踏实。他的生活没有儿女绕膝的温暖,没有小家屋檐下的情味,有的只是浓重的血腥、阴暗的杀戮、冰冷的算计。这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尘世的生活有多么动人。
这样的悔意其实跟贪官被抓后,嘱咐后代“千万别当官”一样,虽然有可信的一面,但实在苍白。日常的生活有那么美好吗?如果尘世的生活那么美好,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宁愿冒生命危险而不顾?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视而不见反而去美化,其实何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呢?优秀的散文需要真实,所以散文背后的人在精神上必须很强大,要敢于面对自己,而人最不敢面对的就是自己。我一直觉得徐海蛟很有文学天赋,但阅历的有限妨碍了他的高度。所以当他有一次向我咨询调动工作的事时,我明知道那岗位与他的气质性情不合,但想着年轻男子在这世俗社会的压力,想着丰富他的阅历对他的写作也许有好处,就赞同了。不料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出了点故障,当时我心疼得流泪,也有点后悔让他换了工作。阅历算什么,写作算什么,以这样的代价去换值吗?所以当我今天写下这些评论的时候,我又问我自己,干吗要苛求他深刻呢?能让那些人物活过来就已比人高明很多了。如果深刻一定要以充满磨难的阅历去换取,那么就这样吧,这样也已不错。■
责编 谢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