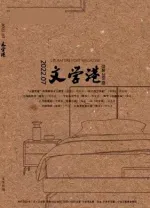山村行走(三题)
叶喆斐
老村长
老村长姓汪,从村办退下来那会正赶上古村旅游热。他家后山腰上修筑了步行道,大批背包客慕名而来,成群结队地徒步上山,转一圈回来,天已擦黑,没过足瘾的就想住下来,次日继续爬行进山。头脑活络的汪村长,在游客一进一出间看到了无限商机。他办完退休手续,就直奔镇上,报名参加了农家乐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等他拿了证走出研修班走回熟悉的村庄时,精神抖擞得像出征的将士。整个春天,他都专注于他的农家乐休闲旅店,信心百倍意志坚定地在他自家的灶口上重新上岗,当上“火头军”总司令。
老村长捏过锄头拨过算盘珠的手,也就从那个春天起,操起了菜刀挥起了大勺。他麻利地在灶台前挥舞着,所过之处,色香味一一呈现。青菜叶绿油油的,菜帮子白白胖胖的,刚刚从自家菜地里拔出来,带着“活灵”。老村长左一刀右一刀下去,绿白相间的小青菜顷刻之间四分五裂,从案板上轻轻一划,吱的一声全部倒入热油锅,窜出一尺高的火苗,映红了半间灶房。老村长的心比油锅还热火,比火苗还亮堂。这年头,城里人大老远赶来,除了看看山里洗过一样的天,看看桃红柳绿、油菜花开,闻闻四季气息、泥土芬芳,还有不就是冲着农家乐里鲜绿的叶,拖泥带水的根还有那份没打过农药的踏实吗?
一大早,老村长便站在自家一楼客厅的旋转楼梯口,用他十分热情十分洋溢的眼光扫视了洗漱的打包的绕到灶房吃早饭的客人,又抬头透过旋梯扶手扫视了楼上楼下整个空间,大约发现客人基本都起来了,便清了清嗓门,开问:“中午回来吃饭么?想吃什么菜?”大家起床后,进进出出打他身边过,十分忙碌。有说白天去爬山,中午自行解决,但晚上想吃土鸡。老村长听了忙解释道:“禽流感来了,土鸡没得吃了。”唉声叹气中少不了几分遗憾。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去年秋天,我和一帮驴友第一次来,都点着名要吃土鸡的。这屋前屋后苍翠欲滴的浓绿,千回百转越岭而来打门前过的溪流,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小鸡小鸭吃着五谷和小虫子,都是天然、无污染的食料,长出来的不是细皮嫩肉才怪呢。老村长说:“不吃土鸡是暂时的,现在可以吃毛笋啊,还有透骨新鲜的倭豆煲。”客人一听来了食欲,七嘴八舌地点开了,村长一一应答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记全。不过我想象得出,那股认真劲与当年在村委会开会,解答村民这个那个问题时的神态是一样的。
记下所需菜单,老村长直奔停放在门外操场上的三轮摩托,插上钥匙,突突突发动起来。他跨上去,摸了摸衣兜。先去哪里呢?猛然想起前两天邻村大阿妹来过电话,她的地瓜粉丝晒干了,让他去取。路过山头顺便还要掏几颗毛笋,那是刚才我们点的。
三轮摩托沿着村道,麻利地拐过一个溪坑桥,一支烟的功夫,已在一排老屋群前停住了。这组老屋由坐西朝东的三间老屋与坐北朝南的五间屋构成,明堂和明堂相接。老村长的大阿妹家就在这组屋群里,老屋大门朝东,围墙是用旧瓦爿和碎石头垒起来的,墙头隔档放了几只小瓦罐,里面横七竖八种了一些大蒜和小葱,在山风中摇摆。厚重的两扇木门,被岁月蚀成褐色,坑坑洼洼露出一根根木筋。老村长一脚跨进石头门槛,迎面是一个长方形天井,天井中央摆着几只圆形竹编筛子,上面铺陈一盘盘地瓜粉丝。
地瓜粉丝,是我最喜欢吃的食品之一,超市里有,但做工完全不一样。临时摊贩叫卖的粉丝担心不卫生,是不敢尝试的,有人说吃它等于吃编织袋。眼下有些食品真不是做给人吃的。相比之下,山里人家自己做的粉丝就相当稀罕了,地瓜都是去了皮的,切出芯子那一块,轧碎打浆,滤去水分沉淀成粉,是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土灰色的粉倒入加工厂的和面机里,拉出一根根土灰色半透明的丝,灰扑扑的,卖相不甚好,但绝对是绿色环保产品,久煮不烂,一口下去筋斗滑爽,口感柔软。
老村长大阿妹家的粉丝是不外卖的,自己留着食用,之余再送些亲朋好友,尤其是那帮上海远亲,特别喜欢地瓜粉丝之类的土特产,越天然的越好,越绿色的越好。老村长是她阿哥,阿哥开门做生意,打的都是天然的绿色牌子,粉丝、淀粉、青菜萝卜芋艿头毛竹笋,小到大蒜小葱,都由大阿妹特供。
从大阿妹家出来,老村长的三轮摩托后翻斗厢里多了两大包粉丝,老村长捋捋裤脚管,又上路了。绕过弯弯曲曲蛇形山路,在一个干涸的山沟边停下,前面有个沙堆,对面有一条狭长的山谷,不是很宽但很长,绵延几公里。村长想跨过山沟,到山谷上方的自家竹林挖几颗毛笋,可又放心不下车兜里的两大包宝贝,情急之下,从山道杂树丛中揪下一大把杂草,盖在上面。有了杂草作掩护,老村长放心大胆地向毛竹林走去。
村长老婆
在老村长家灶房间吃早饭,一股呛人的煤烟味从门边飘了进来,这股怪味很难闻,但却是久违了的。
这种味儿是和我儿时记忆联结在一起的。那时老家没有煤气,烧菜煮饭全靠一只煤球炉。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生煤球炉子。将炉内隔夜的煤灰清空,用废纸点燃,把碎木块放进炉内,木块燃着后盖上煤球。这时呛鼻的烟味就会从炉内冒上来,呛得两眼通红,泪水直流,不得已只好“请”它去了弄堂口。遇到刮风落雨,木柴受潮不易点燃,就给炉子戴一顶“高帽子”——铁皮烟囱,弄堂口摆摊的老铁匠定做的。小喇叭似的烟囱能拔风,能让火苗窜高些,能让生炉子的速度快些,罩在炉口也不用担心炉火被雨淋灭。那时候,每当傍晚,弄堂里的煤球炉子便排起了长队,整个弄堂到处飘散着炉烟。虽说呛人,但那时煤球炉是与吃饭连在一道的,对我来说就有了几分诱惑。
现在城市都用上了液化气天然气,这味儿也只有偶尔在卖羊肉串摊位前闻得到。在山区,多数人家还是习惯烧煤炉,柴禾是现成的,出门就有,比起液化气,点火生炉子,是有些不方便,但成本低,节俭的山里人家会用液化气炒菜,煤炉烧水做饭,冬天取暖。
门外生炉子的是村长老婆。入住他们家,很少听到她开口讲过话。入住第一天,我们在里屋吃饭,老村长就在灶房喊老婆去端菜,她应声而出,客人不禁一怔,大伙嘻嘻哈哈地与灶房里的“火头军”总司令开起了玩笑。村长老婆让人立即联想到传说中的贤妻良母。她低头出,低头进,一直在餐桌与灶头之间悄无声息地来回跑动。有性子急的,不停催她快上菜,热乎乎的农家菜,都有点等不及了。村长老婆勤快地应答着,小碎步迈得更紧密了,但没有发出什么声响,和她的说话声音一样很小,很柔和。
后来发现她一直是笑眯眯的,笑眯眯地端菜送饭,笑眯眯地讲话,笑眯眯地扫地。走路说话都轻手轻脚地低着头,只有和我们客人打招呼时,才会礼节性地抬下头,还没等看清她的脸,早又低下去了。和陌生人打招呼,有点怕难为情,温顺害羞的样子,让人觉得她不是一位老妇而是一个羞涩的小姑娘。晚上,客人打麻将,三缺一,村长被叫去补位,留她一人在厨房打扫“战场”。整个拾掇过程都是按她每晚原定的程序有条理地进行的,一个小时后,灶房又恢复原样,干净整洁,一扫刚才老村长大刀阔斧辗转于此的混乱场面。老村长是个牌迷,上手就刹不住车,一圈接一圈,快到半夜了。她拿着扫帚与畚箕,从厨房到客厅,来来回回打扫,有好几个回合了。我瞌睡得不行了,上楼回房前劝她先去睡觉,她照例笑笑,没吱声。我上楼洗刷完毕,顺楼道瞄了一眼,看到楼下麻将桌边,她依旧安静地坐着。
薄雾笼罩了整个山村,夜间气温较低,空气中的水蒸气在田野里结成霜。初春,山村的早晨依然有几分严冬的寒冽。村长老婆点着了煤球炉在院子里扑打身上的灰尘,拎着炉子回屋,炉膛火红,映着她红彤彤的脸。她给客人悉数倒水沏茶,顺手灌了一壶热水给我,一起递过来的还有一小包茶叶,装在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这是野生茶叶,很香的。”软软绵绵的声音充满疼爱。真是一个细心的女人,知道我好这一口就特意留着。昨晚也不知道她几点睡下的,反正一大早就在扫屋扫院洗衣拆被生炉做饭,里里外外支应,勤劳如蚁。
老人们的村庄
沿着盘山公路,一直走到路尽头。迎面是一个大山坳,坐北朝南,像一把巨型太师椅,四平八稳,横放在我们面前。
七零八落的小村庄都安放在这把“太师椅”里。村子依山而筑,村道从山脚一直伸展到山腰,阡陌交错。抬头仰望,“太师椅”后背险峰层叠,绿林尽染,与这美景不相宜的是灰暗衰老的小村子掩映在绿荫中,显得破败没落。村子很小,没有店铺,没有学校,却有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老式大礼堂,一个破败不堪的轧米厂,灰扑扑的夹在民屋群里,外墙上还隐约可见“文革”时期的标语。轧米厂已经废弃多年了,屋顶漏洞百出,不知怎么也没拆。礼堂偶尔还办个丧事,但也年久失修。
小村子几乎没有一幢新房子。老房子的外墙多半已经坍塌,长出了大量杂草,阳光穿过断墙,满目疮痍。倒掉的部分还是马头墙,以前都是大户人家,老房子屋檐木刻,马头墙特有的青砖依稀可辨。大户人家曾给村子增添过旺盛。人气最旺时村子有数百人,炊烟缭绕,童声喧闹。现在村子静极了,静得有点残忍。年轻一点的男人,女人,孩子连同他们的家,都去了山外面的城市。
通往村庄的公路,只有阴历逢三或逢七,才有班车来。山下来串门的亲戚,城里探望父母的子女,会乘车上来,逗留不到一天,就走了。老人们也会搭坐班车下山,买回一些油盐。
村口,挂在老树上的广播喇叭每天响着,准点播报。树下那间村办活动室,里外坐着几位老人,大的近百岁,小点的也过花甲。房子是砖瓦结构的平房,有了年份,昏暗的屋里摆着两张牌桌和一些板凳。从早到晚,老人们几乎都聚到这里,打牌,聊天,打瞌睡。
我们徒步进村,村外遇见一位老人。我们跟随他在村道上前行,沿途遇到几个熟人,他都开心地告诉人家,他们是从山脚下走上来的游客,那种兴奋的心情,就像过节一样。
山村太孤寂了,老人们太渴望有人进山来,讲讲话,听听声音,有点人气。
一位老太太拎着两只热水瓶,给我们的水杯倒满水,看到我们拍照,一直怯怯地冲我们笑,我们提出和她合影,她像孩子一样兴奋,不停拍打衣裳上的尘土。我不知道她的家庭情况,或许她有很多子女,或许她的子女在城里富甲一方。只是她的眼里,充满了落寞的神情。只有拍照的那一刻,她是开心快乐的。
离开时,老人们在村口站成一排与我们挥手,一口一个再会。
这些老人,我们还会再会吗?这个地方,我还会再来吗?
再来,他们还会在这里吗?这么一想,心里就有了酸楚。人就是一个过客吧。多数人与我们擦肩而过,就永远不再相见了。前行中,自己又何尝不是别人生命中的过客呢。■
选自《镇海潮》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