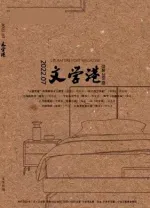至亲
秋阳
我对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这并不是谎话,只是我从不曾用言语将它表达出来。而我的行动又常常遭人误解,甚至,这个误解曾来源于我自己。
去车站接他们的那天,下着大雨。他们的汽车晚点,我又早到了许多,就在候车室里来回走动。候车室里有很多空位置,但我一坐下,就觉得凉意从不锈钢座椅直渗到我全身的每个毛孔,我立即又起身了。悬挂在候车室内的电视机正播着新闻,我抬头注视着电视屏幕,借此打发时间。窗外的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像一层极厚的帷幕,将我团团围住。我已备了一把伞,现在恐怕是不够了。
他们到了后,我小跑到接站口,看见大巴下围满了人,我找着熟悉的身影,直到听见弟弟的声音。他们站在大巴旁的一个小卖部下,身体藏到雨棚里,面朝前方,在来往的人群中显得很单薄(这种单薄和体型无关)。他们的头发已经有点湿了,把拎着的东西往雨棚里藏了藏。他们不能向我走来(因为没有伞),只能看着我跑向他们。
我原本以为久未见面的我们会有种重逢的喜悦和亲切感,至少之前我是这么想的。我想他们看见我时都会笑,脸上呈现出我很久未看到的来自至亲的温暖的微笑。
直到我走到他们身边,才终于看到了母亲的笑容,她一直没变。
“你刚才在哪里?”弟弟说。语气有些埋怨。
“我在候车室里等,你们的车晚点了,我一直留意着广播。可是车子到的时候它又没通知。”他希望在车窗外看到我的影子。可我却让他们等待,他们在关了门的小卖部雨棚下看着越来越大的雨滴,滚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形成无数个水洼。
我换了副轻松的表情,向他们说抱歉。我把其中一把伞给了母亲,另一把给弟弟,然后躲到了他的伞下。他比我高出十几公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常常叫着姐姐姐姐,问我很多的问题,会在我的面前哭鼻子的他。他的话变得很少,我一直和他说着话。他也许并不喜欢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我感受到了他体内的那种抵抗,他将话语都藏了起来。我问了他那边的天气,几点起的床去赶早班车等等。然后我向他介绍了车站附近的变化,他已有好几年没来我这里了。车站附近变漂亮了很多,旧的房子和工厂的旧址都已拆掉,包括那个竖到半空中的废弃烟囱。原先杂乱而无序的景象都被沿河的公园绿化所代替,河面上还搭了几座江南风格的石桥。石桥被雨水浇成了青灰色。
我已离家很多年。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去北方读书,回到家的日子屈指可数。仿佛从那时开始,家就和我隔着一道屏障,我曾想着穿越,却总不能成功。年轻的时候总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然后离家越来越远。这不只是地域上的距离。
我高估了我自己,或者是把很多东西看得过于简单了,要不就是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它们总是藏在一个什么地方,我蒙着头不停地往前赶路时,它们常常会半路杀出来,然后把我碰得头破血流。那些被我匆匆赶过的时间总是躲在后面嘲笑我,你这个小丫头,总是那么天真,你永远都是这么个小丫头。是啊,等我做了母亲,有了更多的承担,我的世界开始更加复杂,我仍旧是那个样子。蒙着头往前赶路,然后跌倒。
也许是我赶路赶得太急,时间虽是一点一点地熬过,但结果却总是来得太快,像是一下子被拉大的禾苗,我常常会被突然间降临的陌生感侵袭。在我的世界里,熟悉的东西渐渐减少,那些空间很快被陌生的事物填满,来不及熟悉,更多的陌生又填充了进来。连弟弟也变得陌生了。
我带他们去了订好的宾馆,那是闹市区一家很小的商务宾馆。条件很一般,只是价格实惠,除了这点,其余的都不能让人很满意。卫生间的窗户朝着一个小区,窗户一直开着,放在窗口洗脸台上的一次性洗漱用品被雨水打湿,塑料袋上挂满了水珠。房间的光线很差,唯一的窗口就是卫生间里的那并排的四扇窗户,拉着遮光窗帘,一些光线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传到房间里。
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青白色的灯光顿时照亮了整个房间。地面上都是湿脚印,还有雨伞滴下的水痕。
要是不下雨就好了。我们可以到处逛逛,也不用弄得这么湿。我和他们说。
是啊,如果不下雨,这间房间看起来也没那么不舒服。不会像现在,整个蒙上一层湿漉漉的黯淡。
我本来计划好带着他们看一看城区的博物馆还有名人故居什么的。他们不是第一次来,我很惭愧,之前从未带他们去过。他们上次来的时候,我刚生了孩子,自己弄得焦头烂额。后来他们再也没来过。可是这雨天,实在不是游玩的好时候,我们又只有两把伞。这雨恐怕要下好几天了,天色昏暗,雨没有丝毫要止住的迹象。
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和弟弟的交谈才多了起来。我们俩之间那种让人尴尬的冷场渐渐少了。从宾馆出来向右拐就是一条热闹的街。我们沿着河岸的石板路走着,进了路对面的一家米线店。当然,我们不是来吃米线的。这家云南过桥米线店除了供应米线,也供应各类的简餐、套饭。立在店中央的灯箱式的价目栏还带着图片,一目了然。弟弟给母亲叫了一份酸菜肉末烤饭,说这个适合她吃。久不与母亲一起生活,对于她的喜好,我全不如弟弟了解。她正坐在灯箱式价目栏的后面,等着我们。她相信我们会为她安排好一切。她不像别的母亲,会说要什么要什么,她并不参与我们的意见,连吃饭这样的小事也是如此。我们点完餐回去,她坐在只漆了一道清漆的原木椅子上朝着我们微笑。
母亲让我们吃她的酸菜肉末,说这个比较咸,她一人吃不了这么多。我用筷子轻轻夹了一点,她又补了一筷子到我盘里。她细细地嚼着嘴里的食物,不再说话。
母亲很好地控制着咀嚼的节奏,看着铁板托盘里的烤饭,用很专注的眼神。我甚至发现,她吃饭的时候有一种“优雅”的神情。我真找不出其他更适合的词,更无法形容我的感觉。她不是什么名媛淑女,她只是以一种无比从容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食物,一点一点地,细嚼慢咽,直到全部吃完。就算只剩下最后几粒米饭,她也不会加快速度,像完成任务一样去迅速解决。她和我们姐弟两个都不一样。
我们又像小时候那样,分享着各自餐盘里的食物。我把咖喱鸡肉夹到他们的盘子里,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吃。我只想这么做。我又伸出筷子,夹了弟弟盘子里的牛肉块,放进嘴里尝了尝。有点辣。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能吃辣椒了,这个沿海小城的人们很少吃辣,他们更喜欢海鲜。
吃完饭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几千年前的文明。我和他们提议。
他们的盘子快空了。外面的雨似乎弱了一些,只是风仍旧很大。
好吧。弟弟看了看外面的雨。点点头。
远不远?他紧接着问我。
不远,就在河对面那个公园后面。我们继续往前走,过了桥再往回走一段路就到了。
我给他说明了路线,又简单介绍了一下这家博物馆。弟弟的眼神里开始露出些兴趣来。从下车到现在,我才刚刚从他的眼神里看到这样的带着光彩的东西。我也开始高兴起来,开始不再在意外面的坏天气。
我们过了桥,沿着河北面的那条路一直往西走。这是条朴实而安静的小街道,汽车只允许单向通行。路的一边是河岸的护栏,粗制的铁索连接着大理石桩子。沿河种了很多香樟树,它们顶着巨大的伞状树冠,高出了对面建筑的屋顶。
弟弟问我这些树是什么时候种的。我不清楚这些树木的具体年龄,只知道,它们伴随着这座城市走了许多年。它们如此的安静,甚至忘却了时间。
博物馆就在这条路的终点。那里是个大公园,博物馆就盖在山脚下。我们进去的时候,整个大厅只看见保安和穿着制服的接待小姐。大厅显得很空旷,正对着大门的屏幕播放着闪烁的变幻的图文。
你这里来过几次?
我手扶着大厅一侧在水里飘着的仿古木船时,弟弟问我。
我照实回答,只有3次。一次是带着孩子来,一次是陪着同事来,一次是陪着你们来。
我突然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对这些古旧的痕迹感兴趣?博物馆是免费的,想来,随时都可以。我来这里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而且都不是出于内心真正的单纯的需求。或者说,只是带着任务而来。
这次也是如此,对待它们,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景点一样,我希望别人能够从中得到美感或是启示,或是其他的东西,甚至是某方面的满足感。这只是我接待人的某一组成部分。我带他们来这里,说这里有多好,这里有很多你从未见过的东西,这些就是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
这是否是种不尊重的表现,不尊重这些古物后面的文明。我看着藏在厚厚的玻璃后面的陶罐和骨器,柔和的灯光让它们仍旧带着新鲜的色泽,仿佛不曾在土底埋了千年。它们被人从各种文化层里挖掘出来,摆在这些美丽精致的玻璃窗里,它们安静地审视来往的人群。
母亲有时候会盯着玻璃窗里的物品看很久,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类似于惊讶或是好奇之类的,她只是看着它,用一种专注的眼神。然后她瞬间把眼神收回并很快转过身,步子快起来(这和她看东西是两个完全不同节奏),跟上我们,然后又会停下来。母亲没读过多少书,因为各种原因,她未能顺利读完小学。她喜欢读书,少女时期的她读过一些家里的藏书。我很小的时候,她常常会给我讲一些故事,诵读一些诗词的片段。这些都来源于她年轻时候读的书。再后来她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和许多人一样,常常为一日三餐发愁,书本便从她的生活中淡去,直到我出生。
那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母亲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她开始为她牙牙学语的小丫头读书,用她仅有的知识。我很愿意听她给我念那些故事。她甚至不会刻意地去挑选,她去父亲学校的图书馆找书,连大本的小说都会拿来给我读(其中有很多她不熟悉的字)。我知道,她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培养她孩子某方面的特长与能力,更不是为了所谓的文化熏陶,她的脑子里从未有此类的概念,她只是出于本能,或者说她喜欢,也愿意这么做。
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场景。在屋子边的泡桐树下,太阳光线并不太热烈,我坐在小板凳上,听着她为我读书。
母亲识字不算多,理解能力也有限,更没有学过什么系统的历史课程。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包括示例牌上的解说词,她不一定能完全明白。但她用一种极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我不知道她看到这些时脑子里会反映出什么,我真的不了解她的思想。
弟弟和我一样,我们受着相同的教育。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区别的只是各自的专业和学校。他用着和我类似的神情看着博物馆里的一切,他会盯着青铜剑,而我会留意先人的字画和断成片的藏书。但我们都没有母亲那种专注的眼神。
我们三人很少像这样一起去某个地方参观或是游玩。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成年后的第一次。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的这些时间我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它们走得很快,没有停下来让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在某一刻的时间片段里悠闲地度过。它们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读书、就业、成家、生养孩子,每一步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战争,而时间也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控制着我,让我有紧迫感,但又对它无能为力。
我刚结婚时,父亲去世了。这太突然。对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我开始把握不了我自己,像一艘失去方向的船舶,无人掌舵,在大海中随波逐流。生活并不是你想要怎样就能怎样。我那时并不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总是想当然地用一种完美的理想去修补现实的漏洞,却发现漏洞越来越多,已看不清原本的样子。
就像现在,我们在一起,有种温暖的亲近感,我很喜欢他们在我身边的感觉,可另一种陌生的距离感,又侵蚀着我。让我的表情无法表达内心的感受,它越来越僵硬,连笑容都是如此。我只能带着他们不停地行走,一旦坐下来,那种安静就让我无所适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着活泼的性格。
那是一座大宅子,藏在闹市当中,一道高墙和一个小广场将它与街道隔开。但它仍有一股森严的气势,从街道上走过的人如果偶然侧目,就能感受得到。我们从隔墙中的一个圆弧形拱门进入一条巷子,看到它敞开的大门。门前没有砌得很高的台阶,不像其他一品官员的祖宅那般的高高在上,它以一种更加平易近人的姿态迎接着来客。
我们进去时雨下得极大,外面白花花灰蒙蒙的一片。雨点和雨点之间相互较劲,迫不及待地落下,猛烈地敲打着地面。弟弟左边的肩膀连带身后的双肩包都已经湿透了。我的鞋跟也进了水,只好踮着脚走路。
我们没有导游,就自己在宅子里转,从一间转到另一间,到处都是走廊和门厅。我不是第一次来,仍旧是没有方向感。
母亲说,这个宅子和她小时候的家很像,只是她家的房子要小一点。
我曾听父亲说起过母亲的事,听说当时她的家族在当地是望族。
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外婆和她的兄长们都很宠她,她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父亲曾对我说起母亲年轻时的任性和我行我素。她会与外婆发生口角,斗气等等,但她是依恋外婆的,比她的兄长和姐姐更加依恋她的母亲。母亲只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的思想,她的感情。母亲不常在我们面前提起外婆,如同我不常在我的孩子面前提起她。这并不代表感情的淡漠,绝对不是。
外公过早的去世,外婆像一个男人一样操持家庭。母亲永远都是她最宠爱的小女儿。即便她常常朝她发脾气,对她做出反抗。她不像她的兄长和姐姐,对外婆毕恭毕敬。外婆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人,但她唯独拿这小女儿毫无办法,除了尽自己的一切来保护她。
我没见过外婆,她去世后两年我才出生。我多想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个词汇。小的时候,这种感觉不是很强烈,那只是种简单的好奇,不太会留意母亲说起的关于外婆的话。而现在,这种好奇已衍变成一种强烈的情感。母亲却老了,她的思想开始混杂,我更加不明白她。
我们打着伞,在那所大宅子里走。这样的雨天,除了我们三个,几乎没有其他的游人。前面是个睡莲池,睡莲小巧的叶片浮出了水面,嫩绿里透着淡红,雨点不停地打在上面。
我家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荷花池,它比这小。母亲说。我喜欢从池子的这头跳到池子的那头。那时我才十岁,在荷花池边来回跑。有一次没跳过,掉进了水里,水不深,但衣服都湿了。你外婆气坏了。
母亲说着她记忆里荷花池的片段。她脸上泛出了光泽,眼神里有着活泼的颜色。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脸上早已爬上了皱纹。她居然会有如此纯净的表情,如同少女一般,也许她的世界一直是如此,从少女时期起,就没再改变。她一直是那样的她。就算她的孩子都长大了,她还是那样的她。我和她不同,但我却羡慕她,能拥有自己的世界,就算到老,也能如此的清澈。我的外婆对她的宠爱,一直在她的生命之中。
我们家的房子是当时县里最大的。大爸爸是县长,就是你外公的哥哥。我们的房子会用来接待贵宾。它的另一半是旅馆,遂县最好的旅馆。母亲继续说着房子的事,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这位明代先贤的故居让她想起了很多事情。她的脸上浮出了笑容。
当时家里住了很多人。我们两家人的房子都是连在一起的。大爸爸的家就在隔壁。旅馆在另一边。旅馆是你外公开的,那是幢三层的楼,遂县只有一幢这样的楼。是祖上在京城做官时,留下的,还有一块御赐牌匾,也挂在上面。他是抗战英雄……母亲很自豪,她提高了声调,那是她家族的荣耀。我很小的时候也曾听她说起,她的先人在抵抗八国联军时立了战功,当时的朝廷赐了牌匾,悬挂在祖宅之上。
也许,母亲内心的优越感亦来源于此。她坚持着她内心那些常人不能理解的想法,从她的童年开始,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就算那些与她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都离她远去,她的亲人,她的故土,她的家,最后只剩下她自己。她的先人,她的家乡也已沉入了水底,几十米水深下的遂县古城无从探究。人们在她故乡淹没的水面上游玩,碧波荡漾,风景独好。她会指着湖面上的小山包和我说,那以前是一座很高的山。
我们都失去了故乡,在别人的土地上逗留,甚至扎根。
弟弟听着我们的谈话,并没有特别的表情。他的眼睛不时地观察着木质雕花门窗里的古朴摆设。也许他并不是很认真地在听我们的交谈。故乡的概念,他也有吗?我摇摇头,自嘲地笑了,也许,他并不像我们。男儿志在四方,所以他带着母亲到了另一个城市打拼。那很累,很辛苦,但他认为自己必须这样做。
几年前,弟弟辞去小县城的一份稳定工作,到大都市打拼。我不赞成,和他大吵了一架。他说,你自己不也是这样,为什么要来管我。是呀,我忘记了,我曾经如一只试图穿越透明玻璃窗的昆虫,蒙头乱撞,只因前方有我向往的世界。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身体里留着相同的血液。就算如今,我们脑子里的世界已经千差万别,毫无相似可言。
姐姐。姐姐。第一天上学的弟弟坐在教室里哭。老师指着门口对他说,你姐姐还在外面,并没有走开。我又重新站到门口,等着他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回家。我替他擦掉挂在睫毛上的大颗泪珠。他紧紧抓着我的手,好像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过。那一大一小的两张脸,重叠在一起,稚嫩而又沧桑,陌生而又熟悉。■
选自《姚江》2013年春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