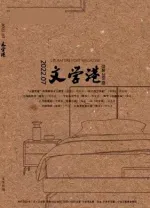老屋杂记
啸奇
一
“家”字笔画、本意并不复杂,但“家”的引申含义极其丰富,家庭、家族、家乡、家国、家天下等等,堪称华夏人伦文明的出发点。有“字圣”尊称的古文字专家,同时也是儒家经纶权威的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条目中怎么也不愿将“家”字原始本意直译成“豕的居处”,唯恐玷污龙的传人居然源自“猪圈”。近代古文字学家早已认定,从最早的甲骨文算起,“家”字本意就是“猪圈”,引申假借为“人的居处”。细细想来,当我们的祖先能够圈养野猪并与家人定居,尽管那时定居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瓦房木屋,甚至有可能还是山洞巢穴,但的确已经具备了“家”的衣食居住、生息繁衍等基本内涵。“家”字本意不但没有丝毫羞辱感,而且应该敬佩我们祖先的聪明、勤劳、质朴、善良。
不想由此探讨儒家学说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宏论,只想和诸多居住在城市商品房乃至豪宅别墅的人们,共同交流一个十分平常的话题:我们现在住的新居与传统的老屋,究竟有什么质的不同与缺失?不要简单抢答,老屋是木瓦结构,新家是钢混结构,那只是房屋的外表壳体;也不要一一罗列彩电、冰箱、煤气灶等现代家具,那只是新居的内部摆设;当然也不要回到家畜饲养的原始话题,谁都感觉城市新居的宠物不会比农村老屋少。我提供另一答案也许会引人哑然失笑:具备几室几厅乃至豪宅别墅的现代新居,唯独没有传统家庭最常见的老屋堂前(祖堂)。平时从不住人的老屋堂前,其承担的婚丧两大主要功能早被宾馆、公堂、殡仪馆所代替,估计今后的城市商品房乃至豪宅别墅也不会再有类似的专用厅室,但堂前承载的人伦精髓理应在现代新居中有所体现与着落。
我家老屋堂前的花格门至今仍是白坯子,这在传统老屋中肯定算不上富贵典雅,但四周柱壁统一色的中国红,还有拱形天顶、水泥地坪,从小就觉得特别宽敞通亮。那时有同学到我家来玩,总会疑惑地问道:“你家以前是地主还是资本家?”我会立马驳斥:“别胡说八道!我爸出身下中农,我妈成分是职员,老房堂前是外公撑外洋轮船赚来的!”其实我家前后两进老屋,只有后面一进小屋才是外公手里造的,前面一进大屋连家母也说不清究竟源自曾祖还是高祖,反正不可能是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商。在上海见过世面的外公外婆均不喜欢在乡下置田从耕,否则倒有可能评为浙东特有的工商地主成分。“八一三”上海沦陷,在法籍外轮任管事(大概是水手领班)的外公也因此歇业,不久因胃溃疡病故,老屋堂前的花格门再也无力完成油漆。曾经开办的“福泰树行”,其实只是以老屋入股的合伙方,房产租赁收入仅能勉强维持一家生计,连小资本家也够不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父、家母先后下放老家务农,由此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命运,却也避免了老屋堂前被肢解“征租”(极左时期的房改政策,拨乱反正后终止)厄运,只是堂前已沦为堆放柴草农具的杂货间。老屋堂前历经台汛雷暴、兵戎战火、房改文革等等天灾人祸,至今完好无损,实属不易。更为称奇的是,并非书香门第的老屋堂前居然还有寓意不俗的“行远堂”雅号,尽管那块木质、镏金匾额静静地藏在阁楼已近半个世纪,但它肯定不再寂寞孤单。我已将它存照作记,并奉赠从小随舅父“建设三线”落户湖北的表姐表妹,还有定居异国他乡的兄长侄女。作为“行远堂”后人理应记住,本堂高祖源自慈溪陆埠(现属余姚);纱厂女工出身的外婆为追念外公,委托本地乡绅手书堂号匾额;先父家母为避文革之灾,无奈将红底金字的匾额涂黑藏于阁楼,并一直保留至今……
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安居黄金海岸现代小区,守望粉墙黛瓦传统老屋。更为幸运的是,面对席卷城镇乡村的城市化浪潮,有识之士已经冷静指出,城市化并非简单地拆旧建新。小桥流水河埠头,弄堂天井七石缸,不应只沦为城市居民的美好记忆。老屋堂前承载了普通家庭的渊源流传,折射了华夏民族的人伦文脉,同样需要现代城市文明来细心呵护与传承。
二
我家住在河塘边,小桥流水河埠头,一头连着“碶上墩”,一头连着“小路埂”。屋檐下,天井旁,听说过孟姜女、隋炀帝的故事,向往过上海滩、跑码头的美梦。位于江南沿海小镇大碶头的我家老屋,是本地比较典型的清末民居,俗称五间二弄七架屋。老屋后门口还能望见南侧高耸秀丽的太白山,但我童年的生活空间大都集中在老屋前后、小镇附近,过着并不富裕也不算饥寒的农居生活。
临近高中毕业时才第一次听说新碶下三山一带要建造北仑港,据班主任老师讲那才是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的未竟宏愿——东方大港。深水良港究竟什么样,那时谁也说不清,倒还是先父颇具见识,乘凉闲聊时,指着刚刚费力整修的河埠头信口直言:“大海边的叫港口,江河岸的叫码头,小桥旁的就是河埠头。”把日常用于洗刷担水的河埠头比喻成吞吐货物的港口码头,让人忍俊不禁,但确有几分道理。随着道路运输的日益发达,内河航船几乎绝迹,人们大概只能从埠头阶沿的缆绳系孔中,追寻内河水运的痕迹;或从老屋床头的睡梦中,重温“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欸乃橹声。乡里有句俗语“河塘旁边生耳朵”,谜底就是河埠头。我家门口的河埠头很独特,一直只有半只耳朵,那天晚上才解开我心中的迷惑。先父缓缓道出:“造桥铺路修埠头,历来都是积德行善之事,你外公倒不是吝啬修半只埠头与邻居共享,只因开办树行,半只埠头更便于树木的装卸运输。那时树木最远来自南洋,途经广州、福建沿海,再从新碶下三山驳运到内河,然后利用纵横交错的碶桥河漕转运到高塘、邬隘、塔峙、大碶等乡镇。相传船家上船前将饭瓜(南瓜)种在船上,到达我家门口时,伙计已经可以采摘充食,足见路途艰辛、遥远。”当时并未意识到内河埠头与海洋港口之间的渊源文脉,倒是印证了老屋门柱上几乎湮没的“公私合营福泰树行”的字迹来历。
当我几经辗转返回老家时,泱泱大港早已挺拔东海,碶塘故乡旋成开发热土,原属镇海的江南区域也因之更名成北仑区,港城北仑更是闻名遐迩。尽管老屋、河流依旧,道路、小桥早已重新翻修,河对岸、后门口也已成了现代商住小区。早年随舅父“建设三线”、落户湖北的表姐曾回家探亲,到了老家河边还迟疑再三。四期集装箱码头会审间隙,一位长我几岁的上海港务设计人员由衷感叹:“你们北仑发展真快,第一次参加北仑港勘测设计时,宁波到新碶只有一条沙石公路,两旁稻田成片,绿水萦绕,下河游泳特别惬意!现在从上海都可以乘高速直通北仑,一路高楼林立,路桥纵横,那条公路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真可以写一篇港口与城市的专业论文!”我笑着回答:“那条公路现在还叫新大路,但早已不是原来路径。那时能够下河游泳不算稀奇,童年的我曾经还有清澈见底、鱼虾争食的记忆。海洋港口新北仑的论文不敢涉足,小桥流水河埠头的故事倒可以信手拈来。”
英年早逝的著名画家陈逸飞先生曾有一幅题名《桥》的传世油画,据介绍场景取自古镇周庄双桥,这与现代红学家考证大观园原型出自北京恭王府有点类似。并非有意穿凿附会,该画主题更像是我家门口曾经拥有的“粉墙黛瓦搕渔船、小桥流水河埠头”。因为该作品另一题名为《故乡的记忆》,逸飞先生老家就在北仑新碶头,他自己也曾说过:“我画的是江南小桥,你可以说它像什么桥,也可以说它不像什么桥。”稍具文史常识的人也都知道,万里长城、京杭运河堪称华夏双绝,但京杭运河终点不在杭州而在宁波,如何更好地开发保护这一漫长、悠远的人类遗产,并发挥其绿色环保、低碳经济的效用,已不再是一项单纯的水运工程。有幸参加过杭甬段运河出海口工程可行性研讨会,无论是小浃江方案,或是凿通岩泰水系,我肯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家门口的河埠头,搭乘一叶扁舟,溯源京杭运河,追寻童年印象中“孟姜女哭长城、隋炀皇帝看琼花”的千古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