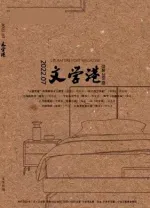滨海的春晓
滨海的春晓一带原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晒盐场,也是甬上较大的盐场,盐场建成那年又恰逢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故取名为“联胜”盐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起,父亲就在盐场的三门碶闸上守候了二十多年,直至他退休回家。
盐场位于春晓的西南面,放眼望去,盐田星罗棋布,滩田间夹着多条纵横交叉的银白色水带,其中有两条是用来纳潮和排淡的。十多华里长的高标准海塘把汹涌的潮水挡在了塘堤外。而上千亩盐田里生产出的优质原盐曾源源不断运往城区供应市民,还调拨到省里乃至全国各地。
联胜碶位于高标准海塘的中间部位,原介于北仑春晓与鄞州瞻岐之间。当我相隔20多年再次来到父亲曾工作过的碶闸房时,境况就大不一样了:几根粗大的螺杆一字形排开,碶座下各有一台电动启闭机,旁边还摆着一台柴油发电机,这是台汛时停电备用的。那天我去时正下着雨,排淡河上的水正在上涨,闸内的操作人员往墙上轻轻一摁按钮,霎时间电动机隆隆飞转,闸门的螺杆徐徐上升,碶下的河水穿闸而出,直奔大海,一泻千里。见此情景,站在一旁观看的我真是感慨万千:“如今的管碶闸条件,今非昔比,连做梦也想不到!”
1971年起,联胜塘由原镇海(北仑)三山,鄞县的瞻岐,大嵩三公社十三个大队的数万民工开发围垦,夯实滩田。平整建设正干得热火朝天,父亲作为村代表,被抽派到盐场临时组建的指挥部工作,并又下派到盐场最前沿,具体做起了条件最艰苦、气候最恶劣的砌塘造碶闸的丈量工作。白天工作在滩涂上,与出没其间的弹涂鱼、红钳蟹为伍,晚上在用油毛毡临时搭起的屋里,躺在树桩支撑、木板铺就的床上睡觉。夏天常热得难以入睡坐起来数星星。印象里曾有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长得一脸络腮胡须,待人和蔼可亲,工作卖力有劲的三山慈东人,父亲叫我喊他为王伯伯,他与父亲是工作上的搭档。
造碶闸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暑期里来到父亲身边,白天捉鱼摸蟹,晚上就睡在油毛毡搭起的屋里,听潮涨潮落。有一天夜里我正在做梦,突然发觉有人把我背起就走,我吓得哇地哭出声来,后来父亲大声对我说:“阿良,这里潮水涨进来了,快走!到对面的大礁山去避一避!”我睁开眼睛一看,潮水已涨到床铺底下了,那一夜我伏在父亲的背上迷迷糊糊困着,直到醒来。东方已发白,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这一次的经历至今让我终身难忘,现在时过几十年,想想那时候父亲的工作是多么艰苦与辛劳。
去年春节,我带着全家老小来到春晓的洋沙山,然后又辗转十华里长的标准海塘上,看一望无垠笔直平坦的塘堤,游客芸芸,海风吹吹,真是思绪万千。禁不住又回想起过去塘堤四周荒无人烟,凄凉萧条的场景。白天尚有人上滩下涂,抲鱼摸蛏,涨网捕捞;一到晚上,海风呼啸,潮水阵阵。父亲回忆,有一年大潮汛,涌过来的浪头就盖过了碶闸房,潮声震天动地,要不是碶闸房用水泥现浇的,早就吞没了。而每年的暑寒假我都无一例外去父亲的碶闸房小住,那时的碶闸用的是钢筋水泥闸门,机械装置,没有电动;连与外面联系的电话也是手把子摇的靠人转接。开闸、关闸全凭肩挨手推。由于碶闸地处村庄的最下游,上面又多山,河网密布,地势低洼,经常要遭遇涝灾。每逢暴雨、雷雨、台风时际,父亲就彻夜难眠值班守候,寸步不离,眼盯着闸外潮水,一旦潮稍退,就立马开闸放水。闸板高2米多,父亲像赶牛车似的一圈圈旋转,常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整个过程需要一个多小时。第一、二孔,内外水位持平,水压尚不高,用手推还勉强过得去,但到海潮大落时,水位内高外低,水泥闸门仿佛有千斤重量,这时用手推就不行了,只能用肩膀一点一点挨过去。在这小住的日子里,我时常和父亲一道咬紧牙关,齐喊一二三……一起用劲相互鼓励。
每当开完闸,我觉得天地在旋转,分不清左右上下,头晕眼花不说,气喘如牛很长时间也缓不过神来,而习惯了的父亲汗水早已湿透全身。有时一天四潮,昼夜四次启闭,分秒必争,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听父亲说:“开闸放水很有科学讲究,早开不行,迟开不行;少放不行,多放也不行,要随时察看情形;有时还要掌握潮时上下间隔,大小潮等。”
长住海塘,条件艰苦,那时候自行车很少见,家与碶闸间的来来回回七八公里路途,父亲全靠两脚疾步行走,天天、月月如此。当时我们兄妹四人一家六口,只有父亲那点微薄的收入来源,于是父亲就利用荒坡、荒塘开垦种菜、种棉花来补贴家用,直至后来我们兄妹四人娶妻、出嫁用的棉花絮还是父亲一年年积聚下来的。有一年“双抢”的夏收夏种,父亲头天晚上回家里准备了翌日收割,谁知半夜里雷声阵阵、暴雨如注,父亲一骨碌从床上下来直奔碶闸,但奔到碶闸时已是水漫金山,滩田大面积受淹,损失严重,结果受到场部通报批评。但好在父亲平时对工作的极端负责,责任心很强,后来只是教育了他一下,象征性地扣了些工资。自此以后,父亲对碶闸的管理更加认真,一丝不苟,十多年下来,在碶闸管理的岗位上再未出现过小纰漏,更视碶闸如家,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嘉奖。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父亲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与碶闸相伴相守,危难与共。六十周岁时他要退休回家了,当时看他真有点依依不舍。退休后他还时刻惦记着碶闸,偶尔还会抽空跑去看看,并与接他班的人说说聊聊,真是难为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痴情。
时间过得飞快,退休了二十多年的父亲,虽然动了两次大手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看上去腰板依然硬朗,走路、说话、做事还是急吼吼,噔噔响,真是风采不减当年啊。他时常跟我开玩笑:“我有如此这般的身体,全靠这二十多年来的长途跋涉,算算路程也可绕地球一圈多了,再加上每天守着碶闸,如此吮吸着这般天然氧吧,是我延年益寿的原因吧。”
2013年元旦我又去春晓,随瞻岐镇上的一位朋友去我父亲原来工作过的那一带地方,已全面变样了……梅山港大桥的雄姿近在咫尺,沿海四车道的穿港公路笔直平坦,东海天然气源从春晓直接引入,美丽的洋沙山海滨休闲区域已初露雏形,风光无限。昔日荒凉落后的大港边陲地,如今已变成一个充满朝气、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滨海经济开发区,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崭新的城镇面貌呈现在眼前。我现在想想,也真是,到我这一辈退休回老家时,说不定,她又变样了,变得我不认得了……
谢良宏,1963年1月出生,浙江宁波人。现供职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东南商报社。热爱写作,近年来有上百篇散文见诸《中囯社会报》、《浙江日报》、《中国散文家》、《散文》、《华夏散文》、《火花》、《文学港》、《宁波晚报》、《温州日报》、《联谊报》等报刊杂志。是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