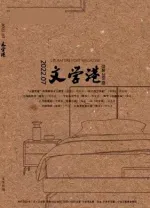遍地葵花
安庆
一
大哥说,再挖宽一点吧,让我躺在墓地里舒服;再挖深一点,兄弟,不要谁一锹就挖出了我的棺柩……大哥还在絮叨,兄弟,我走后,有什么话,你过来说说……大哥有气无力地坐在草地上,风掠过草尖,扯着他的身子。我握着锹,想象着绕村三日的哀乐,飘落在大街的纸幡,漆味浓重的棺柩,哇哇啦啦送灵的哭声。这个提前掘好墓坑的人,终有一天,要彻底和瓦塘南街告别,墓地落满飘零的黄叶。
每天清晨,瓦塘南街的人会看见大哥最早出现在村外的大路上,在路上慢跑,然后,坐在村口,有气无力地看着满地的庄稼和浩荡的葵花。
那一年,大哥对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墓地,直到有了后来的那个黄昏。那个黄昏的所见,毫不吝啬地占有了他生命最后的光阴。他先听到的是一阵小风,接着听见庄稼的晃动,随后,大哥看见了从玉米地钻出的玉露,玉露宽大的臀部闪到了大路上,融进村庄的夜景。问题是,大哥在玉露的身后看到了从玉米地里钻出的田玻璃。
庄稼在微风中摇曳,向日葵的馨香吹进村庄。听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大哥张大了嘴巴。我相信一个病人的想象会更加丰富,忽然而至的联想让大哥一阵揪心。夜色往深处陷落,我们瓦塘南街的天空忽然阴沉,遽然的大风让大哥颤栗,碎屑鸟儿一样弹满了天空。吝啬的时光正消蚀他瘦弱的身体。他裹紧身上的毛衣,捋了捋杂乱的头发,又一次看到了满地的纸幡,风在刮歪葵花的肢体。他倔倔地顶着风,佝着腰,站到了葵花地里,乱草狂卷,向日葵在风中夭折。
大哥把这场大风作为瓦塘南街不祥的预兆。
大哥纠结:玉露怎么会和一个男人从玉米地出来?
二
大哥后来无数次地回忆起他第一次看见玉露的情景:两年或者三年以前,依然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在瓦塘南街的葵花地头,大哥看见一个高大的女人和女人宽阔的臀部。壮实的女人站在恣意开放的葵花地边,葵花的缝隙结满了旺盛的野草和金黄的野菊,蚂蚱在草丛里舞蹈,草棵间镀着一个末日的辉煌。大哥远远地瞅着葵花,身子躲在一个玉露看不到的地方。正是这个叫玉露的女人让全村种上了葵花,每年再把全村的葵花卖出去,换成村里的收入,让葵花疯狂地开在瓦塘,大片的土地成为葵花的大海,瓦塘南街成为巨大的向日葵花园。大哥先看到了她的臀部,后来看到了她的目光,认准了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女人。大哥丰富的经历让他在各种人面前保留着他的沉着,直到玉露离开葵花地,大哥才随后回到村庄。
大哥跟踪过玉露。
大哥说,这个外地的女人嫁到瓦塘南街,他就开始莫名其妙地跟踪。大哥正是在无数次地跟踪后,看出了葵花的异象,这个眉宇清秀藏着锐气的大屁股女人即将为我们的村庄带来福气。大哥说,这是一个心强的女人,嫁到瓦塘南街的第二天就亟不可待地跑到了村外,幽灵一样走遍了村庄的土地,鲜红的新嫁衣荡满了泥尘。那是冬天,大地上铺满青色的麦苗,刚下过的雪还没有化尽,直到傍晚,她瓦罐一样的屁股坐在河堤上,浏览着广阔的土地。
第二年春天,瓦塘南街先是小面积种上了向日葵,在夏天来临前,我们闻到了葵花的香气,葵花的叶子在沟崖和小片的地里飘悠,风中洒落金色的花瓣,葵花照亮了村庄的天空,引来了大群的蜜蜂。接着请来了技术员,教村里人管理葵花。大哥说,他就是这时候跟踪了玉露,玉露钻进葵花地他钻进葵花地;玉露一棵一棵地数着葵花,他一棵一棵地数着葵花;玉露带着干粮,在葵花地里吃,大哥也在葵花地里随便吃点东西。直到秋天,葵花顺利地收割,大地坦坦荡荡,一望无际,玉露安生地守在家里,大哥才停止了跟踪。
大哥和我一样有葵花情结,我们都是花痴。我从小最喜欢向日葵,现在想起来和大哥有关,大哥很早就带我去看地里的葵花,那时候村里的葵花很少,星星点点,开在荒地和河滩上。我热爱葵花,它开得好看,秋天里,排山倒海的葵花籽格外香甜。大哥还带着我去看梨花、桃花,在油菜花地里奔跑,衣服染成了黄色。大哥喜欢带着一只狗,让狗和我们一起撒欢。
第二年,瓦塘南街更多的地里种上了葵花。第三年,我们瓦塘南街已经是遍地葵花,葵花浩浩荡荡,在地里疯长。
为瓦塘南街种植了满地向日葵的女人,满足了我们的欲望,我们沉浸在葵花地里,过瘾地嗅着葵花的香气。大哥的身体还好,他在葵花地给我讲他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盘葵花搞到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后来成为我的大嫂。
大哥说,我们男人可能还不如一个女人。
大哥有感而发,大哥做过村里的干部。
大哥说,我的光阴都他娘荒废了,干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
大哥说,你知道牛村的陈金莲,她是全县的强人。
我知道陈金莲,我们这一带都知道陈金莲,牛村的典型是她搞起来的,她是我们这一带的女强人,劳模,外边的人经常来牛村参观。
大哥天天这样地唠叨着。大哥坐在村口,每天等待着和我唠嗑。这个无数次说着墓地的人,仿佛找到了倾吐的方式和听他倾吐的对象,谈话越来越有魅力。大哥说他临终前,会给我讲很多的故事。
我说,那一天非常遥远。
大哥说,你不要安慰我,有时候安慰是一种欺骗。
我说,我没有说谎,我为什么要欺骗我的亲人?
大哥说,亲人最喜欢在患病这件事上欺骗。
大哥是一个活着的、时常把死亡挂在嘴边的人。
三
大哥去找文校长。
大哥说,把廖老师调回瓦塘南街吧!
廖老师是玉露的爱人,在山里教书。
大哥说,我快不行了,这是我最后求你。
大哥扶着墙,眼光迷离。校长文有福坐在他的对面,案上是一碗冒着热气的面条。
大哥说,你是咱村的校长!
文有福跷了跷二郎腿。
大哥说,我知道你和局长是同学,不然,你当不了校长。
文有福放下挑起的面条,你来损我?
对,你办不成事,我更损你。我死了,我的花圈上也要写上你是草包。
你死了,你怎么写?
我已经写好了遗嘱,我遗嘱里有,我兄弟是笔杆子,这点他能替我做到。将来关于我的传记里,也会写上你是草包。
文有福把面条倒给了他家的白猪。倒完了他哈哈大笑,笑得捂着小肚。说,于大盾,你真可笑,你笑死我了,你这样的人,将来还有传记?你要有传记,我们的乡长,局长都有传记,我们家的猪也可以写本传记。
大哥说,我为什么不能有一本传记?我的兄弟是干什么的你不是不知道,他可以义务为我写一本传记,给你们写,他要收费。
我不会写什么传记,我没有那个钱给他。
大哥说,我的兄弟在我的传记里可以把你写成反面人物,这是我兄弟的自由。
他随便写,反正我不会给他稿费,写得我不答应了,我把他告了。
大哥说,文校长,我们言归正传,还说调廖老师的事。
文有福敲着手里的瓷碗,说,问题是这事不归你管,人家没有这个意思,你多管闲事。
大哥说,我求你了,人家给咱村办了多大事啊!还不让人家夫妻在一起生活。
文有福觉得大哥可笑,说,于大盾,你真可笑,你真是多管闲事,人家这样挺好的,小别胜过新婚。我老婆天天守着我,我都心烦,她要有个工作我恨不得她离我远点,见着不如想着你知道吗?于大盾。
大哥说,你才是得便宜卖乖。
文有福站起来走走,文有福说,人家委托你了?
大哥说,没有。
那你是吃饱了撑的?
大哥说,我是快不行的人了,就想着找点事想想,给你找一个积德行善的机会。
文有福说,照你说,我还得感谢你哩。
大哥软下来,大哥说,文校长,我多管闲事了,这个忙你还是要帮,我可以让我的兄弟和你协助。
大哥扭过身,大哥说,我都倒计时了,你听我一次劝告。
文有福说,你不要老倒计时倒计时的,倒计时也是时间!你有本事你毬弄成,别成天坐在村口,无事生非,让村里人看着晦气。
大哥说,文有福,你鼠目寸光,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你干点好事,积点善德,不会折你的寿命。
文有福说,你走吧,去坐你的村口,天天坐着都坐傻了。
四
一天清早,大哥推开了玻璃的大门。
大哥说,玻璃,你扶我起来。
玻璃弯下腰,去搀大哥。
大哥说,玻璃,我走不动了,你给我寻口水喝。
大哥喝了口水。
秋深了,大哥的身上披了件薄袄。大哥说,我得往厚里穿,我身上没多少热气了。
大哥坐在玻璃家的出厦下,大哥说,我走不动了,我得在你这儿多歇一会儿。玻璃,我是一个时日不多的人了,你陪我说说话;玻璃,好兄弟,别心神不宁的,别把我丢下,我这样的人还能和你说几次话啊,今天好不容易找一个机会。
大哥喝了玻璃递过来的水有了力气。大哥喝完了水,随手把那个破碗扔了,破碗磕在一块石头上,当啷一声。大哥说,让它碎吧,我用过的碗你有疑心。大哥说,玻璃,你坐下来,我和你聊聊。大哥说,我现在老了。玻璃勉强地说了一句,你不老。大哥说,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还说不老,先走为大,先老的人不老也是个老人。大哥说,玻璃,我年轻过,年轻是啥,心不安分。那时候我是生产队长,才20来岁;当村里技术员时,才20多岁;办骨粉厂,才不到30岁;当村里的会计,才35岁。骨粉厂在河滩上,我遇到过一个女人,没有男人对女人不动心的,我每天都想见到女人,那是我不安分的日子,我几乎要疯狂了。水涨潮了,雨季,河滩也是河了,一下子宽出多宽的河床。我对女人说,我要栽下去看能不能活着出来,如果死了,我们彻底结束,如果还能活着,我再考虑。在我下河前我让她走,她拉着我但没我力气大,我跳下去了。我想让自己完,但终究活着出来了。我往回跑,我听见了女人哭,是我的女人,那个女人把我的老婆叫来了。身边没有了她的影子,从此我们就断了,她从我跳下看出我的心了。从此我天天回家,如果不是那次跳河我当不了以后的会计,可是我命不好,又得了大病,现在我常常看到的是我的墓地。
玻璃,你不要心神不定的,你是不是要去哪儿?时间已经错过去了。玻璃,你再给我倒一碗水来,我和你说话口渴得难受,可能和我的病有关,求求你,再给我倒碗水吧。
大哥喝了水,又把碗扔了,不偏不倚磕到了刚才的石头上,啪,碗碎了。
我会赔你两只碗的。大哥说。
大哥说,其实我能讲的,有好多故事。
大哥又在对玻璃讲下去……玻璃,你不要烦,心神不宁的,你安心听我拉呱,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我给你讲一讲我爷爷为什么失踪吧。可惜啊,让我连他的影子也没见过,因为一个女人,他去打仗……玻璃,再给我倒碗水吧,渴得狠啊,我会赔你家三只碗的。大哥张了张嘴,干渴让他的嘴唇起了燎泡,大哥又把一只碗扔了。大哥说,对不起啊,我把你的碗毁了,你看就因为我,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把你的碗毁了。我赔你的碗,实际上我赔的已经不是你的碗了,毁了的碗我凭什么再赔给你,玻璃,这个道理你是懂的,你是有知识的人,我赔给你的是几只新碗。大哥停了停,大哥本来想说,玻璃,再给我倒碗水喝。他忍住了,他闻到了一种香气,他陷在时间里,思考着到底是不是一股香气,难道是碗摔碎后散发的香气?大哥有些累,大哥说,容我歇几分钟再和你聊啊,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你忍一忍。大哥仰着头,似乎睡了,他裹了裹身上的薄袄。大哥几分钟后醒来,大哥说,玻璃,耽误你出门了,我走了,我还要去村口坐一坐,我每天必须从村口才能找到家门。玻璃,兄弟,我耽搁你了,听一个行将就木的人说句话,拒绝吧,成全别人。特别和女人,要离远点!你不敢轻慢啊,咱这样的村庄,针尖儿小的流言比斗还大。
大哥说,玻璃,我会赔你家三只碗的。
五
大哥进了玉米地,差一点出不来了。一场病让他两年都没有进过玉米地了,大哥看到了碎金子样的阳光照亮地上的碎草,缝隙夹进呼呼的小风。他想起一场白汤雨,哗哗啦啦把地上掘出一只只的碎坑。雨让他在玉米地迷过,雨停了,金子样的阳光照射下来,他才走出了玉米地。现在,他又迷了,别说找到玉露留下的痕迹,自己出去的方向都找不着了,一个病人的软弱,你原来并不知道。大哥想,我为什么过早会拥有这种叫病的东西,我究竟干错过什么事?缺什么德了?难道我上辈子是一个坏人?要对我惩罚?
他又一次想到自己的墓地,那片选定在葵花地里的墓地,到了最后确定的时候了。一个人在能确定自己墓地的时候,应该去看好自己的墓地,如果有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件佷重要的事情。他看见自己的墓地正一寸一寸地闪开,越来越大,快能让自己钻进去了。他在缝隙里寻找阳光,眼越来越变得模糊,脚下越来越沉重了。幸亏后来他听见了河水,他的耳朵还可以,否则,他可能迷死在青纱里了。河水最终告诉了他回家的方向,他再一次转身时远离了自己的墓地。大哥说,身体太穰了,不然会在地里找到玉露的蛛丝马迹。
那时候我正骑在自行车上,急切地往我们瓦塘南街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想到坐在村口的大哥,我大汗淋漓。我一急,自行车飞了起来,鸟儿一样掠过几个村庄,我的翅膀嗖嗖地响着,如果不是提前刹车,我要飞到瓦塘北街了,也许能越过许多城市飞到北京,再越过北京,飞到辽阔的北方,或许能飞得更远。我果然没有见到大哥,淋漓的汗水变成泪水,我站在村口,第一次疯狂地喊着大哥,大哥……大哥……我瘫倒在地。
后来,后来我疯狂地窜进了玉米地。我在玉米地里大喊,大哥、大哥……我踩翻了大片大片的玉米,在玉米地撞出一条小路。我冲到河边,又冲向葵花地,在葵花地大喊,葵花地里飞翔着麻雀和各种杂乱的昆虫,野草疯狂地生长拧成了麻花,一群羊在地里乱叫,争夺着一把荒草。我在大哥告诉我他墓地的方向,最后找到了大哥:他的头拱着地,虔诚地听着地下的声音,头发和荒草糅杂在一起,荒草地间拧出一个小坑,坑里溢出了一汪泥水,像玉米糊糊,散发出泥水的香气,他的额头泡在泥水里。他说,你不要乱我,我看到了我的墓穴,听见了墓地下的河水,你听,流得哗哗啦啦……我就要走了……兄弟……真的,有些日子你是挡不住的。我拉起大哥,淌着泪,把狼狈的大哥背回了村里。
六
关于玉露和玉米地的关系,大哥有过无数的猜测。她在玉米地里到底干啥?是不是还有另外的男人?或者她在一方庄稼的深处研究一种作物的生长,是否她的每一泡长尿都浇灌在某棵庄稼的根部?大哥无数的猜测,蒲公英一样飞翔,飞扬在我们瓦塘南街或者霓镇的故乡;葵花地生出了无数的彩虹,蝴蝶飞扬在瓦塘南街或者霓镇的上空,无数的车辆在葵花地穿梭;沧河回到了几百年前,河里游动无数的小船,花花绿绿的游客等在渡口;玉露穿行在玉米和葵花中间,鸟儿一样展开漂亮的翅膀,一种馨香雾一样在我们瓦塘南街和霓镇弥漫……
玉露之后,从玉米地走出的田玻璃,让大哥的想象遭到了打击。
大哥坐在一张铁门外,恹恹欲睡又精神亢奋,他在等待着大门打开,开始他滔滔不绝的诉说。大哥说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的面对玉露,忽然有一种心跳的感觉,这一次的距离比那一次葵花地的伫望近了几倍。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个病人的心跳原来如此巨响,咚咚的鼓点毫无理智地跳过指缝。大哥说,这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女人,她的脸盘和她的屁股一样壮硕而且镇静,宽阔和镇静得可以碾过一辆坦克。有一刻,大哥忘记了他的使命,面前的玉露玉树临风,这样不同凡响的女人一定会有难以抑制的未来。大哥受到了沉重的挫折,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他感到了生命如此的不讲礼节,欺软怕硬。大哥在一次又一次的镇静后终于开始了他预谋之中的诉说,如在玻璃家一样。大哥说,妹妹,先让我讨口水喝。大哥咕咕咚咚地喝完第一碗水后,随手一扔,碗飞过一段距离,打碎在一块石头上,碗碎声似一股遥远的音乐。大哥说,我知道你们不会再用一个病人用过的碗,你们疑心。大哥说,妹妹,我是一个没有多少时日的人了,你听我说几句吧。大哥的话如此悲壮。大哥欠了欠身,把身子努力地坐正,他没有忘记他是一个男人,在他尊重的女人面前不能丢失身份,也对对方尊重。大哥毕竟是一个有过许多经历的人。大哥瞥了一眼他扔掉的瓷碗,他又有了喝水的欲望,咽了口涶沫他忍住了。他说,大妹子,我是一个快走的人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们霓镇曾经出过一个人物,我们称她为女中豪杰,她30岁上死了男人,她守着贞节,送子参军……还有我们村的樊合家……大哥几次咽着涶沫,坚持着没要水喝,即使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时,也一直没有抬头,他有些羞怯,想不到自己会如此狼狈地来见玉露。大哥看看天上,夜幕已经降临了,很好,竟然没有人打扰,让他这个将死的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完。大哥满足地盯一眼夕阳中的光线,想着眼前这个玉树临风的女人给瓦塘南街带来的福气,吉祥物就是遍地的葵花。大哥鼻子发酸,他把对玉露的感谢化成了几句话,玉露,不,大妹子,你值得人爱,包括我。脱口而出,放出的箭,收不回去,玉露惊悸了一下。大哥说,我爱葵花,是个花痴,你帮我实现了愿望,让我在葵花地里行走,葵花的香气让我醉了一样,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又能看花又有收获的葵花好啊。原本我想看到更多的向日葵,你把向日葵种满霓镇,种满沧河两岸,光种在瓦塘南街还不够气派。大哥说,大妹子,这是我的希望,我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大哥说,可我,是快走的人了,时日不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像一只鸟儿快死时的叫声。大妹子,你是瓦塘南街的女杰,英雄!你,你不敢染半点的烟尘!这是我的心里话,今天我说出来,大妹子。我,我说的是人的名分,用官话叫什么来着——声誉!一个人活得干干净净不容易,但还是要这样活着,正是不容易才更让人尊重。大哥说,我终于和咱瓦塘南街一个有本事的女人说了我想说的话了。大哥又咽了口唾沫,他咽唾沫的声音很响,由于说话时间过长,他嘴唇干裂。大哥终于抬起来头,用恳切的目光盯着玉露。玉露一直站着,手插在裤兜里,玉树临风,稳如磐石。大哥胆怯地抽回了目光,大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终于忍不住,说,大妹子,再给我口水喝!
大哥又把一只碗扔了。
大哥说,你把我扶起来吧。
大哥等待着,他知道自己的手已如枯树般干裂。
大哥推动了铁门,晚霞中的铁门叽哽几声。大哥又回过头,说,我已经选好了墓地,就在葵花地里。
玉露不动声色送走了大哥。
七
大哥的病情再一次恶化,又住进医院。
回到瓦塘南街是半月之后,秋庄稼泛滥着成熟的气息。他坐在村堤上,对瓦塘南街感到陌生。葵花地里不断蒸腾起一层炎热的潮气,秋天的太阳亮起来比夏天更毒,夹在玉米地和葵花地间的小路更加迷茫。他的视线受到了影响,不断出现双影。每一次住院,再回到瓦塘南街,都是一种寿命的缩短,和葵花地里的坟墓又一次接近。
在这之前的一个雨天,他固执地披了雨衣走向村口,大嫂和我的两个侄儿没能拦住。他说,向日葵要被冲走了,我看一回少一回了。大哥看到了葵花在风雨中摇动,沉重的葵花在雨柱中低下头颅,葵花的缝隙流淌成一道道水沟,大雨像一道巨大的白布,犹如多日后瓦塘南街因他的死亡而飞扬的纸幡。在这个雨天,让大哥心力交瘁的是他朦胧中看到了玻璃和玉露的身影,只是在他视线里一晃,马上消失在雨幕中的玉米大地。
大哥在雨中发抖。大哥发誓,一定再找到玻璃!
那个雨天的黄昏,大哥再一次撞开了玻璃家的大门,他气喘吁吁,玻璃看见他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大哥大声地吼叫,给我来碗水喝。玻璃似乎预感到大哥的再来,给他准备了一只塑料水杯。大哥喝过水后又随手一掷,他没有听到玻璃的响声,他有点失望,这才看清是一次性塑料的水杯。大哥有些恼怒,想起还没有赔玻璃家的三只碗钱,他去兜里掏钱,又喊了一声,我要用碗喝水!
玻璃看到大哥在越发地憔悴,他回屋里又端出一碗热水,说,大哥,水烧,晾晾再喝。大哥吹了吹水里的哈气,有气无力,水里勉强地泛起几个小泡,他在雨中站立的时间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他鼓了鼓劲儿,冲出的话还是力不从心,玻璃,你听我说……
玻璃从屋里拿出来一摞的碗,又掂出了水壶。
大哥说,水……大哥把一只碗扔了。
大哥说,我会赔你四只碗的。
玻璃又倒了一碗。
大哥说,玻璃,我就是想再和你说说话。玻璃,你听我说,你是个上过大学的人是吧?你是有脑筋的人是吧?你是个有想法的是吧?玻璃,你听我说,听我说。他喘口气,说,离开这个村庄吧,玻璃!听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一句话吧,玻璃!我也算过来人了,我们已经聊过几次,道理我讲不出多少,不像你这样的上过大学,玻璃,我就给你说几句实在话吧,玻璃……
玻璃不知该怎样对眼前的人解释,玻璃又端来一碗水,递到大哥的面前。
玻璃欲言又止,仰着头,情绪复杂。
大哥去找过玻璃的父亲,这是我后来知道的。
八
大哥似乎有更多的话要对我说了。他说,兄弟,我快接近给你讲故事的时候了,讲完了就把眼闭上。我会把好多的事讲给你的……
兄弟,这样的日子快要到了,咱家就你一个有心人,你有一支笔,我只有讲给你听。如果我再一次恶化,你一定要马上赶回,你再飞一次,那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你要珍惜最后的机会。之后,人世的大门要对我关上了,瓦塘南街将与我无关,有的只是一个虚假的墓地。
大哥……
我不要谁的安慰。
大哥……
大哥再一次阻止我说。大哥说,让我歇歇。
大哥停了好久。
玉米叶儿黄了,落地的干叶正在发霉,大豆又苦又香,葵花子儿变了颜色,鸟儿的肚子撑得又圆又鼓,村口羼杂着各种成熟的气息,风儿多了,不断地吹到地里,宽大的玉米叶儿刷拉刷拉地响着,让人的心乱乱的。大哥看到了沧河,听见了河水的流动。
大哥咽了咽唾沫,抓起身边的一只水杯,咕咚咚喝了几口。大哥说,老屯镇的岳子华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比陈金莲还有名气,都是女中的豪杰。
这时候我看见大哥沉默下来,两行细泪挂上他干涩的眼角,他一只手抓住水杯。他说,兄弟,算卦人说过,我们瓦塘南街会出一位这样的女人。
你是说……
我脱口而出。
他推出一只手不让我说。他点点头,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找玻璃,天天坐在村口,甚至天天盯着那个铁门,为什么我去求文校长的原因……我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可是你和我的好多亲人要继续在瓦塘南街生活。
大哥的声音十分沉重。
你将来要多帮她!
好好干你的事业!
我拉着大哥的手。
我走后,你不用天天回来了,好好干你的工作,让头儿满意!咱村的事,多找头儿帮忙;村里人有事找你,要耐着性子,不能急躁;咱平头百姓,衙门里没人,找个人不容易,你也算进了衙门,谁找你,也是让你积德,记住哥的话……
我拉着大哥。
要多记人家的好,做事多动脑筋。
要说话和气,也别气自己,好事多往心里记着,烦恼的事,忘得快些……
我把哥的手抓到胸前,把我的头扎上去。
不忙的时候,去地里和我说说话儿。
大哥……
大哥摸着我俯下的头。
你知道为什么要你天天来陪我吗?
我听着。
大哥说,我就是要磨磨你的脾气,你性子好急。
大哥……
大哥说,我的眼越来越不行了,不过,玉米马上要收割了,也许我真是行将就木。大哥停了停。大哥继续说,吃麦不吃秋,我活得已经够长了,我算了算,咱村和我得一样病的人都过不了这个季节。
大哥——
真的,兄弟,我要告诉你更多了,把我知道的事都告诉你,毫无保留,我不能带进棺材,你再等等,这样的日子不远了。
不,大哥!
大哥有感觉,兄弟。
我想朝树上撞我的头。
大哥不说了。
大哥,那样的日子还很遥远。
我抓着大哥的手。
大哥重复着我的话,还很遥远。
人应该充满信心。
大哥看着我,其实,我就是吓唬你,我不会死的,我想看看咱村要出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第二天傍晚,我在村口没有见到大哥。我着急地看着玉米大地,大哥可能又陷在玉米地了,我要去地里找我的大哥。一小阵旋风在我面前旋动,一直旋到我的脚下,旋风消失,我看见大哥留下的一行大字:我在挖我的墓地。
我找到了大哥,他气喘吁吁,一锹锹挖着墓穴,葵花地里正在掘出一个墓坑。大哥喘着气把锹递给我,说,兄弟,替我挖挖我的墓坑。那几天,我在每天的傍晚都能在地里找到大哥,长方形的墓坑已经有模有样。大哥一直在对我说,替我挖宽一点,让我躺在墓地里舒服;再挖深点,不要让谁一锹挖出了我的棺柩。对,这里离路不远,我能听见你们在路上走,听见葵花长……兄弟,我走后,有什么话,你过来说说,多陪陪大哥。
大哥有气无力地坐在草地上,抓着一把发黄的草,风掠过草尖,扯着大哥的身子。我握着锹,想象着绕村三日的哀乐,飘落在大街的纸幡,漆味浓重的棺柩,呜哩哇啦送灵的哭声。这个提前掘好墓坑的人,终有一天要彻底和瓦塘南街告别,墓地落满飘零的黄叶。
九
玉露去找大哥那天,我没有回家。
大哥还在夕阳里等我,这是他的习惯,他每天除了早晨的慢跑,就是坐在村口。玉露不动声色地走近大哥,玉露说,于老大,我来找你要人。
大哥嘴角翕动,揉揉眼,捂住胸口。大哥说,不要吓我,我是行将就木的人了,你和我要谁?
玻璃!
玻璃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欠他几只破碗而已。
于老大,你赶走了一个对瓦塘南街有用的人。
我自己会死的,我不会被你吓死。
于老大,我不和你胡说,他一直在帮我,不,帮瓦塘南街,研究一种芝麻,你难道忘了,他的父亲曾经是霓镇的农业专家。
这么说玻璃真的走了?
你应该知道。
没有人和我告别!从来没有!
玉露把大哥搀到了玉米地。玉露让大哥听,大哥听见了河水声,还有穿过地里的小风。玉露说,你再闻闻,你闻闻这是什么?
大哥闻到了一种香气。
大哥说,哪儿的香气?
玉露说,你好好看看!
大哥说,我看不见。
大哥又被抬到地的深处,玉米地蹚出了一条小路。
大哥看到了一大片芝麻,香气从芝麻地传出来,纯正的香气让大哥沉醉。
玉露说,瓦塘南街不再单种大量的葵花,我和玻璃一直在研究和试种新品种的芝麻……美国人,日本人,包括很多国家的人都喜欢吃我们的小磨香油,村里还要建很多的油坊,成为葵花油和芝麻油的基地……
大哥闻着香气。地垄间攒动着嗖嗖的小风,玉米叶有力地响着。
很久,大哥说,和他们打交道,要格外小心。■
责编 谢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