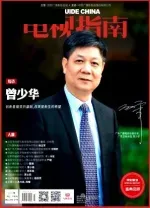漂的故事

夏天来的时候,房东让我搬家,说房子要卖。搬。从北边我搬到了东边。匆匆搬来后,我发现我搬的新家楼下,是一座放置废品的大院。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天天在这院子里生活。男人和女人的工作是把一些废品从这里搬到那里或者从那里搬到这里;(至于)那个小孩的工作则要复杂一些,他有时会哭有时会笑有时会拿着一根废铁丝走来走去。这是明显的一家三口。我原本(来)对搬到一个废品大院旁边有些沮丧,后来我对这一家三口产生了兴趣。我常常写作累了就临窗看看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两个简单的大人和一个复杂的小孩。
我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想象起他们的生活。首先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北京人,我想他们也许来自陕西、安徽或河南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来北京呢?逃婚?逃亡?逃避计划生育?但事实告诉我,事情往往没有这么复杂,也许他们就是在家乡生活得不耐烦了,出来见见世面;或者就是想挣钱。这样想来不免有些兴味索然。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男人和女人难得说上一句话,即使他们说上那么一两句,也就是“拿来、拿去”这样简单的指令性词语。当然,我是从他们口型的变化和动作的指向上来猜测的。我并不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只是偶尔女人呵斥或叫唤孩子时,会有一些声音的碎片飘来窗前又转瞬即逝。我曾经试图从这些声音里面辨别出一些什么,但终不能够。她的声音里(虽然)的确充满外省的元素,然而我更多感受到的,却是她被北京话语硬生生改变了的那一部分语音,干涩、生硬却不可分割。那女人喊孩子的声音我特别爱听,这是典型的乡村女人喊孩子的方式,充满怒气其实爱意深含。这使我常常想起几千里外的家乡和我的母亲。这样想来,就无端地觉得和这一家人有了一点亲近。我想他们肯定或多或少地和土地有过亲密的接触,尽管后来他们最终离开了它。
他们没有星期天,或许下雨的日子算是他们的星期天。这样的日子,他们就躲在院子里一节废弃的火车车厢里。那也就是他们的家。这样的家也算别致了。雨(下得)小的时候,男人会坐在车厢门口,手捏一个酒瓶,拈几粒花生米下酒。我看不清酒的牌子,但从他一小口一小口抿的动作来看,必是二锅头无疑。今年夏天雨多,男人喝酒的机会多了不少。
我喜欢看他们手上的动作。简单重复但却有力充实。更为重要的是,这动作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无疑是幸福的。我渴望自己的双手也能融入到劳动的美德中去。双手收拢庄稼。双手搬走钢铁。双手分开额前的黑发。双手敲打沉默的键盘。这是韵律、美和立体的音乐。
这一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呈现在我的视线之中。
有一天,我近距离遇见了他们。那是个中午,我到楼下的面馆吃山西刀削面。意外地,他们也在。习惯了远距离观察他们,乍一见面有些不太适应,甚至有些陌生的感觉。像一幅墙上的油画摆到了面前,能看见上面坚硬的笔触和粗糙的肌理。但我可以确凿地肯定是他们。他们一家三口,局促地坐在一张桌子旁。他们叫了三碗刀削面。热腾腾的刀削面端上来后,男人用探询的目光看了一下女人,女人说,(:)来瓶啤酒吧。女人是用方言说的,但里面掺有北京语音的元素。男人和女人和小孩开始吃面,不时往里加着辣子。男人喝酒没要杯子,直接对瓶吹。
我也要了一碗刀削面和一瓶啤酒。一瓶啤酒很快就被我喝光了。投眼瞧去,那个男人的酒却才喝下去一小半,他是在以喝白酒的速度喝啤酒。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了。能把啤酒喝得这样慢的人必然是珍惜生活的真滋味的。
吃饭的间隙,男人和女人说着话,熟练地用着外地方言。但他们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用着生硬的普通话。我想在这个孩子的口音里,外省的元素就会慢慢消失了吧。
我吃完离开削面馆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还在不紧不慢地吃着,好象生活的滋味全蕴藏在那三碗面和一瓶啤酒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