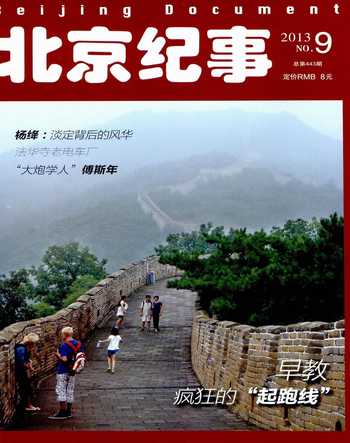我们向往的春天
刘景文
我是1964年9月入读北京师范学院的(1980年代改名首都师范大学),算来将近50年了。回忆岁月的风风雨雨,我与萧振胜同学的交往,或许也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也能透视出个人命运确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花园村
学院坐落在海淀区花园村,当年的校园周边还有很多农田。同班有一位印尼华侨萧振胜,我们同住一间宿舍。当年的萧君可是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待人诚恳、谦和,乐于助人。国内物资短缺的年代,振胜将家乡寄来的椰子酱带到宿舍与大家分享。华侨有侨汇券,他也拿来分给同学,侨汇券可以买到绿豆、尼龙袜。他虽只长我两岁,但因幼年求学辗转南北,阅历丰富,在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大哥:教我夜间暖壶里要留点热水备用,运动后大汗淋漓不要立刻脱掉外衣贪凉吹风,初次与未来的岳父母见面应注意的礼节和称呼。
我和振胜共同的爱好是文艺,尤其是音乐。他有一把德国提琴,下课回到寝室就拉上一曲,我是听众,请他演奏曾使托尔斯泰落泪的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还有莫扎特的《D大调弦乐小夜曲》。晚自习没有辅导员看着,我们就外出看演出,民主德国弦乐四重奏的音乐会、波兰玛佐夫舍国家歌舞团的演出,意大利歌唱家文图里尼的独唱音乐会,都是这个时期与振胜一起去的。文图里尼演唱的《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连托》等拿波里民歌,谢幕献花的是我们的一位女同胞,意大利艺术家很绅士地上前拥抱亲吻,毫无思想准备的中国姑娘吓得直躲。我和振胜相视而笑。夜深,我们返回校区,悄悄地踅进宿舍。
这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显得有点不搭调,于是有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传闻。当时的确让我紧张过一阵,转而一想,那也不见得是坏事呀!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俱乐部”,不正是肯定了我们师院同学崇尚自由,追求理想光明的信念吗?暂时的不理解乃至反应,我相信是出于要求进步的真诚,错不在个人,而在于那个封闭的年代。
“文革”初期我们表现出的幼稚与青涩,不愿做过多的回忆。因怕抄家,我将家里的古典音乐唱片带到宿舍,那就从这里讲一点我们的“逍遥派”生活吧。
我们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这首小提琴独奏曲是描绘、赞美春天和希望:冰雪消融,树影婆娑,春风鸟鸣。在宿舍里我们用的是手摇唱机,振胜以小提琴随唱片演奏。
然而,春天还久远吗?
汾河畔
1968年12月我们由“复课闹革命”转为“毕业闹革命”,集体到人民解放军4657部队接受“再教育”。我与振胜编在学生十五连,驻地在山西汾河襄陵镇,白天种稻子,晚上开批判会。轮到值夜站岗,身披月光,肩扛半自动步枪,枪是真的,只是没有子弹,不过已经够我们骄傲一阵子。
襄陵农村当年还没有电,我们在墨水瓶盖上凿个孔,山西的棉花不错,捻作灯芯,到连部灌点煤油,一盏煤油灯就做成了。没有灯罩的油灯会冒油烟,同学们凑近灯火读“老三篇”或是写家信,熄灯号响了,洗去鼻孔的黑烟,入睡。
农闲时同学们也有迷茫:读书还有用吗?我们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有件事体现出振胜的智慧和眼光。无所事事的我们或洗衣,或绘声绘色地演绎地下传说《梅花党》。我发现振胜常一个人低头翻看一本小红书,凑过去一看是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他在以学习语录的方式复习英语,左派也没脾气吧!他私下告诉我:眼光要放远些,我们不会总在这里,国家肯定会把我们安排到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是啊,学生连一百多号人,国家给每人每月开支四十三块五,按成本计算,大学生种的稻子谁吃得起?
1970年8月我们毕业分配,我先后在北京147中学、中国食品杂志社和民进中央研究室工作。说是四年大学本科,由于运动的原因,我们其实只读了二年基础课。不过文科的特点是不需要理工科的仪器和实验室的,找到专业教材自学也可以,钻研就无止境了,全凭个人的努力。记住了振胜翻看英文“语录”的样子和他说过的话,晚上下了班没事我就读书,补上因“文革”而缺失的专业课,为此我还到中文系廖仲安先生在宣武门内的住处造访求教过。
北京—香港
振胜在1973年移居香港,但他与北京有着割不断的情缘——华侨补校、北京七中、师范学院——他在这里度过了学生时代。因此振胜常来北京,那时我在宣武区菜市口铁门胡同有间12平米的小屋,我们买来熟食、啤酒,畅谈别后。我的唱机不再手摇,已升级为电的了,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在一间小小的陋室里再次回荡,我们都相信,春天一定能到来。
1999年11月,中央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干部到香港学习考察。振胜和同为移居香港的郭春华夫妇,忙里抽闲陪我畅游维多利亚湾。结束考察已是12月初,振胜送我到机场,在免税商店买了一件U2防寒服,他说:“兄弟,飞机降落到北京,会很冷。”
2008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振胜来京,我陪伴振胜伉俪参观了鸟巢,重访母校北京七中。2009年中文系64级校友会,他再次来京,与分手多年的同学们相聚畅叙家常,并到国家大剧院聆赏西班牙钢琴家的独奏音乐会。2010年夏,在振胜的大力协助下,我俩合作的雅俗共赏的《诗说茶文化》在香港出版,并在香港会展中心书市与读者见面。
我们向往已久的“春天”终于来了。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