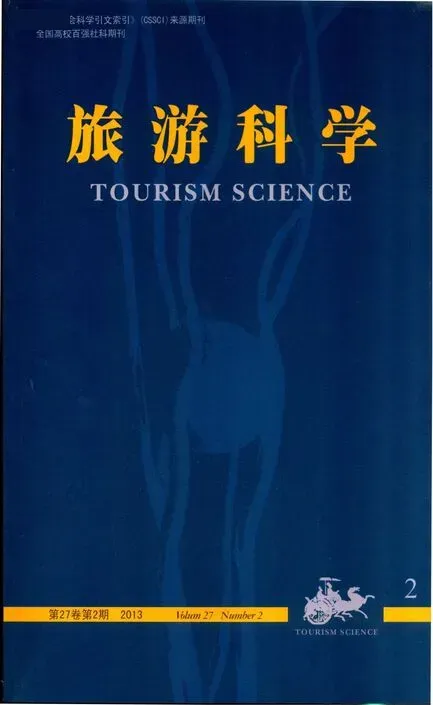国内入藏游客对西藏旅游形象感知的实证研究
甘 露 卢天玲 王晓辉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旅游业对西藏经济意义重大(徐嵩龄,2001)。当前,西藏已经将旅游业确立为“特色支柱产业”之一。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西藏旅游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西藏自治区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进藏游客达869.7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97.06亿元,分别比 2010年增长 26.9%和35.9%。与西藏旅游热不断升温相对应的是,关于西藏旅游的研究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诸多不足:资源研究多,客源市场研究少;宏观探讨性研究居多,微观具体性研究缺乏;旅游交通业研究居多,其他旅游产业要素研究缺乏;等等(陈娅玲,杨新军,2010)。关于西藏旅游形象的研究更为有限,现有的代表性研究几乎都是国外学者所作(Mercile,2005),针对的也是国外游客。而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游客仍是西藏旅游的主要市场。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内游客调查为基础,对他们感知的西藏旅游形象进行实证研究,为西藏旅游形象建设和营销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1 研究设计和数据提取
1.1 旅游形象的界定和模型
多数研究者将旅游形象定义为个体对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感知或全部印象总和,或是对目的地的一种心理的描述。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众多旅游形象的模型和度量量表。其中,Baloglu和McCleary(1999)整理有关旅游形象形成的文献后指出,旅游形象形成包括认知与情感的评估过程,将目的地旅游形象划分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三个部分。认知的评估是指对目的地各种属性的信念或认识,而情感的评估则是对目的地的感觉或情感。旅游形象的形成是潜在游客因为外在的各种信息而感知到特定的旅游地后,先经过认知的评估再启动情感的评估。而整体形象则是综合两种评估结果所得,对潜在游客来说,通常表现为旅游意愿;而对实际的游客来说,通常表现为对目的地的满意程度。该模型一方面总结了之前目的地旅游形象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对目的地旅游形象的构成和形成机制进行了科学的描述,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成为目前描述目的地旅游形象的经典模型。这一模型也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1.2 问卷调查和数据采集
本文用于调查的问卷包括4个部分:(1)旅游动机调查,在 Zhang和Lam(1999)、Crompton(1979)、Kim等(2003)的旅游动机量表基础上,结合对部分游客的实地访谈以及预调研情况,编制本研究的动机测量量表,共25个指标,采用李克特5点模糊测量法进行测量,用1代表不赞同,2代表不太赞同,3代表中立,4代表比较赞同,5代表赞同;(2)旅游形象调查,在Baloglu与McCleary(1999)提出的旅游形象经典量表基础上,根据实地游客访谈和预调研情况修订而成,其中认知形象包含24个指标,情感形象包含2个题项,整体形象包含1个题项,每个指标也采用李克特5点模糊测量法进行测量;(3)西藏代表性符号调查,包括22个多项选择项;(4)游客个人特征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来源地、入藏次数、旅行方式等。
问卷发放于2011年8月5日~15日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进行,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01份,有效率为89.3%。有效样本中,男性占60.7%,女性占39.3%;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及60岁以上分别占 5.1%、50.3%、25.6%、12.6%、4%和 1.5%;高中及以下占 18.4%,本科及大专占62.2%,研究生及以上占19.4%;职业分布中,企业职员和经商人员占31.9%,学生占22.3%,教师占10%,公务员占9.7%,其他占26.1%;来源地中,四川、广东、陕西、上海和浙江位居前五位,比例分别为 30.3%、10.9%、7.5%、6.0%和5.5%;游客中91.5%随团队出行,8.5%自由出行;81.3%的游客是第一次入藏,第二次入藏的占8.0%,第三次入藏的占4.2%,三次以上的占6.5%。
2 基于旅游动机的游客分类
首先通过SPSS 19.0中的聚类分析,在分析旅游动机的基础上对游客进行分类。首先使用Ward分层聚类,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和树状图将聚类数确定为3,继而使用K-Means快速聚类对游客进行聚类,最终将入藏游客划分为三类(见表1)。

表1 三种游客的动机特征
类型1除朝圣动机题项的均值为4.33外,其余动机题项的均值均在3.0以下,表现出单一动机特征,故可以将这类游客命名为“朝圣者”。
类型2中均值大于4.0的动机题项有1、3、6、9,体现出这类游客对西藏自然和文化景观有浓厚兴趣,而其余动机题项除少数题项均值介于3.5~4.0外,其余均小于3.5,可将这类游客命名为“游览者”,其主要目的是游览西藏的人文和自然景观。
类型3除4、11、12、13、25题项外,其余动机题项均大于3.5,且有15个动机项均值大于4.0,且所有动机题项的均值均高于类型2的游客。此外,类型3的游客除了对人文和自然景观兴趣浓厚外,还表现出对诸如寻找自我、寻找心灵家园以及逃避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与类型2游客相比,类型3游客寻求的旅游体验更为广泛和深入,可命名为“深度体验者”。
三种类型的游客中,朝圣者人数最少,仅有6人,占1.5%;游览者181人,占45.1%;深度体验者214人,占53.4%。朝圣者人数过少,不具备统计分析的意义,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为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下文中的全体游客也是指这两类游客的总和。
3 游客对西藏旅游形象的感知
依据Baloglu与McCleary(1999)对目的地旅游形象的划分,可以将西藏的旅游形象分为三类: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
3.1 认知形象
本文对游客认知形象的调查量表共有24个题项。首先进行因子分析,KMO统计量为0.867,Bartlett检验统计量值的相伴概率均为0.000,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题项共同度大于0.5以及各题项在不同因子中载荷小于0.1的标准,删除4个题项,剩余20个题项。最终提取出5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占66.34%。调查量表总Cronbachα为0.922,各因子Cronbachα介于0.600~0.921之间,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见表2)。对各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旅游设施和服务、主要旅游吸引物、旅游环境、配套旅游吸引物和宏观自然经济背景。

表2 西藏旅游认知形象的因子分析
旅游设施和服务公因子包括购物、夜生活、娱乐活动和设施、交通、旅游信息和住宿接待设施等元素。游客对旅游设施和服务的感知均值介于2.5~3.5之间,仅深度体验者对旅游信息的感知均值为3.57。这与实际状况比较吻合,即西藏的旅游设施和服务还有待提高。对比来看,深度体验者的评价要显著高于游览者,表明游客的动机越强烈、动机范围越宽泛,就越容易促使游客积极地接触和参与目的地的各种旅游活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游客的认知水平。
主要旅游吸引物公因子包括西藏的自然风景、宗教建筑、宗教氛围和藏民族风情。作为游客最关心的内容以及必访对象,游客对西藏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感知均值均大于4.0,其中深度体验者的感知均值均在4.5以上。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深度体验者的感知均值要显著高于游览者,评价更为正面。
旅游环境公因子涉及卫生条件、社会治安、政治稳定和当地人的友好程度。游客对卫生条件、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的感知均值处于3.0~3.5左右,这与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并未对这些因素形成强烈关注有关。但是,深度体验者对当地人的热情友好程度感知均值超过4.0,表明该类游客对当地人形成了更加正面的认知。
配套旅游吸引物公因子包括民族工艺品和特产、节事和民族歌舞等特色民俗。工艺品和土特产等内容因游览过程中很容易为游客所接触,因此感知均值较高,达到了4.16。节事活动和民族歌舞尽管也极富特色,但由于时间和场地的局限,很多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并未充分接触,因而感知均值相对较低,分别为3.77和3.81。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深度体验者的评价要显著高于游览者,而且对节事和歌舞感知均值也超过了4.0。
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公因子主要包括西藏自然环境的严酷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游客对自然条件的严酷性有所认知,均值达到3.64,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性感知均值只有2.88,原因在于游客大多集中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拉萨。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深度体验者对自然环境的严酷性认知程度更高,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上二者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游客对西藏旅游形象感知程度较高的集中在主要旅游吸引物上,手工艺品和特产也给游客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游客对西藏最终形成了独特、神秘、宗教氛围浓郁和异域风情的意象。其它旅游要素和环境因素在游客感知的西藏认知形象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对西藏旅游认知形象的评估存在一定的差异:游览者仅仅对西藏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感知程度较高;而深度体验者除主要旅游吸引物外,对配套旅游吸引物和当地人的友好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1所示的调查结果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游客认为最能代表西藏形象的元素包括西藏藏传佛教建筑和氛围、特殊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其中寺庙和宫殿、高山、湖泊、世界屋脊、朝圣者、蓝天白云的选择比例均超过50%,严酷的自然环境、草原、峡谷、珍稀和特有生物、手工艺品以及藏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比例也超过了30%,而其它元素比例相对较低,在游客的西藏认知形象元素构成中没有占据主要方面。
3.2 情感形象
以Baloglu与McCleary(1999)的情感形象量表为基础,设置了两个题项来对游客的西藏旅游情感形象进行度量。整体而言,游客认为西藏之行令人愉快、兴奋(见表3)。对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t值分别为-7.678和-8.117,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二者之间的认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深度体验者的认知程度明显要高于游览者。

图1 游客对最能代表西藏形象元素的认知

表3 西藏旅游的情感形象
3.3 整体形象
在旅游形象的研究中,一般以满意度来度量整体形象。结果显示,游客对西藏旅行的满意度为3.97,整体上持正面评价(见表4)。对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的独立样本t检验,t值为-6.511,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二者的满意度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深度体验者满意度均值为4.22,显著高于游览者的3.67。

表4 西藏旅游整体形象
4 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之间的关系
依据现有关于旅游形象的论述,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先经过认知评估,再启动情感评估。而整体形象是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图2)。

图2 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之间的关系
利用分层回归来考察西藏各种旅游形象之间的关系。首先以情感形象为因变量,认知形象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二步以整体形象(满意度)为因变量,分别以认知形象各因子和情感形象各题项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第三步重点考察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对整体形象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因为在认知形象和整体形象之间的一些环节中,认知形象会通过影响情感形象来对整体形象施加影响。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观点,判断一个变量的中介作用,需要经过三方面的检验:(1)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显著相关;(2)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3)因变量对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同时做回归时,要求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且当中介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或回归系数显著降低。当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到不显著水平时,表明中介变量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如果自变量回归系数减小,但仍处于显著水平,表明中介变量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4.1 对全体游客的考察
在第一步回归中,愉快感和兴奋感对除宏观自然经济背景之外的其他认知形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除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外,认知形象的其它变量对情感形象有着显著的影响。
第二步回归中,除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外,满意度与认知形象其他变量及情感形象各变量之间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除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外,认知形象其他变量和情感形象均对总体形象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因不满足判断变量中介作用的条件,因而不对其进一步考察。
第三步先对愉快感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在引入愉快感后发现,满意度对旅游设施与服务、主要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环境三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减小,其中旅游设施与服务、旅游环境在0.01水平上显著,主要旅游吸引物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愉快感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满意度对配套旅游吸引物的标准回归系数从降低到0.033,p值大于0.05,表明愉快感在配套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依此方式对兴奋感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兴奋感在旅游设施与服务、主要旅游吸引物、旅游环境和配套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考察中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见表5)。

表5 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对总体形象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全体游客)
4.2 对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的考察
采用同样的方式对游览者进行考察,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愉快感对除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外的其他认知形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在0.01或0.05水平上显著,而兴奋感对主要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环境两个认知形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也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认知形象变量对情感形象变量的影响有所差异;另外,除配套旅游吸引物外,满意度对认知形象其他变量和情感形象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均处于显著水平,表明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对满意度也存在有显著的影响。对情感形象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可以知道:愉快感在旅游设施与服务、旅游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主要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兴奋感在主要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旅游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6 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对总体形象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游览者)
对深度体验者的考察结果见表7。可以发现,除宏观自然经济背景外,情感形象各变量对认知形象其他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在0.01或0.05水平上显著,表明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影响显著;就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对总体形象的影响来看,除满意度对宏观自然经济背景的标准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余均表现出显著的回归关系,表明这些变量对满意度存在有显著的影响。对情感形象的中介作用进行考察可以知道:愉快感在旅游设施与服务、配套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主要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兴奋感在旅游设施与服务、主要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配套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7 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对总体形象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深度体验者)
5 总结与讨论
对旅游动机进行聚类分析后,将入藏国内游客划分为三类:朝圣者、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其中,朝圣者以单纯的宗教朝圣为动机,人数很少。绝大多数游客可以归类到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当中,其中游览者以西藏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游览为主要动机,而深度体验者的动机更为广泛,除了自然和文化景观外,他们的西藏之旅还包含有广泛的精神需求。
在游客对西藏的认知形象中,自然风光、宗教建筑及氛围、藏族风情这样的主要吸引物获得了高度认同,其它方面如旅游设施和服务、旅游环境、配套旅游吸引物等,游客认知程度普遍偏低。这表明西藏仍然是一个以特色观光资源为核心的目的地,旅游软环境和配套建设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就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的比较来看,深度体验者对西藏认知形象的整体评价明显高于游览者,且获得认同的元素也明显更加宽泛。
游客对西藏之行感到愉快、兴奋,表明西藏整体来说对游客产生了正面的情感体验。其中深度体验者的感受也明显高于游览者。就整体形象(满意度)来看,游客总体来说对西藏之行感到满意,然而深度体验者的满意度明显比游览者要高。
对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整体而言,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产生了显著影响,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都对整体形象产生了显著影响影响;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对总体形象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其中愉快感在旅游设施与服务、主要旅游吸引物和旅游环境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在配套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影响中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兴奋感在旅游设施与服务、主要旅游吸引物、旅游环境和配套旅游吸引物对满意度的考察中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具体到游览者和深度体验者,认知形象对情感形象的影响以及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对总体形象的影响也得到验证,情感形象的中介变量作用也得到体现,但方式有所差异。
这些结果表明,西藏旅游形象建设以后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在形象推广中,除了关注西藏独有的资源优势外,还应该关注西藏所特有的精神内涵,构建西藏旅游体验的特殊性,从而使游览者群体向深度体验者进行转变,引导他们去发现西藏更多的独特和精彩之处。
(2)提升旅游设施质量和服务水平,强化旅游环境建设,并提升诸如节事、民俗艺术和旅游商品等配套吸引物的建设。
(3)由于情感形象在认知形象对整体形象的影响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因而需要构建认知形象与情感形象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效提升游客的整体形象感知。也就是说,如何在游客对认知形象各要素的体验以及他们的愉快感和兴奋感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将会对他们的西藏旅游总体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
整体来说,本文运用Baloglu与McCleary模型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的量表比较简单,而游客对目的地的情感评估和整体感知往往复杂,特别是西藏物质景观吸引力和精神吸引力都比较特殊,这就导致量表测度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会产生一定局限。二是无论何种形象,其影响因素都是多方面的,诸如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媒体中介对西藏形象的构建和特殊的地域背景等都会对游客的形象感知产生重要影响,而本文论述不多,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1] Baloglu S,McCleary K W.A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4):868-897.
[2] 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6,51:1173-1182.
[3] Crompton JL.Motivations for pleasure vac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4):408-424.
[4] Kim SS,Lee C K,Klenosky D B.The influence of push and pull factors at Korean Nation Parks[J].Tourism Management,2003(2):169-180.
[5] Mercile J.Media effects on image:The case of Tibe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5(4):1039-1055.
[6] Wang N.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349-370.
[7] Zhang Q H,Lam T.An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ese visitors’motivations to visit Hong Kong[J].Tourism Management,1999(5):587-594.
[8] 陈娅玲,杨新军.西藏旅游研究三十年回顾及展望[J].西藏研究,2010(6):27-36.
[9] 徐嵩龄.旅游产业应是西藏经济的主导产业[J].西藏研究,2001(1):5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