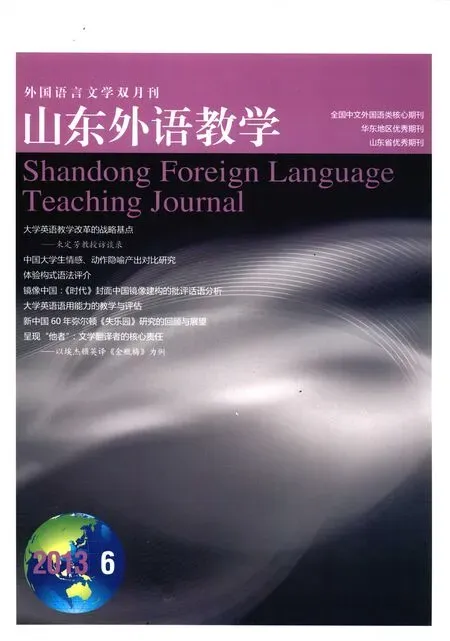呈现“他者”:文学翻译者的核心责任
——以埃杰顿英译《金瓶梅》为例
温秀颖, 王颖
(1.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204; 2.天津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Presenting Otherness: a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Literary Translator
呈现“他者”:文学翻译者的核心责任
——以埃杰顿英译《金瓶梅》为例
温秀颖1,2, 王颖1
(1.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204; 2.天津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交际行为,译者是不同文化的调停者,因此,他/她需要以恰当的策略和方法向译语读者呈现“他者”,这也是译者的核心责任。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会在译入语文化中创生一个“杂合”文本,这个“杂合”文本融合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双重特征,是两种文化妥协的结果,体现的是一种不同文 化的共生关系。本文以研究案例为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的《金瓶梅》英译本TheGoldenLotus为例,集中探讨在文学典籍英译这一跨文化交流活动中,运用陌生化翻译策略保留和再现“他者”的方法及其跨文化传播意义,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杂合”文本的基本特征。
陌生化手法;英译《金瓶梅》;异域化;混杂化;杂合文本
Presenting Otherness: a Major Responsibility of Literary Translator
1.0 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文学典籍翻译中如何运用“异域化”和“混杂化”两种翻译方法保留和再现原作的陌生化效果,从而在译入语文化中呈现“他者”,实现文学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意义。所选研究材料为英国汉学家克莱门特·埃杰顿的英译本《金瓶梅》(TheGoldenLotus,以下简称埃译本)。
我们将会看到,在翻译过程中,试图运用一种方法翻译所有的文化问题是极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探讨译者如何具体解决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移植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笔者将简略描述“陌生化”和“陌生化翻译”的理论背景。之后,从文学性角度简要介绍《金瓶梅》及埃译本。接下来,对原文和译文的陌生化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着重讨论保留原作陌生化效果的翻译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传达原作主题思想,提升译作艺术价值,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上的重要作用。
2.0 陌生化与陌生化翻译
关于到底是什么文字组合构成文学作品这一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根本不存在文学的本质,任何作品都可以进行非实用性地阅读——如果那就是把原文读作文学的意思——这就像任何作品都可以以‘诗’的方式来阅读一样”。(伊格尔顿,1988:24)而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则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乃“文学性”。(转引自Lemon & Reis,1965:107)那么,如何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这种鲜明的文学性呢?为解决这一问题,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提出了“陌生化”(defamiliarzation)概念。什氏认为,陌生化就是要对抗日常生活的惯常感受方式,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延。要“创造性地损坏习以为常的、标准的东西,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我们”,“迫使我们戏剧性地去认识语言,使这些习惯性的反应更显清新,并且使客体‘可以理解’”。(什克洛夫斯基,1989:7)
关于陌生化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初,但在此之前西方已有类似的观点,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给平常的事物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亚里士多德,1979:90)柯勒律治认为诗的任务是“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转引自刘若端,1984:63)诸多大文豪、评论家甚至美学家比如歌德、雪莱、华兹华斯、尼采、巴斯可里等都曾表示过这样的观点:“观事体物,当以故为新,即熟见生。”(钱钟书,1984:321)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本质,使得文学翻译有别于其他翻译。然而,长期以来,中西翻译界的主流倾向一直都是重内容轻形式,译者多以传递文本信息为己任,而忽视了承载信息的语言形式所具备的意义。关于这一点,谢志辉、刘庆曾于2010年专门撰文加以论述。他们在考察了从鸠摩罗什到钱钟书的中国传统译论,以及从西塞罗到奈达的西方译论之后,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和西方的译论家们虽然各个说法不同,但其思想中都有同样的倾向:“翻译就是要传达原文内容和信息,形式在翻译中无足轻重。这种翻译思想在中西方都影响深远。”(谢志辉、刘庆,2010:160)但在主流倾向之外,也有学者注意到文学作品形式的重要性,并开始强调译文要尽量保留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段。本雅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号召译者进行“陌生化”翻译,他说:“好的翻译不会寻求消除语言的异样性(外来性),相反,会允许母语接受外语的影响、扩展和陌生化。因此,译者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母语从意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在忠实法则的基础上,任其在语言流动的自由中追求自己的道路,从而改变母语的综合结构。”(转引自Mohanty,1994:28)
这样,译者一方面通过让源语“在语言流动的自由中漂流”而扩展了源语的范围,另一方面,它又在译入语文化中将其陌生化。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在其著作中的一节“翻译的影响”中提出了“陌生化”翻译原则,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翻译确实地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理解和交流,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的功能。(Heaney,1989:36)
国内有不少学者,如申丹(1995)、孙致礼(2001)、郑海凌,许京(2002)、郑海凌(2003)、陈琳,张春柏(2006)、陈琳(2010)、金兵(2009)、蒋骁华(2010)等,都敏锐地认识到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陌生化手法对保留原作的文学性发挥的重大作用。郑海凌等认为“真正艺术化美的译作,都是陌生的、奇特的,与原作有一定距离的”,这里的“距离”需要通过陌生化这一手段得以实现,这种实现无论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只要让读者感受到新奇就好。(郑海凌、许京,2002:47)同时郑海凌还从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文学的再创造性角度出发,认为译者可以创造性地、主动地采用陌生化手段传达出源语文本中的差异性特征,使译文和原作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从而弥补意义和审美的缺失。(郑海凌,2003:45)申丹认为,从文体学角度对原作中的陌生化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文学意义进行阐释,可有效避免翻译过程中的“假象对等”(即译文和原文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相去较远)。(申丹,1995:90)
3.0 埃译《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它通过描写西门庆一家及与其相关人群的日常琐碎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明代社会风俗、商业经济、官场政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清代文学批评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然而,因书中涉及大量色情描写,长期以来被冠以“诲淫”之名,屡遭批判、查禁,又禁而不止。从万历丁巳刻本问世直到今天,对它的作者、版本、人物、成书年代、创作素材、文学价值,以及它是“淫书”还是“逸典”等一系列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讨论,一直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第一部以城市市民生活为题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平凡的世情生活的长篇小说,无论是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还是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都堪称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郑振铎,2005:1067),特别是其在文学技巧方面的创新实验,如闲笔、白描、家常口语、伏笔等艺术手法的应用,更使其可与《源氏物语》、《堂吉诃德》等世界一流文学典籍相媲美。(Roy,1993:xvii)
英国汉学家埃杰顿(Clement Egerton)在老舍先生的帮助下,翻译了全本《金瓶梅》(100回),1939年由伦敦劳特莱基出版社(G. Routledge Press)出版。翻译过程中,他坚持在保持英文流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中文的精神实质。他希望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获得和他阅读原文时相同的印象,尽管这有时需要耐心,但这耐心定会得到回报。(Egerton,1979:vii-x)该译本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欢迎。1954年和1972年分别由纽约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和纽约帕拉冈出版社(Paragon Book Gallery)进行修订再版。其后又分别于1955年、1959年、1995年和2011年由格罗夫出版社、帕拉冈出版社、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N.Y.,John Wiley & Sons)、塔特尔出版社(Tokyo,Tuttle Publishing)进行再版重印。2008年,大中华文库专家委员会将其选定为中华民族文化典籍外译版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出版。下面我们就通过具体译例来分析埃氏如何通过陌生化翻译策略来落实其翻译原则。
3.1 异域化翻译
异域化翻译,是指译者通过直译的方法保留来自原文的语言、文化和文学成分,如一些新异的词汇和句法,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意象和观念以及译入语文学中所缺乏的文体和叙事手法等等(陈琳、张春柏,2006:91),从而满足译入语读者对译文“陌生感”或曰“异国风味”的需求。
例1.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你早些来时,不受这淫妇几场合气了。(第五十六回)
Hullo, my square-holed brother, my dear square-holed brother! How bright and good you look! You may make my body tingle all over. What a pity I can’t swallow you down with a drop of water. If only you’d come to me earlier, that whore would not have been so rude to me. (Chapter 56)①
这个例子运用了异域化翻译,直接保留了原文的陌生化手法。原文用“孔方兄”喻指钱币,用“……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的新奇、夸张手法,道出钱之通神使鬼,主宰一切的作用。据百度百科释义,“孔方兄”一说有两个由来。一来自于晋惠帝元康(291-299)年间文学家鲁褒著《钱神论》中论述钱的价值及功用一段:“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二来自于宋朝大诗人黄庭坚诗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无论哪种说法,都记载了中国古人对钱币的一种独特称呼,对西方读者乃至中文的现代读者而言,都具有陌生化效果。此外,爱钱爱到想要把钱吞到肚子里的表达方式同样令人感到新颖、奇特。译者通过直译保留了这一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意象和表达方式,创造性地“损坏了”译语读者对金钱及贪婪的“习以为常的、标准的”比喻,如dough,lettuce,lolly,Oscar,sugar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颖别致的意象和观念,迫使读者戏剧性地去认识这种陌生的语言方式,拉长了他们的关注时间和认知难度,从而强化了他们的审美快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
3.2 混杂化翻译
“不是所有原作中达到陌生化效果的修辞和选材取境直接转移到译入语中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陆珊珊,2009:114)如:
例2.神仙道:“请先观贵造,然后观相尊容。”西门庆便说与八字:“属虎的,二十九岁了,七月二十八日午时生。”(第二十九回)
“Sir,” the Immortal said, “tell me first the eight words of moment in your honourable life, and I will relate the future for you.” His-men Ch’ing told him the Eight Characters, saying that his animal was the Tiger...” (Chapter 29)
“使客体‘可以理解’”是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的要义之一,如果片面追求陌生感而导致表达方式的不可理解,则与陌生化的艺术追求背道而驰了。“贵造”和“八字”对当代中国的大众读者也具有陌生化效果,特别是“贵造”(称人生辰八字的敬语),若不借助于网络或相关工具书,一般读者恐无法理解。这里埃杰顿采取了异域化的翻译方法,保留了源语的陌生化,但由于该词语文化专有色彩太浓,对译语大众读者而言理解难度太大,因而不作任何解释、补偿的直译,可能不仅无法给他们带来审美快感,反而可能会打击他们阅读的积极性,从而失去陌生化应有的效果。《金瓶梅》的另一个译者芮效卫(D. T. Roy)就把这段话译为:
“May I begin having a look at your horoscope?” said Immortal Wu ... His-men Ch’ing then told him the eight characters determined by the celestial stems and terrestrial branches for the year, month, day, and hour of his birth ... (Chapter 29) (Roy,1993)
既保留了原文的陌生化效果,也有助于译入语读者的理解。
因此,当陌生化手法在译入语中无法通过“异域化”进行表现时,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选择翻译手段,如“混杂化”翻译,来保留或重构源语的陌生化效果。
所谓混杂化翻译是指翻译过程中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间的一种妥协,具体表现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源语某一语言、文化现象或文学成分采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方法,从而保留或重构源语的陌生化效果。
例3.金莲道:“贼小肉儿,不知怎地,听见干恁勾当儿,云端里的老鼠——天生的耗。”(第二十回)
Golden Lotus cried, “Why are they doing this? They are like rats flying in the skies.” (Chapter 20)
这句话是金莲戏谑春梅是个天生喜好干那种“猫儿头差使”,即奔走逢迎差使的人,明表对春梅的不满,实表对李瓶儿的怨恨。此处“耗”与“好”构成谐音双关歇后语。译文将其译成“rats flying in the skies”,应为英国英语中“flying rats”的变体。flying rats在英语中喻指鸽子(pigeon),也称sky rats,feathered rats或flying ashtrays。因为一些人认为鸽子粪便会成为疾病的传染源,同时损害财物,污染环境,驱逐其它鸟类,所以十分讨厌它们,便送给了它们这样一些绰号。这里埃杰顿在源语与译语之间进行了妥协,既部分保留了源语的修辞手法,又借用了译语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英语读者极有可能会将该句译文与“flying rats”联系起来,从而联想到鸽子及其隐喻的“令人厌恶之人”的含义,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例4. 第38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中,她在雪夜里等西门庆,和衣睡不着,低头弹唱一曲《二犯江儿水》。下面来看这一段戏曲唱词及其翻译。
1) 闷把帏屏来靠,和衣强睡倒。
I rested sadly on the lattice
Then sought my rest without undressing.
谈起戏曲唱词翻译,不少翻译家感觉很难。它之所以难译,除了源语、译语两种语言文字自身的差异以及语言各自所负载的文化差异之外,其表现形式的诗性特征(poetic feature)乃是根本原因。戏曲唱词“有诗意而不朦胧,能歌唱而忌平直,偕舞蹈而入剧情,情境一而重抒情,形象性、个性化、情绪化兼而有之”(王宏印,1998:41),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构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也为译者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两句是写潘金莲苦等西门庆时慵懒烦闷的情态。形式上,原唱词两句,押“ao”韵,译文亦为两句,不押韵,但译者运用了英语自由体诗歌插入音步的方法营造了译文的节奏。其音步节奏模式如下:
ˇ | ˇ | ˇ | ˇ |ˇ
I rest|ed sad|ly on| the la|ttice
ˇ | ˇ | ˇ | ˇ | ˇ
Then sought | my rest | without | undre|ssing
译者采用了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并以一个轻音节收尾,整句歌调呈下降模式(a falling tone),营造了夜色已深、佳人愁眠的纠结氛围,尤其是结尾处的轻音,似乎是歌者压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意义上,原词用“闷”、“和衣”、“强睡”突出金莲焦躁烦闷、难以入眠的情状,译文中译者用了“sadly”,“undressing”,“sought my rest”来对应,语义对等,特别是“sought”一词更形象地传达了“强睡”的语义效果。文化特色词“帏屏”译为“lattice”,与原文本意及意象均不对应。在原文中,“帏屏”指放置于寝居中,用于分隔空间、挡风和美观的一种木制家具,借指寝息之处,而“lattice”则指用木条制成的菱形格栅(the structure that is made of strips of wood that across over each other with spaces shaped like a diamond between them——OxfordEnglishDictionary)。但从表达陌生化的效果看,“rest on the lattice”亦能引起读者联想,并借助上下文理解其转喻意义。
猛听马蹄声响,以为是官人到来,便差使春梅去瞧瞧,原来是窗外风起落雪了。金莲提到嗓子眼的心跌落下来,又唱道:
2) 听风声嘹亮,雪夜窗寮,任冰花片片飘。
I hear the sound of the wind
The snow is fluttering against my window
And the ice-flowers drifting one by one.
原词中词末“亮”、“寮”和“飘”押韵,译文中句末“wind”,“window”和“one”押头韵,体现了音美;“snow ... fluttering”,“ice flowers drifting”,体现了动态的意美,陌生化效果明显。“fluttering”一词用得极为传神,是一语双关,既活灵活现地刻画了风雪击打窗棂的动作和声音,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风雪夜人未归”情形下闺中人坐卧不安的心情。“drifting”与“fluttering”既上下承接、又彼此呼应,风雪敲打窗棂,窗户上凌花片片飞落,一如潘金莲散乱烦躁的心绪。
金莲在这寂寥的雪夜里盼啊盼,等到灯昏香尽,懒的去续,于是接着唱道:
3) 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
I am too languid to trim the jeweled lamp
I am too languid to light the incense
这两句是整首歌的中心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说潘金莲等西门庆归来等到了百无聊赖的程度,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心情,也打不起精神,呆呆地、懒懒地静卧着陷入了沉思,过往的种种誓言与情话如今想来都毫无意义。这两句的音步节奏模式如下:
| ˇ ˇ | ˇ ˇ | ˇ ˇ |
I am too | languid to | trim the jeweled | lamp
| ˇ ˇ | ˇ ˇ | ˇ ˇ |
I am too | languid to | light the in|cense
译者采用了扬抑抑格三音步(dactylic trimeter)的韵律模式,并以一个重音节收尾,整句歌调表现为上扬模式(a rising tone),把闺房中盼郎归的无聊和烦闷推向了高潮。潘金莲就这么一唱三叹地诉说着独守空房的烦闷与落寞:
4) 捱过今宵,怕到明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想起来,今里心儿内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来没下梢。
I make shift to pass the night
Dreading the tomorrow that must come.
When I think of you, how shall my sadness end?
When I think of you, my mind is consumed.
You have despoiled my tender years, the flower of my youth
You have deserted me.
You have not fulfilled the promise you made in days gone by.
这段译文,译者先用了一个长句进行过渡,而后连用两个“When I think of you” 构成重复,并用“d”形成尾韵,发音阻滞,潘金莲满腹苦闷郁结于心,无处倾诉的意象跃然纸上;而后,由重复“You have V-ed ...”结构和选用“despoiled”、“deserted”和“not fulfilled”三个谴责含义极强的动词,将唱词人的满腔怨恨表达得淋漓尽致。
总之,这段唱词翻译的陌生化效果表现在译文内容异化和形式归化的混杂化策略上。首先,译者通过借用英语自由体诗惯用的不固定节奏(如插入音步、排比、重复等)和建行(如诗行长短交错)等内在节奏营建手段,再现原文相对一致的节奏与韵脚,弥补译文无法复制原文节奏与押韵效果的缺憾。其次,译者运用新异词语如“sought my rest”(强睡)、“ice-flower”(冰花)、“trim the jeweled lamp”(宝灯挑)、“the flower of my youth”(青春年少)和“my mind is consumed”(内心焦儿)等,保留原文文化意象和思维观念,在译入语读者头脑中形成一种模糊的意象——漫长冬夜、灯光凄凄,潘金莲独守空房,内心焦灼等待西门庆的到来,但他迟迟不归,不禁使她感慨青春已去,斯人不在。
4.0 结论
译文分析表明:
1) 埃译《金瓶梅》在实现译者所宣称的兼顾英文流畅与最大限度地保留中文精神实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译者通过异域化和混杂化翻译,在译文中较好地实现了原作陌生化效果的移植;
2) 陌生化翻译策略的应用在保留原作文学性特质、传达“他者”文化、艺术新奇性,延长读者审美感受及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功能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埃译《金瓶梅》是一个“杂合”(hybrid)文本,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均糅合了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双重因子,是中西文化互动、妥协的产物,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共生关系。
由此,推而广之,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译本都是“杂合”的结果,因为他们在本质上都是源语文本向译入语文化语境的移植物。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形式-内容”的统一性被打乱,不可避免地会对译入语施加压力,从而实现异域因素——形式的、内容的——向译作的迁移,这是保持文学翻译文学性的根本要求,也是文学译者的核心责任。正如英国伦敦大学著名学者、泰戈尔诗歌翻译家雷迪斯所说的那样,
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像是一场“联姻”。两个人——诗人和译者——带着各自的天性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与两个个体之间都有细微的差别……我们都知道生活中的“婚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但多数人都相信它依然值得尝试。(转引自Mohanty,1994:31)
这是翻译的无奈——它永远不会完美,也是翻译的魅力——它依然值得尝试!
注释:
① 文中所引用的例句除说明外均引自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1991)和C. Egerton的TheGoldenLotus(1979)。
[1] Egerton, C.TheGoldenLotus[M].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79.
[2] Heaney S.TheGovernmentoftheTongue[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9.
[3] Lemon, L. & M. Reis (eds.).RussianFormalistCriticism:FourEssays[C].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4] Mohanty, N. Translation: A symbiosis of cultures[A]. In C. Dollerup & A. Lindegarrd (eds.).TeachingTranslationandInterpreting2[C].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4.25-38.
[5] Roy, D. T.ThePlumintheGoldenVaseor,ChinP’ingMei[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6] 陈琳. 论陌生化翻译[J]. 中国翻译,2010,(1):13-20.
[7] 陈琳,张春柏. 文学翻译审美的陌生化性[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版),2006,(6):91-99.
[8] 金兵. 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9] 蒋骁华. 典籍英译中的“东方情调化翻译倾向”研究[J]. 中国翻译,2010,(4):40-45.
[10]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M]. 济南:齐鲁书社,1991.
[11] 刘若端.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 陆珊珊. 谈翻译中陌生化效果的保留[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2):112-115.
[13]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申丹. 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5] 什克洛夫斯基. 作为手法的艺术[A]. 方珊.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 北京:三联书店,1989.1-10.
[16] 孙致礼. 翻译的异化与归化[J]. 山东外语教学,2001,(1):32-35.
[17] 王宏印. 诗意与写意——《西湖遗恨》唱词英译略论[J]. 外语教学,1998,(3):41-46.
[18]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M]. 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上)[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50-87.
[19] 特里·伊格尔顿. 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 王逢振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0] 谢志辉、刘庆. 中西翻译理论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10,(3):159-162.
[21] 郑海凌. 许京. 文学翻译中的距离问题[J]. 中国翻译,2002,(3):47-49.
[22] 郑海凌. “陌生化”与文学翻译[J]. 中国俄语教学,2003,(2):43-46.
[23]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TheGoldenLotusby Clement Egerton
WEN Xiu-ying1,2, WANG Ying1
(1.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Tianjin 300204, China;2.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recognized as an act of culture-specific communication. Acting as a mediator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 translator needs to present the “other” to his/her target readers with proper strategies and methods, which is his/her major responsibility. As is observed by many scholars,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would result in a creation of a “hybrid” text, which integrates features of both the sourc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The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fromTheGoldenLotusby Clement Egerton, focuses on how a translator retains and presents “otherness” to his/her target readers in the vision of de-familiar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lassics translation, and examin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so-produced “hybrid” texts.
de-familiarization; English version ofTheGoldenLotus; foreignization; hybrid
2013-03-28
本文为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翻译改写理论视域下的《金瓶梅》英译研究”(项目编号:TJWY12-010)的阶段性成果。
温秀颖(1966-),男,教授,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翻译批评,典籍英译。 王颖,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I046
A
1002-2643(2013)06-00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