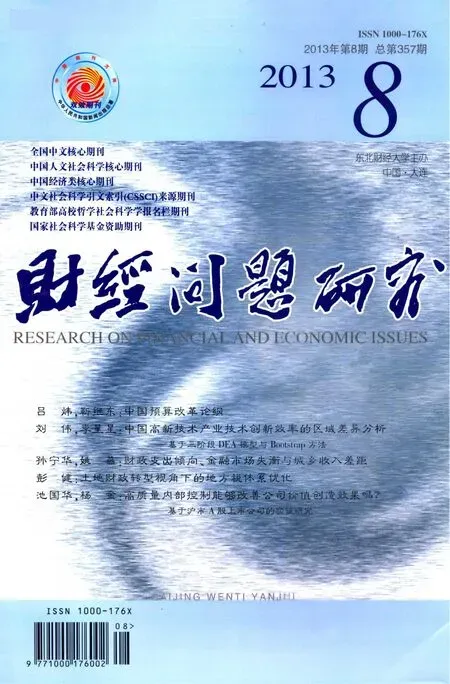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问题与监管优化
关 伟,张小宁,黄鸿星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一、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研究,国外最早是从基本的消费者保护问题逐渐延伸到金融领域的,对消费者金融保护问题的关注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随着信用消费形式的普及和消费者主权运动的兴起,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开始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注意。Goodhart认为设计一个国家的监管体制必须基于金融监管目标来考虑[1]。Budnitz重点分析解决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纠纷的方法,包括仲裁手段和诉讼渠道[2]。相比仲裁,他认为诉讼机制其实可以更好地解决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因为诉讼机制更加正式。Briault认为应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监管职能独立出来,即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3]。此外,金融监管中强调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解决金融消费纠纷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以信息不对称为起点,以强化信息披露为手段,用监管的方法制衡金融机构。
与大多数学者认为的金融监管是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最佳途径看法不同,Benston崇尚市场化精神,强烈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更不支持在金融市场中使用更多的监管手段[4]。
进入21世纪,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研究已经从理念上在监管体系中建立消费者保护的目标逐渐延伸到对具体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举措上。Hynes和Posner提出了通过强制性立法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5]。这一阶段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研究最著名的莫过“双峰理论” (Twin Peaks)的提出,该理论认为金融目标是金融监管的关键和起点,金融监管不应仅围绕审慎监管一个目标,为了追求金融机构发展和市场稳定,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应该作为金融监管的目标来实施,而且应该与审慎监管同时进行。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Lusardi和Tufano认为实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第一步是确认金融消费者的身份[6]。Tennyson认为消费者的非理性、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是需要在金融市场上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主要原因[7]。当然,Gail认为金触创新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消费者面对大量的信息无所适从,这才是需要监管当局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要原因[8]。Carlin和 Gesvais与Inderst和Ottaviani为了证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以金融中介为主体用数学模型进行推导论证,认为由于绝大多数金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分离的,而大多数金融消费纠纷都来自于销售过程,现有的金融中介机构对销售人员的激励措施过于激进,使得销售人员以谋取利益为目的欺骗消费者,从而导致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因此,监管部门应该从改革金融中介的薪酬激励制度着手保护金融消费者[9-10]。
经过次贷危机之后,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有必要设立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来承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责任。当然对这一观点也有反对的声音,Tennyson与Calvet等认为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仅需强化和整合即可,单独设置可能会引发部门利益的冲突并增加纳税人的成本。此外,将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权限集中到一个新成立的独立机构,从政治角度看可能会造成利益上的纠纷,孤立新成立的独立机构,产生监管竞争,最终反而损害消费者利益[7-11]。
我国理论界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关注相对滞后,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以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制改革为契机,而且国内大部分文献主要以借鉴英、美、日、韩和澳等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结合金融危机的发生得出国内监管机构应当加大对金融消费者保护。
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建设的理论分析方面,胡怀邦基于我国金融领域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背景,提出审慎监管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负面影响[12]。朱晓磊和姚佳从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平衡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利益关系[13]。李明奎认为次贷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监管真空,金融机构利用这些规则的漏洞,以逐利为目的将金融商品卖给不合格的消费者,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14]。巴曙松分析了美国、英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经验,认为各国 (地区)监管机构应重点加强金融商品售前、售中和售后的信息披露,完善消费者民事赔偿途径。通过完善法律救济措施赋予即使在金融交易结束后仍然保留金融机构的追偿权,同时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补偿力度,加强对消费者投诉金融机构信息的公开披露,要求金融机构披露投诉处理的进展情况,以此惩戒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监管当局通过媒体对一些欺诈案件公开披露对消费者予以提示[15]。罗传钰专门探讨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绝大多数金融领域的投资者都可以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未来,无论是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市场,都应当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提升到金融市场的监管层面,从而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维持金融消费者对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信心,从长远角度看,金融机构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提升金融业整体实力[16]。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制度建立时间短,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紧迫性却已经凸显,因此有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1.“混业商品”的出现使保护真空和保护重叠同时并存
我国现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属于典型的机构监管模式,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分别按照各自所属监管部门的要求来销售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保险和证券领域的产品及服务不再有明显的界限,这导致当前的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务不断交叉创新,综合化经营趋势日益明显,兼具银行、保险和证券属性的金融“混业商品”(Hybrid Product)不断问世,并且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在此情形下,“混业商品”与相对于单一功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保护真空 (Protect Gap)的情形。如新型的金融衍生品到底应该由投资者保护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还是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来受理?目前都没有明确,以至于真正出现纠纷时,如何解决成为问题。
从市场监管过渡到产品监管的过程中,消费者保护机构希望从源头制止对消费者可能的风险,在产品研发和销售环节进行风险控制,这就可能导致所发布的保护规定出现冲突,相同性质、相同类型的产品,在不同的金融行业内适用的监管标准却宽严不一的结果。而金融机构则发现自己必须接受不同监管者的重复监管,即消费者保护重叠 (Protection Overlap),从而加大金融机构创新压力。多头保护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一家保护机构得到足够的权限对最终产品负责,而最佳的保护时机往往因为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监管机构还需要承担促进行业发展的使命,金融机构的盈利往往是以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金融业与金融消费者长期具有合作共生性,但是就短期而言,利益冲突在所难免。监管机构基于眼前利益有可能更倾向于保护行业利益,降低消费者保护程度,以牺牲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换取金融行业的发展。当然,分立的消费者保护架构也可能会带来更有效率和市场负担更轻的结果,因为不同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会展开监管竞争。
2.分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竞次”和“监管套利”
我国金融行业的分业监管体制,决定目前的消费者保护监管由“一行三会”分别进行。这种监管体制,可能会导致各个消费者保护机构基于自身行业利益产生“地盘之争”(Turf War)。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并不一定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制定的,现实中往往是不同领域的利益集团争夺和平衡的结果。监管机构自然属于公共利益部门,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往往存在利益输送,并且消费者保护监管往往需要与受监管对象——金融机构的配合才能有效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目的,因此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受到相应金融机构的影响。消费者保护机构在确认监管范围和监管对象时往往尽可能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拒绝其他金融部门的介入,甚至有倾向去侵占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资源,这是一种监管制度的可怕结果。这种在监管领域的“地盘之争”(Turf War)最终会导致“监管竞次”现象 (Race To The Bottom)[17],即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利益集团、吸引潜在监管对象或扩大监管势力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以致降低了整体监管水平,损害了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一般来说,在监管体系中,同一个层面的监管机构越多,监管结构越复杂,竞次风险就越大。
金融消费者分业保护监管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风险是“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虽然我国目前是分业监管的格局,但是市场已经露出了混业的端倪,金融市场中很多金融商品已经开始跨行业生产和销售,而对于跨行业的“混业商品”出现消费者纠纷,一方面会导致消费投诉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多个监管机构交叉处理。而各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保护规则、保护标准甚至执行手段、措施都可能具有各自的特色,从而最终迫使金融机构改变金融商品的性质,将自身置于监管标准最宽松和监管手段最温和的监管机构管辖范围,以逃避可能的处罚。这一点在美国曾经体现得非常明显,2007年底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 (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发表题为《提高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的报告指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暴露出明显的结构性缺陷,众多监管机构设计的监管目标不同,但是对于监管对象却出现‘混同’,联邦政府和各州的监管者对同一监管对象的监管产生冲突,最终导致监管套利的发生。而一旦冲突发生,基于更高‘利益协调’就会导致相关政策延缓,最终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出现问题”[18]。
3.消费者保护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可能诱发积弊
多个监管机构分散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权力的做法会因缺乏统一协调平台而产生积弊,这种问题在目前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制下也有可能发生。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第三十五条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都预见性地提出要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条文规定:“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应当在相互之间及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或者“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但是,到底由谁牵头,何时建立起真正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迄今为止没有说法,特别是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涉及范围更广,如果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还像原来那样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不定期召开的监管联席会议,只是在政策层面,不建立法定机制,那么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协调问题就成为空谈。
当前,“一行三会”各自组建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这是一种较典型的多头监管形式。各国监管部门职责都严格限定在现有的法定职责范围之内,虽然各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职能定位明确,但是仍存在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导致问题之间的重叠、繁复甚至是互相矛盾,金融机构谨小慎微,制约金融创新,使得消费者面对利益侵害无所适从。此外,很多金融商品都属于交叉金融,而综合性金融集团是跨市场和跨行业存在的。因此,分业监管在体制上必然存在难以协调与配合等固有缺陷。如何加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职能和工作的协调,处理混业趋势下综合性金融商品与服务涉及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确保金融行业间规则的一致性,既不要重复监管,阻碍金融创新,也不要出现监管真空损害消费者利益是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关键问题。
4.法律的缺失使消费者保护缺乏依据
我国金融业从计划转向市场仅仅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时间,金融市场还有待完善和成熟。从立法理念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仍未上升到立法的高度。实际上在我国金融行业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更多地被贴上“国家”的标签,以往我国立法都是更注重对金融机构利益的保护,经常忽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至今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中没有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直接规定。与此间接相关的如《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这些法律是针对一般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于专业性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适用性不强。金融领域中的一些立法对金融消费者也有涉及,像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五条对消费者公平选择权做出规定“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在保障消费者资产安全上做出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在消费者信息保护权方面做出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收集个人金融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合理原则,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信息或采取不正当方式收集信息。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篡改、违法使用个人金融信息”,《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等部门规章一定程度上明确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但由于部门规章政出多门,不仅存在着政策空白,而且已有的规则之间也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由于在立法方面存在上述不足,实践中也没有形成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机制。而金融行业中的其他专业法律,像《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也缺乏对消费者保护的明确规定,有的也仅仅是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说明,基本没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仅有的由行业协会颁布的自律规范,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更不用说一个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法律、法规的缺失一方面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即使“有名”也“无实”。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消费者保护试点期间处理消费者投诉时的无奈。另一方面也使得消费者面对侵害时“无处喊冤”。基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在金融消费者遇到权益侵害问题时,消费者协会或工商行政部门往往力不从心。于是消费者只能向金融机构投诉,但金融机构自身投诉渠道往往基于自身利益保护使得纠纷不了了之。法院基本上不受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诉讼,即便受理,往往也是耗时耗力。而我国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和保险业协会等自律机构虽然已经成立多年,但是由于制度、机制和监管等方面原因,行业协会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作为非常有限。同时,行业协会是具有特殊利益金融机构的集合体,与金融消费者群体的利益存在天然的对抗,没有充足的动力涉足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我国的行业协会多是在监管机构的组织下建立起来的,与监管者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显然“一行三会”各自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为消费者纠纷处理提供多种渠道,但是这种安排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解决金融消费者权益问题还是未知数。此外,法律的缺失也带来对于消费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规定模糊,消费者求偿权难以保证等问题。
5.信息披露问题是消费者权益损害的关键
我国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信息披露程度明显不足,不少金融机构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即尽量多披露对销售金融商品有益的信息,而尽量少披露或者不披露对金融商品销售不利或会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信息。金融机构仅满足于信息披露的法定要求,信息披露的不完整不能算是欺诈,以此逃避法律的规定,但是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或者泛滥都会增加消费者辨别、分析信息的困难。更有金融机构利用欺诈性的信息披露和误导消费者或者从事具有利益冲突的营销。在保险业,欺诈性销售会导致消费者的退保风潮。①美国友邦保险深圳分公司于2006年1月20日,接到梁秀霞等6位客户以其购买的《友邦守护神两全保险及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存在明显欺诈内容为由,要求全额退保。事情的起因源于2005年12月一名自称买了友邦重大疾病保险的人写的一篇网络文章,梁秀霞等6名投保人看到该文后,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辉向友邦保险深圳分公司要求全额退保,并称如果友邦不同意其请求,将提起集体诉讼。在银行业,已经出现消费者向法院起诉银行涉嫌欺诈的事件。
这种现象在结构化金融商品的销售和售后信息披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伴随着新型金融市场(如资产证券化市场和信用衍生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创新型金融商品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但相关商品的开发和销售机构却没能跟上这种变化,不能及时、充分、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相应信息。再加上对创新型金融商品信息披露的尺度标准难以把握,即使披露信息,消费者也可能“误判”。于是,有观点认为此类金融商品的购买者应该排除在“金融消费者”之外,只要金融机构披露充分的信息,没有恶意欺诈和误导行为,就应该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我们深入剖析这种观点就会发现还存在问题。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 (例如金融衍生品)信息含量巨大,金融机构雇佣专业的金融工程团队,利用数学模型和金融假设,通过大型计算系统测算,金融机构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这种产品绝非一般消费者或者投资者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将这类群体排除在外,那就相当于以合法的借口认可金融机构开发复杂金融商品的先天优势,实际上是对金融机构的保护,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6.消费者金融知能整体水平较低,金融教育薄弱
金融知能,在西方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中英文表达为“Financial Literacy”,②一般教育学者将英文Literacy一词也译作素养。一些简明字典,包括 Webster New World Dictionary及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对Literacy一词的定义都是: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而在韦氏大辞典 (Webster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的定义则是:the quality or state of being literate.literate: (Webster):1.characterized by orpossessed of learning,2.verse dorimmersed in literature or creative writing,3.well executedor technically proficient.台湾地区翻译为“金融识能”,③Literacy一词,若译为“识能”,更能表现其含义。随着社会的演变,个人为适应社会生活所需具备的基本识能也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两类。第一类为传统的识能,即所谓conventional literacy,包括了读、写、算和辨识记号的基本能力。第二类为功能性的识能,即所谓functional literacy,意指个人为经营家庭和社会生活及从事经济活动所需的基本技能;也可以定义为一个群体为其成员能达到其自我设定的目标而所需的基本能力。国内有学者译为金融素养,④素养原本的意思就是平素的修养。《辞海》中对“素养”的解释是:谓平日之修养也。《汉书·李寻传》: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更有学者直接等同于金融教育 (Financial Education)。所谓金融知能,它的含义可以界定为两层:客观上的“知”即通晓金融常识,对金融法律法规了解,熟悉金融市场运作,精通金融工具的使用;主观上的“能”即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准则,驾驭自己的金融行为。具体来看,具备良好金融知能的公民在宏观层面要对国家金融政策的实施做出有根据的公共选择,应该对金融体系的运行情况有基本了解。从微观层面具备良好金融知能的公民可以较好地管理个人资源和处理好基本的家庭金融决策,例如消费和储蓄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和风险管理决策等。如果消费者具有较高的金融知能水平,自然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受侵害的可能性就减小。
就我国而言,由于我国金融业相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时间短,我国民众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商品的了解和判断程度较低,自然金融知能水平较低。但是我国民众对参与金融市场的热情却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长时间的“全民皆股民”现象。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消费商品种类繁多,消费者选择余地越来越大,金融消费意识提升较快;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能水平却较为落后,这种有悖常理的金融发展方式,必然会产生负面后果,也是导致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更可怕的是,当金融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后,缺少自我保护意识,找不到司法救济的渠道,甚至都不寻求外部帮助,这都说明我国金融消费者缺少足够有效的金融教育。因此,提高金融消费者的知能水平,普及和加强对公众消费者的金融教育势在必行。
我国的金融教育前期更多的是基于金融宣传角度进行的,如由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出版的普及性读物《金融知识国民读本》,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也发布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宣传手册》,从公众的角度让消费者了解金融常识,更重要的是了解金融风险,对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金融机构每年也集中开展“金融消费者宣传月活动”,巡回进行金融知识展览,大型金融知识讲座等,但是这些做法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我国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体系。
实际上,在金融监管机构督导下,金融机构的集中宣传活动具有明显的功利性目的,能够把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作为长期工作来做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宣传形式也流于表面,大多以挂横幅、做标语、发传单、建网站和上街咨询等方式宣传金融知识,这种灌输式教育方法,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相应的金融教育效果如何也没有反馈机制,更多的是以报告的形式证明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做了什么,做的效果无法评估。金融教育的重要意义似乎也没有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充分重视,新成立的四家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虽然都设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金融教育目标,但是如何实施,具体由谁负责,都没有配套的方案。况且金融教育本身就具有长期性的特点,仅靠一朝一夕的宣传是无法解决本质问题的。因此,我国目前缺少对金融公众教育的整体规划。
三、监管视角的优化建议
针对上述提到的六个方面问题,为优化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应主要注重以下方面:
1.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监管目标体系
政府和监管机构必须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纳入其监管目标的范畴。必须在监管理念和监管目标上确认消费者保护原则,要将原有的以经营者为本位,以金融效率为目标的审慎监管理念,转变成以消费者为本位,以金融安全为目标的监管理念。
2.建立和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
一方面,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我国目前应尽快构建和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尽快制定专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 (暂定)是一种选择。但制定专门法规时要注意两点:一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涉及到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工商管理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涉及部门多,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二是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目前处于起步阶段,缺少立法素材和经验,若直接上升到法律层次,就需要参照国外成熟的相关法规并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如果不专门立法,也可以在现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设专门一章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作出规定,至少明确界定金融消费者保护适用范围,列明金融消费者权益也是一种过渡的选择。但是,从长远来看,进行专门立法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引入集团诉讼,加强消费者保护。集团诉讼的优势在于“一人诉讼,惠及大家”,即面对类似利益受到侵害而产生损失的未起诉消费者也可通过集团诉讼获得赔偿权利,在诉讼人数的不确定和“搭便车效应”使得普通消费者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维权积极性提高,同时该制度所设定的违法成本极高,金融机构违法意愿和冲动自然获得有效遏制,所以能极大地降低金融机构因利益驱动而产生的违法行为。此外,集团诉讼制度可以推动市场诚信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在集团诉讼制度条件下,不成熟金融市场上常见的财务造假、虚假陈述、信息披露不充分、关联交易和销售误导等问题会遭到集团消费者和集团诉讼律师的监督,一旦诉讼成功,金融机构便会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法律代价,如安然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证明。
3.逐步完善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从国外发展实际来看,一般来说,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参与方包括: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法院系统。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提供了5种消费者纠纷的解决方法:与经营者协商和解、由消费者协会调解、向主管行政部门申诉、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这5种做法同样可以用于金融消费纠纷的解决。但是考虑到金融消费纠纷与一般商业纠纷的差别,其中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知识,本文建议应该遵循一定的先后次序来解决纠纷问题。对金融消费者纠纷的解决,遵循先协商,后调解再诉讼,和先内部后外部的纠纷解决次序。当然作为监管机构则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4.尽快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调机制
目前,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充分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协调职能,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下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协调办公室,专司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协调工作,其地位超然,人员构成从“一行三会”选聘,协调办公室必须是常设机构。对于事关全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比如政策、法律的制定,在相关部门制定后,由其负责最终审定提交;对于跨市场的金融商品标准的审定和群体性消费者投诉争议,由其协调各监管机构,并负责进行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交流;对于各监管机构每年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情况,由其进行汇总、公布;对于各个金融领域金融机构违反消费者保护的信息,建立数据库进行信息共享;对于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由其负责组织协调安排。最终,建立完善的部门交流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以交叉业务为契机,形成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合力。
5.以信息为核心,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
信息不对称是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诱因,信息获知权是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让消费者在金融交易时获得充分有用的信息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核心内容。金融消费者只有掌握充分的信息,才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金融机构选择正确的金融商品。要坚持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中贯彻信息披露原则,推动建立第三方金融商品和服务评价体系,以及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建立金融机构信用信息库。
[1]Goodhart,C.A.E.Financial Regulation:Why,how and where now?[M].London:Routledge,1998.
[2]Budnitz, M.E. Arbitration ofDisputesbetween Consumersand FinancialInstitutions:A Serious Threat to Consumer Protection[J].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1995,10(2):267-342.
[3]Briault, C. The Rationale for a Single 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R].FS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1992.
[4]Benston,G.Consumer Protection as Justification for Regulating Financial Services Firms and Products[J].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2000,17(3):277-301.
[5]Hynes,R.,Posner,E.A.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Consumer Finance[J].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 Review,2002,4(1):168-207.
[6]Lusardi,A.,Tufano,P.Debt Literacy,Financial Experiences,and Overindebtedness [R].NBER Working Paper,2009.
[7]Tennyson,S.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Protection Agency [R]. NFI Policy Brief,2009.
[8]Gail,H.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J].Chicago-Kent Law Review,2008,83(2):769-811.
[9]Carlin,B.C.,Gesvais,S.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 [R]. NBER Working Paper,2009.
[10]Inderst,R.,Ottaviani,M.How(Not)to Pay for Advice:A Framework forConsumerFinancial Protection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0,105(2):393-411.
[11]Calvet, L.E., Campbell, J.Y., Sodini, P.Measuring the Financial Sophistication of Household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2):393-398.
[12]胡怀邦.金融监管机构的良好治理:内控机制与外部环境[J]. 中国金融,2005,(2):21-24.
[13]朱晓磊,姚佳.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J]. 理论界,2009,(5):63-64.
[14]李明奎.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制度建设[J].中国金融,2010,(23):50-51.
[15]巴曙松.全球消费者保护:全球金融监管改革重点[J]. 资本市场,2010,(4):56-58.
[16]罗传钰.金融危机后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构建——兼议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J]. 学术论坛,2011,(2):108-112.
[17]廖岷.从美国次贷危机反思现代金融监管[J].国际经济评论,2008,(4):38-41.
[18]Brown,E.F.E Pluribus Unum-Out of Many,One: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Singl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 [J].University of Miami Business Law Review,2005,14(1):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