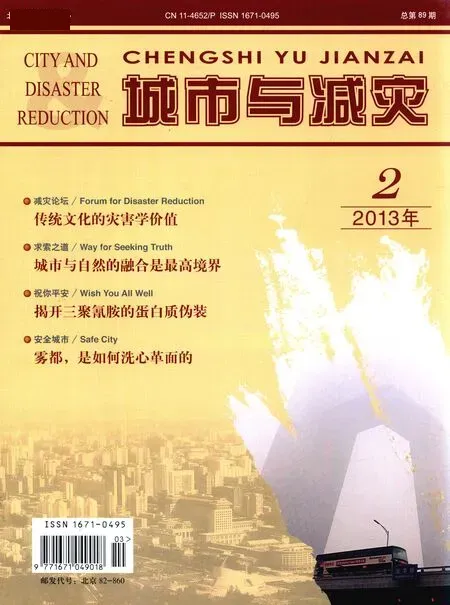蜜蜂想回家(下)
—— 保护生物多样性
广州大学 蔡亚娜
蜜蜂想回家(下)
—— 保护生物多样性
Bee wants to go home (2)
广州大学 蔡亚娜

古埃及神庙墙壁上的蜜蜂图形
人类对蜜蜂的尊崇
古代的埃及,是由两大王国组成的,即南方的上埃及王国和北方的下埃及王国,分界点大约在今天的开罗。上埃及以鹰为神,以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则以蛇为神,以蜜蜂为国徽。公元前3100年,南方的上埃及国王美尼斯(Menes)征服了下埃及王国,完成了国家统一,成为古埃及法老统治的第一王朝的创建者。
在古埃及人眼中,蜜蜂是太阳神把自己的眼泪洒布到地上的化身。埃及人还认为,蜂蜜除有食用价值外,也可预防流产,防治感染,保存尸体,所以还特别为法老王的重生,准备几罐蜂蜜为之陪葬。
在希腊,认为蜜蜂原是一位绝色美女,是古代克里特国(Crete,现在是希腊最大的岛屿)国王的女儿。据说,她曾向众神之神宙斯(Zeus)奉献过山羊奶和蜂蜜,为此,宙斯留下她化为蜜蜂。用蜂蜜酿成的蜂蜜酒被克里特人、埃及人和希腊人奉为长生之酒。雕刻在坟墓上的蜜蜂则宣告死者会复活。
公元前2000年的亚叙(Assyria)王国(今伊拉克北部),在著名人物逝世后,将其遗体涂上蜡,再用蜂蜜防腐保存。这种习俗不久就传到了希腊。
1848年,一名考古探险家在埃及古代名城阿比杜斯(Abydos)的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塞提一世(Sety I)的神庙入口十米高的横梁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图像。当时没人知道该图像是什么,直到150多年后有考古学家耸人听闻地宣布,那是直升机和潜水艇的模型!就是说,他认为在3000多年前的塞提一世时代,就已经有20世纪才发明的这么先进的装备了,然而怀疑论者认为,古埃及艺术家画在神庙墙壁上的只不过是蜜蜂的图形而已,因为塞提一世法老有个别名叫做“蜜蜂”。
我国云南的一个古老民族——怒族,自称是蜜蜂的后代,并以蜜蜂作为图腾崇拜。
我国古代周武王(约公元前1087年-前1043年)在讨伐殷纣王(约公元前1105年-前1046年)时,在他军队里的大旗(纛dào)上有“蜂群”聚集。周武王认为这是吉利的兆头,便命名这面大旗为“蜂纛”。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尽管人们不再像先人那样对蜜蜂顶礼膜拜,但蜜蜂仍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亲朋好友。千万年以来,蜜蜂默默地参与并推动着大自然的繁荣昌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文人墨客题文作画,赋诗填词,抒发对蜜蜂的喜爱,歌颂蜜蜂精神,使源远流长的养蜂事业和蜜蜂文化至今还在不断地传承与弘扬,诸如蜜蜂杂志、蜜蜂研究所、蜜蜂专著、蜜蜂协会、蜜蜂网站、蜜蜂公司、蜜蜂研讨会、蜜蜂节、蜜蜂文化节、蜜蜂权益保护组织联合体、养蜂俱乐部、蜜蜂文化馆、蜜蜂故事馆、蜜蜂博物馆、蜜蜂自然保护区、蜜蜂保种场、蜜蜂基因库、蜜蜂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医蜂疗培训班等等;还有蜜蜂之歌、蜜蜂舞蹈、蜜蜂邮票、蜜蜂影片、蜜蜂状小礼品……
养蜂业的兴起与发展
远古时期,人类的祖先从黑熊猎食野生蜂巢的行为中受到启迪,学会了猎取野生蜂巢中的蜂蜜和蜂蜡,供食用和祭祀。进入渔猎时代,人类学会了用竹丝或藤搓绳,并利用此绳索、做成绳梯,下悬到山崖或攀爬到大树,从岩穴、树洞或树梢上寻找蜂巢。其后,逐渐记住了一些野生蜂巢的处所,刻以标记,定期去采集。
古代人类不仅发现了蜂蜜是唯一的甜味来源,还知道蜂蜜具有医疗作用,也可以制酒;蜂蜡可以照明。
在公元前2600年,埃及第五王朝的寺庙里,遗存有刻着养蜂人向蜂窝吹烟驱蜂的浮雕,这是世界上最早饲养蜜蜂的史实。公元前2400多年,当时古埃及的养蜂人就已经懂得带着豢养的蜂群“逐花蜜而居”,转地放养,以增加蜂蜜的产量。
进入农牧社会后,人们把附有野生蜂窝的树段砍锯回来,搬到住所附近,无需管理,任其自生自灭,让蜜蜂生活在半野生状态,以方便采集蜂蜜。逐渐地,人们又学会了使用各种容器,如木桶、陶罐、笆篓等收容蜂群,天长日久就把蜜蜂从野生状态驯养成家养的昆虫。后来,各种新式蜂箱、蜂具的发明和生产;使用和管理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养蜂业无论在规模或收益等方面都在蓬勃发展,成为现代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洲是人工养蜂较早之地。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约前560),在公元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第一任执政官时期制订的法律中,就有“新建蜂场不能建在原有蜂场的300码以内”的规定。说明当时的养蜂业已相当普遍。
我国也是养蜂古国,养蜂记载颇多,现仅摘述几则于下:
我国先人们驯养蜜蜂,较之驯养鸡、鸭、鹅、狗等动物要迟得多。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在狩猎中击毙了那些动物的父母,然后把幼禽或小兽捕捉回家,逐渐驯化;但是由于蜜蜂是群居的昆虫,故无法将幼蜂带回驯养。
经过我国昆虫学界泰斗周尧教授(1912-2008)的考究,在3600年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蜜”字和“蜂”字。至于这个“蜜”是来自野蜂,还是已被驯养的家蜂,就无从查证了。
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礼记·内则》云:“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说明早在2300 年前,甜美的蜂蜜就被用于孝敬老人和长者。
越国著名政治家范蠡(约公元前536-前448年)尽其全力侍奉越王勾践(公元前496-465年)治国用兵。在灭吴雪耻后,他功成身退,结庐而居,道德经商,著书立说,被后人尊为儒商之鼻祖。在他的著作《致富全书》中,就记有养蜂、采蜜、收蜂、驱害等方法,说明我国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养蜂技术,并指出了养蜂致富之路。
西晋医学家皇甫谧(公元215-282)撰写的《高士传》中,收录了91位高士的传略。所谓“高士”,指的是志趣、品行高尚出俗之士,多指隐士。其中,第88位记载的是东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年)汉阳郡上邦县(今甘肃天水)名士姜歧,“隐居以蓄蜂”,为中国养蜂之始,并被公认为是我国古代养蜂第一人。姜岐不仅自己爱蜂、养蜂,还招收学徒传授养蜂技艺,先后达300余人,说明这时已经出现了人工养蜂和以传授养蜂技术为职业的专业养蜂人员。
西晋文学家张华(公元232-300) 编撰的《博物志》中,也有我国家养蜜蜂的确切记录。到了唐宋之际,养蜂已能盈利。大约到了宋代后期,就逐渐走向普及了。宋朝罗愿(1136-1184)撰写的《尔雅翼》,记载了蜜蜂的种类及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而清朝郝懿行(1757-1825)的《蜂衙小记》,则是我国最早的养蜂专著。书中关于蜜蜂的形态、生活习性、社会组织、饲养技术、分蜂方法、蜂蜜的收取与提炼、冬粮的补充、蜂巢的清洁卫生以及天敌的驱除等,都有所叙述。
至于我国将蜂蜜作为药用,始载于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成书于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由于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故撰人不详。在《本经》中,蜂蜜又被称为“岩蜜”、“石蜜”、“石饴”、“蜂糖”,被视为珍贵的上品,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奢华的体现。例如,从商周时期开始(即公元前17世纪),就有用蜜做蜜栗、蜜枣的记载,而且实际利用蜜糖的时间,肯定比文献记载得还要早。在古文献中常可见到“蜜”多被用作贡品,或是作为国君赐与臣下的赏赐品,或是诸侯国之间互相交流的社交礼品的记载,是“特供”珍品,专为宫廷和贵族享用。
三国时期,蜂蜜用于制作清凉饮料和浸渍果品,用于解暑。《魏志·袁术传》记载,三国时代的著名人物袁术(?-199年)称帝后遭众人围攻而惨败,时值盛暑,袁术要喝蜜水而不得,竟被活活气得吐血而死。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也有相似的经历,晚年,因口苦而求蜜,结果不得,也忧愤、抑郁成疾。
直到唐朝,蜂蜜仍是珍稀之物。宰相杨国忠(?-756年)为了取悦杨贵妃,用炭屑混合蜂蜜做成了龙凤呈祥的雕饰摆件,令人啧啧称奇,被视为贵重的工艺品。
不过,开创中国近代养蜂事业的先驱,是清末秀才张品南(1879-1927)。光绪21年(1895年)应县试中秀才,后在家乡办学执教,并对养蜂情有独钟。1912年,他赴日本学习活框养蜂技术,回国后,毕生致力养蜂技术的研究与推广,为我国引进了国外的优良蜂种、科学的养蜂器具和技术,在福建福州首创了“三英蜂场”,开启了国产蜂王外销的先例。他的朋友和学生,或受其影响,或受其培训,很多都成为我国养蜂界的前辈名人。
新中国成立后,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1886-1976),在1959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于1960年1月16日给中共中央和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提出应加强对蜜蜂的研究和普及(全文见《蜜蜂杂志》2012年6期)。
197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委托华国锋给西藏带去《养蜂促农》彩色科教影片,借以推动西藏的养蜂事业。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1915-)是中国蜂产品协会的名誉会长。他在87岁高龄时还明确指出:“发展蜜蜂产业是利国、利民的重任。”
奥地利生物学家弗里施(Karl von Frisch,1886-1982),1946年因为破解了蜜蜂舞蹈传递食物信息的秘密而获得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人们受蜜蜂的启示,将蜂巢这种最节省材料、空间容量最大而又最坚固的力学结构,广泛用于飞机、火箭、宇宙飞船的设计和制造;还复制蜜蜂的视觉导航技能,应用于探测火星无人驾驶飞船的导航。这些都是航天工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

野蜂的蜂巢

养蜂业
人间“蜜月”的由来
谁都知道,新婚后的第一个月叫“蜜月”,新人的柔情蜜意,当然不在话下。只是这个“蜜”不仅仅指的是甜蜜,还和蜜蜂有点关系哩!蜜月的英语单词 honeymoon就是由蜂蜜(honey)和月(moon)组合而成。
据说,“蜜月”一词起源于公元500年前的英国。当地,有个名为条顿(Teuton)的少数民族,素有抢婚习俗,任何一个条顿族的青年男子都可以抢一个自己中意的本族姑娘为妻。为了避免别人再把自己的妻子抢走,于是不少男子将姑娘抢到手后,就迫不及待地携新人外逃,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因此,很多外逃夫妻,游荡于荒山野岭之间,食宿无着。有幸的是山林中野蜂窝随处可见,蜂蜜唾手可得,可聊以充饥。后来,条顿族的首领,定了一个法规,不管是自愿的、还是抢来的,结婚30天以后就不能再抢了。这样,新婚夫妻在野外,靠着蜂蜜的滋养,一个月后,就可以安全回家,厮守终生了。由此,就把外出躲避的这个月叫做“蜜月”。“蜜月”的说法慢慢地由英国传到欧洲,久而久之,流行到世界各国,演变成了新婚度假的代称,被人们愉快地称之为“度蜜月”。
在古代的俄罗斯,有一习俗:要为年轻人的婚礼特别制作一种浓度较低的蜂蜜酒。新人不仅要在婚宴上喝蜜酒,而且在婚礼举行后的一个月中,每天都要喝蜂蜜酒和蜂蜜水(在此期间新人是不允许饮用其他烈性酒的),这也是俄罗斯“蜜月”一词的由来。
“蜜月”的不同版本还有许多,当然都与蜜蜂或蜂蜜有关,这里就不赘述了。
蜜蜂想回家
生物,一般都有自己的住处,这是他们的家。诸如:鸟巢,狗窝,蛇洞、羊棚、兔窟、牛栏、猪圈、马厩、虎穴、鸡舍、蚕匾、蜂房等等,无论它们飞得多高,跑得多远,最后都能准确不误地回到自己的家;就连植物,也还有“落叶归根”的说法哩。
蜜蜂原是一种有强烈归巢本能的昆虫,可是如今的蜜蜂,就像有人患上了“失忆症”似的,这些以“恋家”出名的小虫,不仅无奈地不识归途,还消失得无影无踪!
蜜蜂的家不是空巢家庭;不是单亲家庭、丁克家庭、残缺家庭;也不是仅由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且不是由父母和已婚子女组成的主干家庭;更不是四世同堂的联合家庭。蜜蜂的家,以群体的方式生存,过着一种母系氏族的生活。这是一个团结互助、纪律严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温馨和谐、生机勃勃的家。通常,在一个蜜蜂的家(蜂群)里,有着数以万计的工蜂(99%是工蜂),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蜂王(或蜂后),和数量不多的雄蜂。
蜂王唯一的职责就是传宗接代,她一生就像一架产卵的机器;至于短命的雄蜂,那简直就是超级情圣,除了负责交配外,无所事事。
而工蜂,则是蜜蜂家里的“苦力”,是效忠蜂王的“臣民”,更确切的说,她们都是蜂王的女儿。虽然都是雌性,但性腺退化,不会生育。工蜂在其短暂而又忙碌的一生中,不仅要采粉、采蜜、采水、侍奉蜂王、养育幼蜂,照顾雄峰,还要包办该“蜂家”里里外外的一切事务,包括食品的采集,蜂巢的建造与维修,巢内温度湿度的调节,卫生、保安、抵御敌害等工作,全部由工蜂负责。她们白天不辞辛劳地到野外去寻觅、采集、搬运花粉回家;晚上还要加班加点、细心制作;她们恪尽职守,从不懈怠,最后默默无闻地累死在工地或路途。她们为了“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在蜜蜂的社会里,没有文字、没有教科书,但它们凭借着遗传的本能,以身作则,尽善尽美地把各项职责和技艺代代相传。
现在,工蜂们莫名其妙地回不了家,家成了空巢,留守的蜂王和幼儿被活活饿死,家就没了。想想看,回不了家的工蜂们,该是何等地牵挂、惦记着家中的一切,又是怎样地担忧、焦虑和伤心!
拯救蜜蜂在行动
蜜蜂,原因不明地大量消失,引起了世界各国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拯救蜜蜂,已刻不容缓。在美国,已经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研究,试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2007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播放了一部《沉默的蜜蜂》记录片后,使得养蜂在美国成为了时尚。许多家庭的后院、公路的两旁,常可见到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蜂箱,养蜂俱乐部的成员数量急剧上升,许多新的养蜂俱乐部也在先后形成。原有传授养蜂知识的人,现在成了香饽饽,人们自得其乐地把养蜂称为“绿色休闲”。因为,民众为美国蜂群数量持续减少而担忧,希望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
“谷歌(Google)”目前被公认为是全球规模最大、并且是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据2011年5月国外媒体报道,“谷歌”已向非核心业务进行了十大项怪异的投资,如向风力发电厂投资、进入能源市场、养蜜蜂等。在谷歌总部,有正式员工专职养蜂,照料蜂箱。虽然这项投资并不昂贵,但足以表明“谷歌”对“蜜蜂消失”这一事态的重视和积极参与。
欧洲议会于2008年批准在欧洲范围内建立蜜蜂“恢复区”。“恢复区”是未经开垦的绿地,将会有数量众多、品种丰富的含有花蜜和花粉的植物,而且不使用化肥和农药。2010年12月6日,“欧洲联盟”又出台了一项拯救蜜蜂的行动计划,该计划涉及范围之广,保护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其内容包括:一、设立研究项目,搞清蜜蜂死亡的真正原因,并调查清楚蜜蜂死亡的严重程度及后果;二、鼓励发展养蜂业,对养蜂人进行培训;三、成立蜜蜂健康研究室,提高蜜蜂的身体素质;四、修改欧盟相关法令,禁止对蜜蜂有害的农药进入市场;五、就保护蜜蜂加强国际合作。
2010年8月18日,约500名英国国家青年剧院的演员在伦敦巴特西电站(Battersea Power Station)前进行表演,呼吁人们关注由蜜蜂种群减少带来的全球环境危机。
目前,我们的蜜蜂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我国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有关机构及公众都在有所行动。2010年12月,农业部编制了《全国养蜂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了养蜂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2012年4月,广州从化市的政府部门还下达“红头文件”开展全民爱护蜜蜂大行动,成为全国首创。
……
应该说,无数的地球人,都在关注着这群危难中的生灵,努力帮助蜜蜂回家团聚。归根结底,这也是在拯救我们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