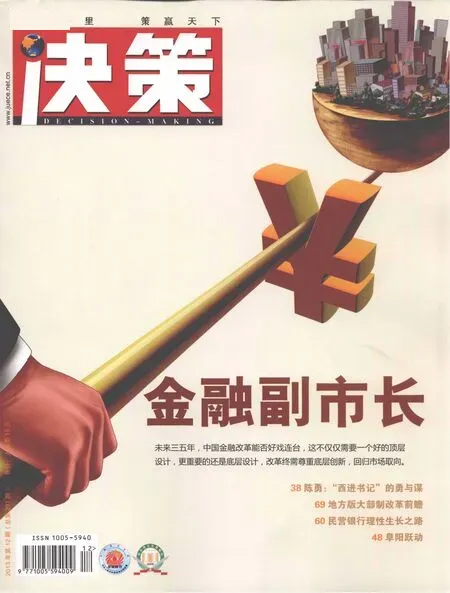宋代“官不修衙”的制度安排
■刘越藩 刘明泉

两宋时期,地方官想要修缮官衙就不那么容易。探究其原因,首先是大宋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官不修衙”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层面上筑起了擅自修缮官衙、从工程中捞油水的防火墙。
在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是比较愿意修缮衙门的。比如唐代的李听当节度使时,发现衙厅长时间不利葺修,都要倒塌了,立刻就无所顾忌地“命葺之,卒无变异”。李听之所以一刻也不耽误地使人修缮官衙,既可以拿到工程回扣,也可以享受良好的办公条件,否则作为节度使的李听,绝不会有这样的利益冲动。
可到了两宋时期,地方官想要修缮官衙就不那么容易了。探究其原因,首先是大宋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官不修衙”的制度安排。
从制度上筑起“防火墙”
根据相关规定,宋代的地方官要修缮衙门,必须报请中央政府审核、批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即在大宋建政不到60年,朝廷又进一步明令地方政府“无得擅修廨舍”。这就是说,各级政府不得擅自修缮官衙。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大宋朝廷又“诏京城内外除修造仓场、库务、店务、课利舍屋外,自宫殿、园苑以至百司廨舍、寺观等,并权停。过七年取旨”。也就是说,京城内外官家的楼堂馆所一律暂停修建,等七年后看国家财政状况再说,因为政府要优先建设仓场(贮存粮食的仓库)、库务(国库)、店务(公租房)、课利舍屋(税所)等公共项目,为民生和经济建设服务。
如果地方官不遵守规定,私自修缮官衙,必将受到弹劾和撤职、降职处分。所有这些,都从制度层面上,筑起了擅自修缮官衙、从工程中捞油水的防火墙。
当然,这也不是说宋代所有的官衙,不管多么破旧都不进行修缮。宋代修衙之事,还是能够见诸相关史志的。但总的来说,宋代地方官员对修衙之事都不太热心,很少出现大建楼堂馆所的热潮。
不过,官衙如果太破败了,地方官员也可以申请修缮官衙的费用,朝廷经过严格审核后,方能在一般性行政经费中划拨。但官员给朝廷打报告时,需要着重强调本地的官衙如何破败不堪,已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而且还要反复保证修建过程中不会出现强迁扰民之事。不过地方官员申请归申请,可是要批下来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大宋朝廷在官衙修缮的制度建设方面,确实比较完备。
苏轼在杭州的“囧事”
宋朝政府,一直是个“小政府”,财政规模非常有限,朝廷没有修缮官衙的专门预算,因此地方官想要修官衙,工程立项异常困难。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大文人苏轼到杭州履新,担任通判一职,这是相当于副市长的职位。虽然他任职的是美丽天堂杭州,却看到这里的州衙屋宇“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这就是说,苏轼每天从官衙的墙边通过,很怕严重倾斜的房屋把自己掩埋掉。就这样,苏学士在惶恐中当了三年的杭州通判,直到改任他职,州衙也没有得到些许修缮。十多年后,苏轼重回故地。这一回朝廷让他担任了知州,也就是杭州的行政一把手,但他发现破败的州衙依然没有得到多少修缮。就在苏轼履新杭州的那一年六月,州衙的房屋终于倒塌了,还压伤了衙门的两名书吏;又过了两个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就是杭州官衙,屡屡出事,致使公务员及其家属狼狈不堪,人心惶惶。
没办法,苏轼只好向朝廷打报告申请拨款修缮州衙,并反复说明了修缮的理由:“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尽管苏轼将州衙危房描述得如此形象传神,可报告打上去,竟然被朝廷拒绝了。
第二次再打报告,聪明的苏东坡事先设计了一些变通的办法,不过也仅仅批准了很少的钱,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廉政爱民的苏轼,并没有因此抱怨朝廷不给自己面子,因为他知道:“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没办法朝廷真得很缺钱,况且还有制度管着。
在杭州任上,苏轼主持修建了一处大型公共工程——西湖苏堤,所用的款项和劳工远远超过了修缮官衙的规模。因为苏堤首先是为疏浚西湖而构筑的,故苏学士这样做,不但没有受到弹劾和降职处分,还作为“西湖十景”之首,为属地的后辈们编织了一个千年不朽的旅游钱袋子。
强行修衙的严重后果
在宋朝,官吏若强行修衙,不光政声受损,还可能受到弹劾和撤职、降职处分。
诚如前所言,宋朝政府收取的税银,主要用于建设仓场、库务(国库)等公共项目,修缮衙门的工程通常会被列为“不急之务”,远远排在其它公共工程的后面,更难被当作政绩工程或首长工程来夸耀。既然如此,官员也就不能拿城市的土地当作商品来经营,并把经营所得用来修缮官衙,因为这是制度所决定的。
比如,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杭州知州薛映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即在知州任上擅自修缮官衙,于是朝廷马上派遣御史去调查,一查,果然如此。马上交大理寺议罪,于是薛知州就从省级行政一把手,被贬为“连州文学”,即很小的一个地方闲职。其职务收入和职务消费,自然也比当知州时差远了。
宋仁宗时,汝州知州李寿朋因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同样被御史所弹劾,当然也受到了降级使用的处分。
还有一个因素,是限于当时的施工水平,工程进度一般比较慢,官衙修缮一般工期都比较长,官员很难得到实惠却很可能招来骂名。大宋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得极严自不难理解,那么地方官员为什么也不热衷于修衙呢?给自己整一个豪华气派的办公场所,不是很舒服很惬意吗?工程立了项,大兴土木,使钱差役,不是还可以为自己捞些回扣吗?
大家知道修缮衙门,难免要劳民伤财,招募或征调民力。在宋代对公共工程招来的民工都要雇佣付款。可官府资金紧张,很多时候会无钱支付,若因拖欠工程款闹出事儿来,就可能影响官员们的前程。比如王安石执政时的三司使韩绛就曾说过:“害农之弊,无出差役之法。”为了免除杂役,减轻农民负担,令其安心农业生产,于是王安石接受韩绛的建议,致使“募役法”在1071年正式颁布实施。
修缮衙门,既然难免劳民伤财,所以宋代的官员们都不敢大兴土木。而且那时的官员任期又比较短,不过三五年而已,限于当时的施工水平,工程进度一般都比较慢,故此当时的官员,都不愿意自己费劲修缮衙门,没享受几天就由后任来乘凉。如果当时的官衙确实破败,地方官吏宁可自掏腰包小修,也不愿为人作嫁,给自己找骂。比如苏轼修缮杭州官衙时,除了从僧人的度牒中想办法外,还捐出自己的“公使钱”五百贯。公使钱是宋朝财政拨给地方长官的特别经费,由官员自主支配,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是无须用在修缮衙门的事项上来的。
应该说“官不修衙”的制度,在宋代发挥到了极致,有时甚至倒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不过这种好传统却影响到了后来的几个王朝。紧随其后的元代,固然没有什么吏治可言,可在明清两代近600年的时间里,“官不修衙”的制度还是执行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