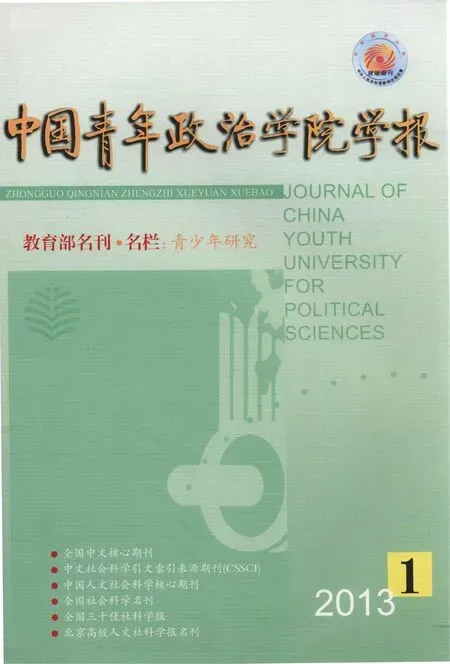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多维性社会适应研究
赵 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北京100089)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领域,积累了部分的研究成果,但其中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梳理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多数是基于人口密集、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民工进行研究,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深圳的“平江村”研究,以及周大鸣等人对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带的农民工研究,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关注较少。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多数是把不同行业的农民工集中在一起,作为统一的农民工整体笼统地加以介绍,强调农民工同质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差异性,没有对特定行业农民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是一个异常复杂多元的群体,内部也在不断地分化。农民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同时期的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很大,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笔者将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外出打工的群体称之为第一代农民工,而第二代农民工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即新生一代农民工。本文的研究对象——安徽搓澡工,正是新生一代农民工的一分子。他们来自安徽阜阳市临泉县,生活在人口并不密集、经济欠发达的三线城市——Y市,从事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搓澡服务行业。
因此,本研究以生活在Y市的安徽搓澡工为研究对象,运用建构故事的叙事手法,从经济层面、社会交往层面和心理层面讲述这一群体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并通过对这一过程的阐释和分析,试图归纳出安徽搓澡工的社会适应过程所呈现出的特征。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丰富对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农民工群体的研究,避免社会对农民工“边缘群体”、“弱势群体”标签化的认知模式,很好地呈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新特征、新趋势。
二、研究发现
鉴于本研究从社会网络和关系建构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进行考察,笔者将社会适应定义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环境,并具备从这一环境中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使得自身在城市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从外延上看,这种社会适应包括三个方面:经济适应、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
(一)经济适应
相对于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经济适应最容易实现,也是最先实现的适应。事实上,搓澡工一到城市就已经开始经济适应的过程了。在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职业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
1.初来乍到:生存
多数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都是为生存压力所迫,他们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不仅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都难以保证。尽管他们在城市里大多干的是“苦、脏、累”的工作,但是他们获得的收入远远高于农村,至于能否赚钱致富,他们并不敢奢求。搓澡工刘凤琴在来Y市搓澡之前,和丈夫马老二在广州收破烂儿,说起为什么随同丈夫到Y市搓澡,刘凤琴说:“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刚分完家吧,两个人过日子,农村农田需要施肥料,都没有钱买肥料,孩子喝奶粉都没有奶粉钱。当时就想,最起码给孩子挣个奶粉钱,也没想挣什么大钱。”
我们可以把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定位为流动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频繁地变更工作地点,变换不同的职业。他们最初并没有驻扎在某个地方的想法,而是为了养家糊口来到城市,生存理性是这个阶段的主要选择。
2.安营扎寨:生活
当初,一年仅靠卖大葱赚了220块钱的刘凤琴做梦也没有想到,经过几年的打拼,他们不仅在Y市的黄金地段买了房子,而且两个孩子也能在城市接受教育。现如今,搓澡却能在物质上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丈夫马老二说:“这职业还行,一个月能兑付好几千块钱。现在淡季时1000多块钱,旺季3000来块钱。加上我爱人也搓澡,现在一年能攒下3万多块钱,现在没啥大买卖做,靠两双手勤劳,也只能这样了。”
经笔者了解,与Y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比,搓澡工的收入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这个意义上,稳定的工资收入以及较高的相对经济位置是搓澡工们在此安营扎寨的根本动因。如果把搓澡工初来乍到的阶段定位为流动的话,那么他们在城市里安营扎寨的阶段就是准备融入城市生活的迁移阶段。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搓澡工已不再是频繁奔波的“流民”。他们打算稳居在工作的城市,不再为了生存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二)社会交往适应
1.关系的存续:和同乡的关系
在乡土社会,同乡仅仅指同一村或同一族的人,而在同一个城市聚集以后,同乡成了一种颇具弹性的、泛化的、模糊的概念。小到同村的、大到同镇的、同县的都可以叫同乡。先赋的老乡、亲戚的“强关系”不仅继续存续,而且随着交往的密切,这条“关系链”会在异地变得更加紧密。甚至原先毫不相识的同乡会因为同在一个地方、同一个“圈子”工作,而有了更多的交往机会。和其他安徽搓澡工一样,小辛子正是依靠着同乡来到了Y市,从事了搓澡的行业。从最初一无所有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小辛子对孔老大心存感激。小辛子说:“要不是孔老大我们根本就不能来这搓澡。来到Y市以后,觉得有个老乡在这儿,心里有底呀,他们确实也帮了不少忙。我老婆经常去他家,每次去都得拎点东西去。现在我们这帮人都有来往,逢年过节,大家就在一起聚一聚。”
有学者认为,来自同一地区的农民工之所以在同一个城市迅速聚集,是因为他们的流动与亲友们有紧密的关系,一个带一个,呈现出典型的所谓“链式流动”的形态[1],这个链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传播和加强心理上的安全感,搓澡工通过这个“链”提供的信息获得经济资源的机会。但是不可否认,这条“链”上的关系在原先的交往上并非那么紧密,搓澡工来到Y市以后,这样的“链条”才因为同属一个职业圈子,增进着彼此的交往。
2.关系的重构:和城里人的关系
搓澡工社会交往层面的适应离不开“搓澡工”的内聚力,即乡邻亲戚关系在迁入地的植入和认同。在城市中,以业缘为纽带的社会交往作为“外力”,也是搓澡工社会交往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老二离开Y市,马老大成了安徽搓澡工的核心。马老大善于交际,性情豪爽,所以,老乡有事都找他帮忙,他也乐意帮助别人。说起他在Y市的“朋友圈”,马老大说:“我这儿的朋友招待的太多了,真是太忙了,基本上都是老乡。我在这儿混得熟,Y市的浴池基本上我们都熟悉,啥人都接触过。有些人有啥难事,我都帮着处理。Y市当地的朋友也有,到哪哪就是朋友,像总找我搓澡的人就是我朋友,哈哈。”
搓澡的工作性质预示着和搓澡工日常接触最多的城市人就是顾客。由于顾客对搓澡工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认可,他们之间的互动交往从浴池延伸到日常生活。随着他们日常交往的密切和频繁,他们之间不再仅仅是一种消费和服务关系,还成了生活中关系密切的朋友关系。换言之,顾客成为了搓澡工在城市社会交往圈子中的一分子。当然Y市人对他们也是接纳的、友好的,这一状况与当地的民风不无关系。Y市人性情豪放粗犷、仗义直性、比较重视人情和关系。毫无疑问,搓澡工和城里人在不断的交往中,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和互惠,城里人成了搓澡工在社会适应中可以依赖的群体。
(三)心理适应
心理适应实质上就是心理层面上的一种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简单地说就是,别人如何定义我们,我们如何定义自己。自我认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互动中形成和发展的。这种自我认同直接反映在他们对职业、地域、身份是否认同。
1.职业认同:“我”和“他人”眼中的自己
职业认同是搓澡工对自己搓澡职业的认同感。拥有14年从业经验的永强,对于搓澡这个职业已经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谈起搓澡这个职业,永强说:“现在没啥可干的。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也不好干。小了吧不挣钱,大了吧没本钱。你如果做买卖,像在市场租个亭子1万块钱,3天不开张,赔死你,那是你自己的钱没了。搓澡不,最起码我不需要投入,赔就赔了力气。”
众所周知,城市人,尤其是东北人好“面子”,像这些诸如给人家搓澡等“跌份子”、不体面的工作,他们不会去做。因此,精打细算而又能吃苦饮卑的安徽人不远万里,来到Y市干起当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却挣了很多钱。“面子”在搓澡工眼中,虽然满足了人们的虚荣心,但是满足不了他们对物质的渴望。“行行为衣食、职业无贵贱”,当城市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安徽搓澡工们已经在这个行业挣得盆满钵满了。
2.地域认同:半个Y市人
地域认同即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孔老三在Y市已经生活十几年,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谈起归属感,孔老三深有体会地说:“你像我每次从外面出门回来,就感觉亲切,觉得到Y市,就到家了一样。现在,感觉家就在Y市,因为家里人都在Y市。在这儿什么人都能找到,在这儿有个大事、小事啥的,都能找熟人办。”
随着乡村网络关系的外迁,城市汇集了孔老三原先家乡里的各种关系,城市成了现实中的“家”;家乡已经没有家的感觉了,成了意识中的“家”。目前,像安徽搓澡工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熟人”包括从乡村社会中移植过来的亲戚、老乡,还包括在异质性的网络关系中新结识的朋友。这些“熟人”的存在,使原本对城市的“陌生感”、“排斥感”逐渐消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城市的归属感。
3.身份认同: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
农民工身份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表现在作为职业身份的工人和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身份认同就是对这种身份双重性的认同。农民的非农化需要经历职业身份的转变——从农民到工人,而且还需要经历社会身份的转变——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只有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同时发生转变,才会成为真正意义的市民。已经把Y市当成第二故乡的小辛子并没有表现出对城市户口的渴望,恰恰相反,现在的户口在哪里他并不在乎。小辛子说:“不打算把户口迁过来,现在这个户口也不重要了。你看现在出去办什么事,也不需要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照样可以在城市买房。户口转过来,其实什么都没有,不迁户口那边还有地。”
不同于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像Y市这样一个人口并不密集的三线城市,户口并不是稀缺资源,外地人想上城市户口其实并不难。然而安徽搓澡工大多安于现状,并不想把户口迁到城市。不可否认,户籍制衍生的一系列政策,如教育政策、保障政策等形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当他们的市民身份得不到制度的认可时,他们或多或少能感受到在户籍制度下的排斥力量,但是这些排斥力量并没有剥夺他们在城市就业、买房以及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对于这些已经稳居在城市生活的安徽搓澡工而言,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并不重要。况且农民工外出打工无论多久,土地仍然可以保留,对于他们而言,土地如同一份“社保”,为农民工化解了诸多潜在的风险,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结论:多维性社会适应
综上,笔者从三个方面描述了安徽搓澡工是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析,笔者打算用多维性适应来阐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特征。这种多维性适应主要体现在:经济适应是基础,社会交往适应是条件,心理适应是结果。
(一)经济适应: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
经济适应是社会适应的基本层次,也是实现社会适应的第一步。经济适应就是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即经济层面上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只有经济适应得以实现,他们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生活中,逐步实现社会交往适应和心理适应。安徽搓澡工的经济适应能力随着他们职业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增强。
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安徽搓澡工借助老乡、亲戚关系来到城市,从事搓澡服务行业,唯一的目的就是挣钱。可以说,在城市打工之初,他们更多地表现为生存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理性选择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生存已经不再是他们搓澡的动因和目的。他们发觉,搓澡不仅能够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还能满足他们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于是在生存理性选择之后,经济理性已经成为搓澡工的最新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就是以摄取最大限度的经济资源为目的,而搓澡行业正好满足了他们对经济理性选择的追求。事实上,搓澡这个“汗领”职业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超出预期的收入。
同等收入的农民工在不同迁入地区所处的相对经济位置是不同的,随之而来的经济适应程度就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当农民工的职业收入与当地居民的收入接近时,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生活。毫无疑问,拥有相同收入的农民工在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相对经济地位,身居小城市比身居大城市具有更高的经济地位的优越感。与Y市的社会平均工资相比,安徽搓澡工的收入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同样的收入置于经济发达地区则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如果再算上地区间的生活成本差,同样的收入在不同地区生活的实际水平会进一步被拉大。因此,安徽搓澡工较高的经济相对地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状态、社会适应、自我认同等各方面会有所不同。可以说,安徽搓澡工稳定的职业收入以及自身所处的较高的相对经济位置是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
(二)社会交往适应:构建新的“社会空间”
如果说经济适应是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那么社会交往适应就是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它表现为搓澡工社会网络关系的移植和重构。基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选择的经济适应是农民工立足城市的基础,在完成初步的经济适应之后,社会网络关系的移植和重构是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他反映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社会交往适应不仅保证了获取经济资源的可能性,也增强了获取经济资源的持续性。社会交往适应是实现经济适应和心理适应的外在条件。
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初期,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不熟悉的社会。在这个充满陌生人的社会中,他们首先能够依托和寻找到的就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社会关系。当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在异地聚集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会得到重新认可和建立。他们互动和交往因为传统关系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紧密,同乡人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拉紧了他们的关系链条。在这样的网络关系中,他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的支持,还获得了精神的支持。一般而论,这种传统关系的移植和存续,成为了他们在城里求生存、谋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但是,农民工不可能只是在“熟人圈”里“混饭吃”。以亲戚、同乡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网使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了在城市生存、适应和发展,他们必须要和“陌生人”打交道。随着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也具备了在城市中建立新的关系网络的条件。由于搓澡行业的职业特点,安徽搓澡工每天都要和城市人打交道,长此以往,随着关系的建立,其互动的频率、交往深度也会不断增加,他们可能会成为新的朋友关系。布劳的“机会性假设”指出,人们之间的交往程度和关系密切程度取决于他们发生接触的机会。这个假设非常明确,人们永远不能与自己无法接触的人交朋友[2]。这种新建立的朋友关系不单是一种工具性的弱关系,可能还会转变成情感性的强关系,从“弱关系”转变成“强关系”是在双方信任和互惠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结果。可以说,社会交往适应不仅会减少城市的陌生感,还会增加城市的认同感,帮助他们逐步地融合于城市社会。农民工在城市所建立的这种新的社会联系愈多,他们整合和融入于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社会的程度似乎就愈高。
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的过程。不可否认,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客观存在的,由此产生对外来者的束缚和限制也是不可避免的。站在农民工的立场,在制度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他们只能主动地适应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各种排斥。安徽搓澡工利用“强关系”的移植和“弱关系”的重构,在异地重建一个独立于体制、身份之外的新的“社会空间”。
(三)心理适应:一种自我认同
如果说经济适应和社会交往适应是农民工外在的适应,那么心理适应就是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内在表现。心理适应作为一种自我认同是实现经济适应和社会交往适应的必然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心理适应是农民工社会适应的最高层次,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只有完成心理适应,才算完成真正意义的社会适应过程。
第一,职业认同是心理适应的核心层次。职业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搓澡工心理适应的程度。职业认同感一方面取决于职业收入的满意度;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人如何看待这个职业。对于安徽搓澡工而言,最让他们满意的就是收入,这种较高的职业收入满意度带来了较强的职业认同感。
第二,地域认同是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或接近的价值观。当然,地域认同还包括对当地人的认同。随着传统乡村网络关系的植入,以及和基于乡土网络关系基础上的城市网络关系再生产,安徽搓澡工在城市中的“熟人”越来越多。事实上,他们在回乡、不回乡的犹豫中,年复一年地在Y市生活着。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中成长的搓澡工子女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城里人,他们从小就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接受城市教育。与难离故土的父辈相比,他们更愿意生活在城市,更愿意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可以说,子女的城市梦想在无形中坚定了父辈们在城市生活的信念。
第三,农民工的身份具有双重性特征。这种双重性表现为他们在职业身份上是城市搓澡工人,而在社会身份上仍然是农民。农民工身份的双重性从根本上说,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的产物。由于身份的双重性,搓澡工并没有摘掉农民身份的帽子,他们无法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根本转变。随着国家各种惠及农村及农民工政策的出台,这种双重性身份成了搓澡工们“刻意”要保持的一种状态。在他们看来,双重性身份给农民工带来的不是利益的缺失,而是双重的利益,追求一个制度认可的市民身份并不“实惠”。在这个意义上,流动农民与“城里人”形成的可能是一种“隔离性融合”[3]。笔者认为这种“隔离性融合”意味着农民的市民身份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认可,他们还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那个过渡阶层。
总之,经济适应、社会交往适应以及心理适应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实质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这三个层面的适应是并存的,但却并不是同步实现的。根据农民工外出流动的不同阶段,实现的顺序有先有后。在短时间内,以赚钱为目的的进城农民工很容易完成经济适应。虽然心理层面的适应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是经济适应和社会交往适应已经为进城农民工的心理适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的中央一号文件,表明了中央政府推动城市化、农民工市民化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公民权益保障的决心。而后温家宝总理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考虑为大城市减负,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安徽搓澡工生活的城市——Y市,正是中小城市的典型代表,而搓澡工也正是温总理所说的具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没有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已经具备了在Y市落户的经济条件,至于他们何时落户,从文中可以看出,这不仅取决于政策的落实情况,还要取决于农民工的个人意愿。不论怎样,虽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制度障碍,但是这种制度性障碍的作用和意义在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趋势下正在减弱。
[1]项 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页。
[2]赵 莉:《国内外社会网相关理论及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王毅杰:《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