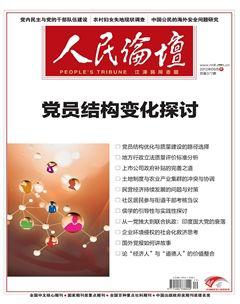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兼得模式优化
杨慧
【摘要】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兼得模式的核心在于法律设置侵权责任法及社会保障法两种并行的法律,工伤职工可依此向不同的义务主体主张权利。兼得模式运行的结果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但无疑增进了对工伤职工的权益保护,同时并未增加责任主体的责任。区分侵权主体,对用人单位侵权和第三人侵权分别对待是正确适用兼得模式的关键。
【关键词】工伤保险 侵权责任 兼得模式
兼得模式的理论基础
所谓兼得,即工伤事故如果存在侵权方,劳动者既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同时可按照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由工伤保险基金或者用人单位要求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兼得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单一的工伤保险救济存在局限性,工伤保险仅对人身伤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补偿,而工伤事故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不在工伤补偿范畴之列,这与侵权赔偿的全面赔偿原则相比,对受害人的保护是不利的。
兼得模式无疑加强了对工伤劳动者的保护,按照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精神,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和工伤保险基金的法定义务,必须依法予以履行,该义务不能因劳动者已经获得侵权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而予以扣减或者免除;同样,侵权第三人的民事赔偿义务也不应因劳动者已获工伤保险待遇而获得扣减或者免除。工伤事故中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具有不可逆性,即使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补偿兼得也不会造成所谓的“多重受益”、“双重得利”,两个请求权的产生都具备合法来源因而不会构成不当得利。
有学者从衡平的角度提出质疑,认为侵权法给予所有公民相同的保护与救济,如果仅仅由于被侵权人同时具有在职职工的身份就能获得双重赔偿,会对“其余被侵权人”造成相对意义上的公平损害。该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个体角度衡量,不采用兼得模式也不会为兼得模式下受到公平损害的“其余被侵权人”带来额外利益,只是增进了具有职工身份的劳动者的社会福利。
兼得模式的现行法依据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对工伤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给予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是雇主替代责任,第三款同时排除了雇主替代责任在工伤保险调整领域的适用,即工伤保险范围内发生的工伤事故不适用第十一条而应直接适用第十二条。第十二条对工伤损害中用人单位侵权及第三人侵权的法律适用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责任,侵权第三人则按照民事侵权法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工伤职工而言,可以在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向侵权第三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即两种赔偿可以兼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2号)明确规定,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从侵权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可以向工伤保险机构或用人单位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上述公报及答复十分明确地表明了最高院的态度,对于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工伤,无论工伤职工先获得何种赔偿、范围如何、是否充分,都有权向另外一方主张权利并获得赔偿,即工伤保险待遇及侵权损害赔偿可以无条件兼得。
《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中曾就是否规定工伤保险问题有过争议,有部门认为工伤问题属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范畴,不宜在侵权法里面给予规定,而应当由当时同时起草的《社会保险法》规定,最终侵权责任法对这一问题没有规定。就工伤事故的性质而言,早期学说多主张为一般侵权行为,后有学者认为工伤事故属工业事故,依照现代民法应归为特殊侵权行为,还有学者认为其兼具工伤保险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双重属性,其实上述定性都未回避工伤事故的侵权属性,侵权责任法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对这一问题进行回避。
《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对兼得模式下医疗费用的双重给付做出了排除性规定,明确了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种追偿权的制度安排表明医疗费用最终应当由侵权第三方承担,工伤保险基金的先行支付则集中体现了社会保险的救济功能,就医疗费用而言,工伤职工及其家属不能兼得。对于医疗费用以外的其他工伤保险待遇是否能够兼得,包括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在内的社会保障法都没有明确,同时也没有赋予工伤保险基金代位权,因而上述侵权法律制度所确立的兼得模式没有在社会保险法中给予根本否定,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兼得模式仍然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应当予以适用。
兼得模式下的用人单位侵权问题
当工伤事故的发生与用人单位外的第三人侵权无关时,劳动者只需考量与用人单位的诉求,由于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确立的工伤事故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因此无论用人单位有无过错,用人单位及工伤保险基金都要依法按照各自承担责任的范围为工伤职工提供工伤待遇,给予劳动者最基本的保障。鉴于侵权责任法并未将工伤事故作为特殊侵权对待,因而当用人单位无过错时当然不存在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用人單位只需按照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提供工伤待遇;问题在于当用人单位在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劳动者可否同时追究其过错的侵权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工伤保险的属性。
与其他社会保险不同,工伤保险的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全额缴纳,用人单位通过购买工伤保险,将其职工发生工伤事故时的赔偿义务和责任转移至工伤保险基金,这与商业责任保险中投保人通过投保转移民事赔偿责任如出一辙。商业责任保险标的的民事赔偿责任可以是过错责任,也可以是无过错责任;可以是契约责任,也可以是侵权责任,在工伤保险这种责任险中,用人单位通过投保转移责任和风险,工伤保险基金通过承保体现社会福祉,保险标的是用人单位对其职工在发生工伤事故时依法应承担的责任,该责任既包括无过错的工伤待遇支付责任,同时也应包含由用人单位过错引发的侵权责任。
与第三人侵权不同,在用人单位侵權的情形下,比较法上多否定工伤保险机构的代位求偿权,是在于工伤保险的责任险属性,如果工伤保险机构在对工伤职工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可以向有过错的用人单位追偿,这样会降低工伤保险制度的吸引力。
兼得模式下的第三人侵权问题
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发生工伤的,劳动者可以兼得侵权赔偿及工伤保险待遇补偿,问题在于审判实践中法院常以“赔偿项目性质相同”、“系同一补偿费用”等为由予以扣减,如“丧葬费”与“丧葬补助金”、“死亡赔偿金”与“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残疾赔偿金”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交通费、医疗费、住院伙食费等。也有学者提出,可依类型化的思路,按照不同赔偿项目分别判断的原则解决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并行给付这一难题。①这样的处理显然比单纯的兼得模式更具公正性,但从效果上看与“就高不就低”的补充模式更为接近,同时与补充模式相比又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难度。
笔者认为,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仍应以兼得模式为基础。因为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由此可见,兼得模式的核心在于法律设置了侵权责任法及社会保障法两种并行的法律制度,工伤职工是依照各自的法律关系向不同的义务主体主张权利,兼得模式运行的结果无疑增进了对工伤职工的权益保护,同时并未增加责任主体的责任,即不要看权利人获得了多少利益,关键是要保证义务人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比较法中也常见赋予工伤保险基金代位权,工伤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质是工伤职工在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将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请求权转让给工伤保险机构,兼得模式下显然不能做如此安排,工伤保险机构代位权的缺失从表面上看增加了其运营的成本,实际上是让利于工伤职工,符合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确定了过失相抵原则,基于追究有过错的行为人责任的考虑,让工伤职工承担自己过错行为引起的后果,也是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203049)
注释
①周江洪:“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并行给付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