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士商”与古之士商
文Ⅰ周之江
今之“士商”与古之士商
文Ⅰ周之江
“九二派”被作者称为这一时代的“新士商”,“和传统士大夫相同之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不同的是实现目的的路径和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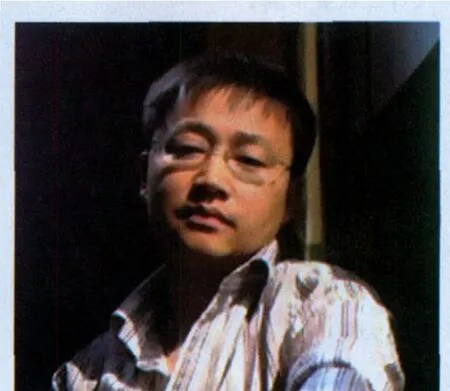
陈海,贵州人。现任《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特约研究员,偏好商业写作。曾任职《中国新闻周刊》副主编、《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南方周末》记者、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特聘讲师。从事媒体工作期间,长期致力于时政新闻及调查类报道的实践与探索,有编著作品《真相的力量》等。
最近读到一本好书,即《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与理想》。作者是陈海,1992年进大学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这个年头,碰巧是《九二派》里那些当代“士商”们自觉跳离体制,投奔市场的风云际会之时。
窃以为,此书绝非一般的财富故事,其要点在于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也即是所谓的“士商”精神,这是中国自古缺乏的东西。时至今日,从耻于言利到纷纷下海,其转变不可谓不剧烈,我想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官本位”到“商本位”而已。这些年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因何而来的著述不少,比如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虽众说纷纭,不可否认的是,要适应当代中国的转型,大概不能全然地从传统或者西方去求出路,士与商的结合,也许是路径之一。不但与财富有关,更与社会的治理结构有关,而且,这条路径并非上层设计得来,说得夸张些,也是发源于基层。早年间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来看到杜维明等辈试图从儒教伦理中寻觅亚洲复兴的秘密,总觉得牛头不对马嘴。
谈到“商道”,中国是大陆型国家,历来重农抑商,工商社会不能发展,早成学界共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著《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即说,传统中国的“管制阻碍着一种创立商业统治集团之企图。只有最下层的商业,(包括)市镇间的店铺和集场(能够)有功效地作业。”
书中写到,“九二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武克刚,曾发表题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的演讲,追溯中国“商道”,特地点出三个大人物的名字:管仲、范蠡、吕不韦。在他看来,“遗憾的是,他们对后代的影响,不是表现在制度建设上,而是表现在理论思想上,他们都明白自由与法治对百姓富裕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生搬硬套之嫌,背后的意思却堪寻味。时至今日,当代工商业巨子,早成社会中坚力量,而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群体“九二派”,用开篇处陈东升的话来定义,乃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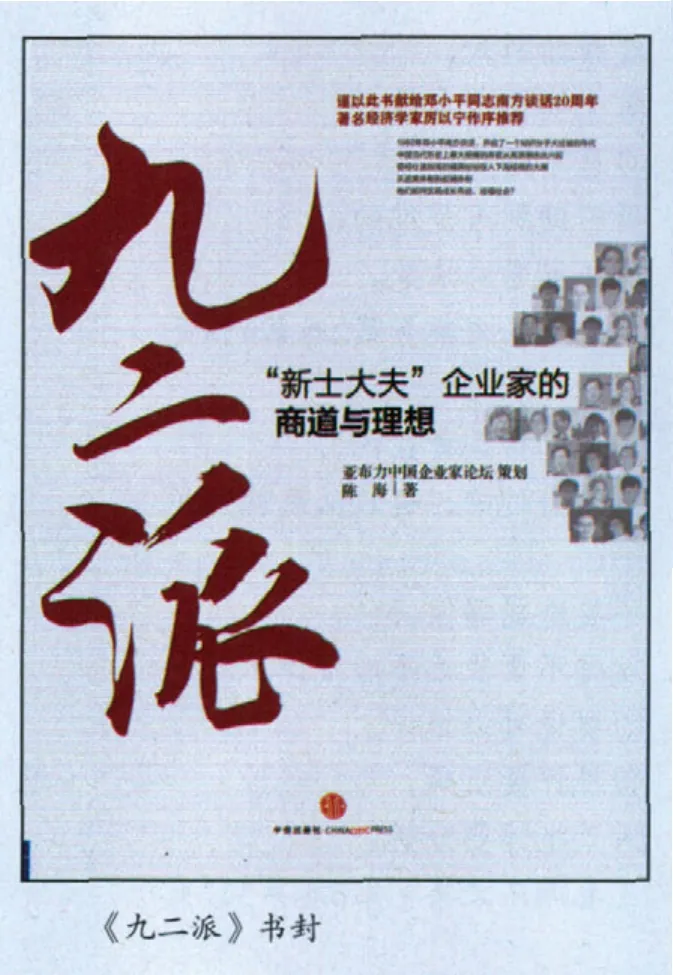
“九二派”被作者称为这一时代的“新士商”,“和传统士大夫相同之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不同的是实现目的的路径和手法。”
晚清时,龚自珍著《京师乐籍说》,就明白写到,“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很显然地,这种“聪明喜论议”的脾性,确乎是新旧“士大夫”们的共同点之一,昭示了某种浓烈的政治情结,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从政还是经商,都挥之不去。虽然,“士”与“商”结合派生出来的今之“士商”,已然不同于古之“士大夫”,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说,士大夫集二重角色于一身,“帝国政府庞大复杂的行政事务凸显出了‘官僚’的形象,浩如烟海的诗文著述凸显出了‘文人’的形象”。
不管是官僚还是文人,都与“九二派”的气质不尽契合,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是体制内的“官员”,甚至还多多少少有一点“诗人”的理想色彩。按照陈海的归纳,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这批多供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其感召,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武克刚、王梓木、黄怒波、胡葆森等为代表的“九二派”。毫无疑问地,这样的背景,使得他们在初涉商海时,便迥异于一般的生意人。在追求财富之外,“九二派”有着更强的使命意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批自觉或不自觉以思想家自居的企业家。
前面说过,所谓“士商”,其实缺乏历史的承续,古来“士农工商”四民,士居其首,而商叨陪末座,两者素少瓜葛,《孟子》亦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显然把“士”当做精英阶层来看待,惟士可称“君子”,余者皆“小人”。
明清以降,工商业的发育超过历代,大商巨贾富可敌国,其豪奢靡费、一掷千金之态,在旧籍中多所记载,但仍为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所不屑。乾隆年间所修的《山阳县志》就说,“淮俗从来简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荐绅即士人,明白地与商人对立而言,作为负面教材,正是中国古来习见的立场,也是“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观念的缘来,至今影响不绝。
可举的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暂且打住。之所以说士与商的传统缺乏交集,是源于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实在大相径庭,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里有过精辟的总结:“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造社会。”而有趣的是,其实“士”的地位在传统社会里也有尴尬之处,代表性的说法如顾亭林《与友人论学书》所言:“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说白了,空谈无益,光会耍嘴皮子可不行。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外族侵凌,西学东渐,老大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之大变局,为秦汉以来未有之世变”,变的结果之一,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也随之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其风光。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费孝通先生著有《中国绅士》一书,即说,“在传统的中国权力结构中,有着两个不同的层次,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其领袖是绅士阶级”。这也是学界早有共识的看法,换言之,在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大夫群体是社会不同阶层的捏合剂,甚至可以说是实现社会自我管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时运迁变,费孝通观察到,“一方面是土地租息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是具有新型政治意识的通商口岸群体的兴起,这两者都减弱了绅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须赘言的是,“士”不再有其成长的土壤,日渐远离权力中心,勉强地说,作为精神层面的“士”,倒还一直余韵悠长,不时就要跳出来指手画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讨论不绝于耳,而这也是我们理解“九二派”故事时,必须要参照的一个背景。
“新士大夫”之所以“新”,大概还源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不同于传统士人,所谓“体制内”经历,赋予了这一群体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傅小永先生在此书的前言里,以代际划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企业家,第一代是乡镇能人型企业家,第二代即“九二派”也便是“士大夫”企业家,第三代是“海归”企业家。
不好简单地将不同代际的企业家做高下之分,更值得重视的话题也许在于,近百年来的中国,确乎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把眼光放到一个较短的时段,也即“九二派”企业家孕育成长的改革开发年代,30余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固不待赘言,但也时时要承受转型的阵痛,原因或者在于,社会犹如一个大而复杂的有机体,其转变不能处处尽如设计,种种不适应因此发生,一个有责任感而且真能承担责任的所谓“士商”阶层,的确能对社会治理起到切实的作用。
现成而且就在身边的例子,是去年贵阳市成立的“和谐贵阳促进会”,媒体报道说,“促进会”由非公经济人士、宗教界人士、民主党派人士组成,他们通过捐资募款,帮扶困难群体,协同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破解信访难题,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效补充力量,是第三方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探索。更进一步的解读,称之为新时期的“太平绅士”,乍闻之下,有些诧异,细想则不无道理。
还是借用费孝通的一段文字,来为本文作结:“社会结构的本质还是和以前一样起作用。我相信它在变化,但新秩序是不会一下子突然产生,完成于一刹那间的。新秩序是从旧秩序中产生的。”
“九二派”也好,“新士大夫”企业家也好,都是这种变化的产物,费先生说得很清楚了,它不会“一下子突然产生”,也不会“完成于一刹那间”。(作者系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蒋叶俊)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