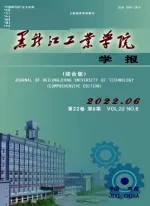论《诗品序》中的“真”美
孙刚 刁凌霞
论《诗品序》中的“真”美
孙刚 刁凌霞
《诗品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篇影响深远的文论,历代学者不乏对其研究。但是多数研究者是把这篇文论分成几个部分单说,很少讨论其贯穿始终的品质。“真”美便是这些品质之一,真实地感受,真实地表达,真实地表现,从而“真”意盎然。
《诗品序》;感受;表现;表达;“真”美
作为一篇影响深远的文论,历代学者不乏对《诗品序》的研究。然而,大多数的研究者把《诗品序》分成“物感说”“滋味说”“自然说”等几个部分单说。对于贯穿始终的品质提及不多。本文所要论述的“真”美,便是其中之一。可以认为,“物感说”“滋味说”“自然说”最终指向便是“真”美。即作者真实地感受自然和社会,再把内心的情感真实地表达出来,并且通过一定的表现技艺和手法,使这种表达“真”意盎然。
一 “真”美的来源——“物感”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丰富多彩的客观事物使人意志萌动情思绵绵,进而“摇荡性情”,使情感外化成诗歌。《荀子·正名》云:“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2]刘勰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3]可以说,钟嵘的“性情”,荀子的“性”,刘勰的“情”,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即主体的心灵。再深一步去思考,这里的“性情”与今人情感是不尽相同的。前者倾向于先天的本质和气质,是纯“真”、纯“自然”的艺术气格。当这种气格被外物所“感”时,人会有所心动,心动的展露和表现,便形成诗歌在内的艺术。同时除“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外,“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骨横朔野,魂逐飞蓬”“负戈外戍,杀气雄边”等都可以“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能够看出“摇荡性情”者,除自然事物外,还包括社会生活。它们都是抒写“真”美的源泉。故袁枚有:“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另外,“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1]钟嵘只抽取《论语》“兴、观、群、怨”中的“群”和“怨”,并且,与《毛诗序》相较,没有提及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4]一类的伦理功能。这就表明,钟嵘不认为诗歌是为政治教化服务的,而是“可以陶性灵,发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1]的审美性活动,是一种对“真”美的欣赏性活动。由此,那些“摇荡性情”的“物”正是“真”美之来源。
二 “真”美的内容与本质——“自然”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1]不难看出,对于诗歌和一般非审美性的实用文章,钟嵘认为在情感的表达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诗歌的特性在于“吟咏情性”,目的在于抒写心灵所感,以表达万象“真”美。所以,在内容上,抒情必须自由;在表现上,须有清丽、流畅、淡雅的自然美。而对经世治国的奏表、文书、驳议之类,“应资博古”“宜穷往烈”则是非常必要的。对重在表现情感体验的诗歌来说,吊书袋显学问,究源穷典,不仅妨碍诗歌“自然”情感的表达,更抹杀了自然本色艺术的表现,故钟嵘反对那些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1]这是《诗品》正文中对谢灵运和颜延之诗歌作品的品评,对于当时诗坛的领军人物颜延之,钟嵘不但评其诗“错彩镂金”,而且将之列于中品。可见钟嵘对当时诗人追求文辞藻饰,忽视“自然英旨”之“真”美,是非常鄙薄和抵触的。再看对谢灵运的品评,如众所知,谢为山水大家,其诗清新自然,所以钟嵘品曰:“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1]同时又批评其过于繁富、不够自然:“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1]也就是说,钟嵘认为谢灵运的诗歌也没有完全达到“自然”之“真”美的境界。因此说,“自然”乃“真”美的本质和内涵。
三 “真”美的表现手法与技艺
“真”美的表现手法与技艺,即如何把诗歌写得尽量“自然”。钟嵘《诗品序》中说的比较细散,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适当用典。这点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在此稍详叙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1]如果大量堆砌典故,会使诗歌诘屈聱牙,文意晦涩,难以呈现自然美。对此,钟嵘有言:“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这里,钟嵘提出“直寻”说,以“直寻”来对抗大量用典的风潮。诗歌以“吟咏情性”“独抒性灵”为准则,“直寻”说强调了直接可感的形象和由这些形象所引发的直觉的重要作用,二者感染诗人的心灵,并使之外化,便让诗歌具有“自然英旨”。另外,有一点还要注意,钟嵘虽主张自然,反对用典,却非全部否定,盲目反对。而是主张将适应的典故化入诗中,服从“吟咏情性”和“自然”的需要,并在此基础上,把“巧似”和“自然”统一起来,经过努力而达到出神入化、浑然一体的艺术高度。
2.适当讲究声律。南齐永明年间,“永明体”渐成,作诗讲究声律。“王元长创其首,沈约、谢眺扬其波。”[1]在这种时风的影响下:“士流景慕,务为精密。”[1]沈约著有《四声谱》,辨析汉语平、上、去、入,并提出“八病说”,虽然为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破坏了诗歌的自然流畅美。钟嵘从提倡自然美的角度出发,尖锐批判当时的永明声律。他认为过于讲究细密的声律会使诗歌“襞积细微,专相凌架。”[1]最终,“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1]反对永明声律,并不是说反对所有声律,相反,钟嵘认为凡诗必有声律。“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1]并且钟嵘还列举曹、刘、陆、谢四位诗人说他们尽管“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1]但其诗作并没有因此而失声律之美,这于钟嵘看来,便是自然之“真”美。“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1]钟嵘并非反对诗歌音韵美,只是不要像永明体那样琐碎细繁,“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1]
3.抑玄言诗、四言诗,扬五言诗。达到“真”美意境,是否玄言,是否四言,是否五言,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在钟嵘眼中,也许五言诗更胜一筹。“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为钟嵘对玄言诗的评价和批判。玄言诗以玄理为内容,少有具体可感的审美形象,缺乏真情实感。“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1]这是对四言诗和五言诗的评析。相对于四言的“文繁而意少”,五言拥有“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优势。所以钟嵘认为五言能够更加完美的体现什么是“自然”美,什么是“真”美。
4.“三义”融合。“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1]此“三义”由《毛诗序》演来,但与原意有较大区别。《毛诗序》中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钟嵘只抽取后“三义”,并且改变三者位置,把“兴”放在第一位,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1]突出强调诗歌的言外之意,以有限的文字蕴含无限的情感。说明钟嵘摆脱伦理教化的束缚而转向审美和“真”情的表达。对“比”和“赋”的阐释也有重要发挥:“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1]也都强调诗歌的抒情言志、述说性灵的审美特征。继而将比、兴、赋有机结合,“宏斯三义,酌而用之”,[1]方能于有限的空间寄寓无限的“真”情。即如刘熙载言:“《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5]若偏用一方,则如钟嵘言:“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1]
5.“风力”与“丹彩”相统一。“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1]这里的“风力”强调内容,“丹彩”强调形式。从正文钟嵘对各家诗的品评看,“风力”主要是指情感、力度和气势等,能够撑起一首诗的特质,是骨架;“丹彩”主要是节律、音韵、用语等,是能够润饰一首诗的特质,是血肉。如钟嵘对曹植诗的评语:“骨气奇高,词彩华茂。”[1]就很符合这一点。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能写出上乘之作,“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1]
四 “真”美的终极价值和体现——“滋味说”
我国古代文论中有关“味”的论述比较常见:“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6]“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7]但以“滋味”论诗始自钟嵘。是钟嵘把“滋味”作为专门的文学批评标准,使之成为古代文论中一个基本的审美范畴。“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所之有滋味者也。”[1]能够看出,钟嵘不但把“滋味”作为一个品诗标准,而且把它放在首位,并且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作,才是“诗之至也”。也就是说,钟嵘把能够让读者反复品读不厌,并且从中获得情感认同或共鸣的诗歌,视为诗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境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滋味”是“真”美的终极价值和体现。有没有“滋味”,有没有“真”美,是前文列举的所有文论点的统摄,它们一切的方向和价值就是“滋味”和“真”美。
综上,“真”是贯穿《诗品序》的一个重要审美理想,它体现着作者的评判标准和审美创作倾向,作者围绕它进行了各方各面的论述与诠释。这无论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还是对诗歌创作的爱好者来说,都是宝贵的议题和财富。
[1](南朝梁)钟嵘,著.曹旭,整理集评.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10-13,21,25,30,43.
[2](战国)荀况,著.蒋南华,等,注译.荀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393.
[3](南朝梁)刘勰,著.黄霖,整理集评.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
[4](宋)朱熹,集传.朱杰人,导读.诗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
[5](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97.
[6]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528.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1312.
On Beauty Expressed in the Poetry Preface
Sun Gang Diao Lingxia
As a profou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Poetry Preface"has already been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Most researchers divided this article into several parts,such as“material”,“taste”and“nature”.However,few people discussed the qualities throughout"Poetry Preface".True feelings,true expression,true performance are taken as some qualities of poems in which the true beauty included.
Poetry Preface;feeling;expressiveness;expression;true beauty
I206.2
A
1672-6758(2012)04-0087-2
孙刚,硕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研究方向:唐宋文学。邮政编码:637009
刁凌霞,硕士,山东大学,山东·济南。研究方向:中文信息处理。邮政编码:250100
Class No.:I206.2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