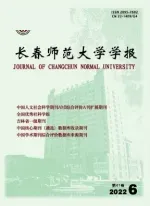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监护研究
王 晖,池中莲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监护研究
王 晖,池中莲
(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本文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监护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梳理,提出父母离婚后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上法律应确立这样的标准,即规定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个人的、直接的和经常的联系应予维持。
离婚;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
离婚解除了当事人之间的夫妻身份关系,但不消除父母子女关系。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监护的权利义务,这是保证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但是,离婚毕竟会导致家庭破裂、共同生活解体,这便产生了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以及监护的制度问题。对此,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散见于《婚姻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收养法》 《民法通则》 《民通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等法律文件中。只是这些规定不仅不够完善,而且彼此不乏矛盾冲突。以往研究大多采用亲权或监护进行理论分析和制度构建,论述中往往将婚姻家庭法上关于抚养的规定解释为亲权,或推定为监护,唯独忽略抚养本身。这大概因为我国婚姻法中既没有明确规定亲权,也没有明确规定监护,而一律采用“抚养”“教育”“保护”的立法语言,学者研究监护或亲权问题时只能依赖这些抚养上的规定。不过立法之所以如此,正说明抚养关系具有独立性,以目前法律规定而言,抚养构成亲子关系最基本的内容。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紧密相关,正是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法律才确认未成年人的父母从未成年子女出生之日起便取得了法定监护人的资格,成为其当然的法定监护人[1]。所以,一般而言,父母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是其监护的基础,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一、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
(一)父母对子女抚养的一般含义
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抚养,是指父母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供养和在生活上对子女的照料。包括负担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抚养义务是父母对子女所负的最主要的义务,目的是保障子女的生存和健康成长。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无条件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情况下父母都必须履行抚养义务。[1]
从抚养的程度来说,学理通说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强制性的生活保持义务。所谓生活保持义务,又称共生义务,通常指发生于夫妻之间、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为维系家庭共同生活而由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条件抚养义务。其法律属性和要求有以下四点:(1)抚养的长期性。从子女出生时开始,到子女达到成年年龄乃至具有独立生活能力为止,父母均应责无旁贷地承担抚养义务。(2)抚养内容的复合性。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涉及子女身心成长、发展的全过程。(3)抚养责任的无条件性。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作为生活保持义务,是无条件的,子女一旦出生,无论父母经济条件、劳动能力如何,也不论是否愿意,均必须依法承担抚养义务。(4)义务履行的自觉性。基于亲子关系的特殊情感联系和家庭共同生活状态,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除在特殊情况下动用社会公力强制外,绝大多数情形是以父母自觉自愿地圆满履行其义务为结果。[1]
(二)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的特殊问题
以上所述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的一般原理,亦基本以父母子女共同生活为基础展开论述。对离婚亲子关系而言,我们当然希望上述未成年人抚养的完整状态得以保持,但父母子女共同生活关系的改变,势必对抚养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婚姻法》36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均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子女往往只能由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从共同生活、共同抚养到生活分离、一方直接抚养、一方间接抚养,如何能最大程度地维持前述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程度?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基于我国一般社会生活实际,对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首先确定离婚后由父母何方担任直接抚养方,何方作为间接抚养方。直接抚养方行使与子女共同生活、直接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而间接抚养方行使探望权,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有学者指出,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将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作为离婚的效力之一,放在婚姻法离婚一章规定,实际上确定的是子女在夫妻之间的归属问题,即谁有权与子女共同生活,担任子女的直接抚养人。将离婚亲子关系放在离婚法而非亲子法中,将子女视为父母离婚时被确定归属的客体,且将离婚后探望子女只作为父母一方权利,这些正是中国传统“父母本位”子女观的体现[2]。在“父母本位”的影响下,离婚夫妻将子女抚养或当成权利争抢,或当成负担推诿,很难理性、平和地从子女的成长、发展出发并考虑子女的感受和愿望来处理子女抚养问题。
(三)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及其关照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公约促进缔约国各国在婚姻家庭法立法或司法实践中相继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儿童权利公约》还确立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将儿童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得到保护,而不是将儿童视为权利客体从而认为对儿童的保护是一种可怜和施舍。由此,《儿童权利公约》要求下的一国亲子立法必然是“子女本位”而非传统的“父母本位”。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离婚亲子关系的立法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怎样以子女为本位,维护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责任的连续性,并探索在生活分离的情况下间接抚养一方除了负担子女生活费,行使探望权之外,还能够参与决定有关子女利益事项,与子女保持实质性的联系,即“法律应该确立某些标准,规定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以外,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个人的、直接的和经常的联系应予维持”[3]。笔者认为,法律既然由“父母本位”转向“子女本位”,就应该要求离婚父母摆脱成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不要站在自己立场而要从子女立场出发维持子女对父母双方经济上、生活上以及精神上、心理上需要的满足。尽管现有法律规定探望权不无这方面的考虑,但显然仅靠现有规定无法达到我们的目的。
二、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一)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监护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4]。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而言,监护关系是指在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发生的由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予以监督和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1]。
监护制度在中国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及前大理院判例始得确立;1930年公布的民国民法典《亲属编》专章规定了监护制度,将监护分为不在亲权之下的未成年人监护和禁治产人的监护,我国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5]。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1950年还是1980年婚姻法均未设立监护制度,而是在父母子女关系或家庭关系中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直到1986年的《民法通则》专门规定监护一节。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第16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第18条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权利与民事责任。
不同于大陆法将亲权与监护区隔的传统,民法通则采用广义监护的制度,即将亲权的内容包括在监护之中。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资格是法律直接赋予的,无须再经过其他任何程序。既然如此,无论是处于婚姻中的父母,还是离婚后的父母,都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父母担任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的资格,不应因父母离婚而丧失。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推定我国关于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以共同监护为原则,以单独监护为例外。
《婚姻法》在2001年的修订中未对我国亲子关系性质属于监护还是亲权作出明确表态,依然使用“抚养教育的权利义务”这样的术语,但这并不表明婚姻法排斥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职责在内容上可以被抚养教育义务所包含。相应地,《婚姻法》36条关于离婚亲子关系的规定便可解释为蕴含了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共同监护的意旨,从而与《民法通则》和《民通意见》的规定相衔接。但是36条的“直接抚养”同时指出并引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随父或母一方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虽然父母双方对他/她都有抚养义务,而且应由父母双方共同监护,但他/她却是由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的。对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母或父而言,她/他的监护往往因不能共同生活而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监护如何实现呢?有学者认为此时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事实上处于停止状态,只有抚养关系变更或因故重获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机会时才复活。[6]但既然“共同监护是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在离婚亲子关系中的体现”[12],而且在法律上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状态并不停止监护的全部职能,我们依然需要探索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共同监护的实现方式。
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直接抚养的归属、抚养费的支付、探望权三大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婚姻法将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分为直接抚养和间接抚养,体现的正是共同监护的理念,任何一方在离婚后均有监护子女的权利,只是监护的方式发生变化,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父母子女共同生活,夫妻共同监护子女,改为离婚后的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另一方通过行使探望权、支付抚养费与直接抚养方分担对子女的共同监护责任。[2]但是,共同监护的职责是否仅通过行使探望权和支付抚养费就能得以实现呢?《民通意见》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司法解释在规定共同监护以后,同样在考虑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监护权的落空,而只让其对未成年子女的民事责任承担补充责任。
许多国家都倾向于即使父母离婚,也应当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由父母双方继续共同照顾子女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2]但我国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离婚后子女的直接抚养归属以及间接抚养方支付抚养费,行使探望权的规定,在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共同监护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理解为法律对夫妻离婚后便自动处于隔绝状态的默认,对父母离婚的子女还能继续享有父母双方的共同照顾的彻底不信任。完善监护制度,就是要改变这一现有状态,弥补现有抚养规定将离婚亲子关系分割为直接抚养归属、抚养费给付以及探望权三大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二)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制度的完善
从世界各国的亲属立法来看,离婚后父母对子女行使监护权的方式可以概括为单方监护与双方监护、部分监护与完全监护、身心监护与法律监护。除单方监护与完全监护外,双方监护、部分监护、身心监护与法律监护尽管在监护形式上有所区别,但都强调离婚后无论子女随何方生活,均不改变父母对子女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实质。[2]
在婚姻存续期间,父母共同生活、共同监护,对于监护职责的履行如对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重大利益的决定,不论其作出的真实过程,法律都推定系父母共同的意思表示。但父母离婚后分别生活的状态,使法律作出这种推定的基础丧失。重新使离婚父母对监护事项达成意思表示一致的最佳方式或说唯一方式就是协议。法律基于共同监护而要求在某些重大监护事项上父母必须进行协商达成一致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并非不可行。由于必须参与重大监护事项的决定,非共同生活的父或母一方因此保持了与子女连结的纽带,从而也为提高子女的主观福利水平提供了可能性。至于对法定监护职责中哪些属于日常事务,哪些属于重大利益事项,法律或法院应根据一般理性人的标准作出认定。
在监护模式上,能够实现共同监护的双方监护、部分监护、身心监护与法律监护都应作为可能的选择,至于具体案件中适用哪种模式,无论是协议离婚还是判决离婚,都可以由当事人协议选择。除了监护模式,当事人也必须在协议中就具体监护事项进行协商和确定,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并商定未议事项或突发状况的补救或解决办法。协议时应根据子女的年龄和成熟程度征求其意见或看法。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对监护协议的内容是否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负有审查职责。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法院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综合考量各项因素作出判决。
三、结语
关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监护,一直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难题。本文不欲也无法对该问题立刻提供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但本文坚持应该改变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将离婚后未成年人的抚养归属作为离婚效力的做法,改变亲子法中的“父母本位”而转向完全的“子女本位”。在现有将离婚后未成年人的抚养问题分为直接抚养的归属、抚养费的给付、探望权三大问题的制度条件下,必须完善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共同监护制度,以保证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责任的连续性。在共同监护的模式上,应为当事人提供多元选择,促使当事人在听取未成年人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充分协商订立监护协议来确定双方对未成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最后,法律以自己的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该协议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并保障该协议的执行。在当事人分歧过大而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法院应依职权,以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作出判决。
[1]杨大文,曹诗权.婚姻家庭法[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夏吟兰.离婚亲子关系立法趋势之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7).
[3]黄金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内实施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M].2版.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
[5]王竹青.论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6]蒋月,韩珺.论父母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兼论亲权与监护之争[J].东南学术,2001(2).
The Study of Fostering and Custody of Minor Children after the Divorce of Their Parents
WANG Hui,CHI Zhong-lian
(Economics and Law Institute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Urumqi 830046,China)
This article makes a careful analysis about the fostering and custody of minor childr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roblems,and believes that law should establish some criterions for the problems about the fostering and the custody of minor children after their parents divorced,which support the maintenance of the individual,direct and regular contact between minor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apart from some exceptional conditions.
divorce;minor children;fostering;custody
D923
A
1008-178X(2012)08-0026-04
2012-03-23
王 晖(1968-),女,湖南湘潭人,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讲师,从事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