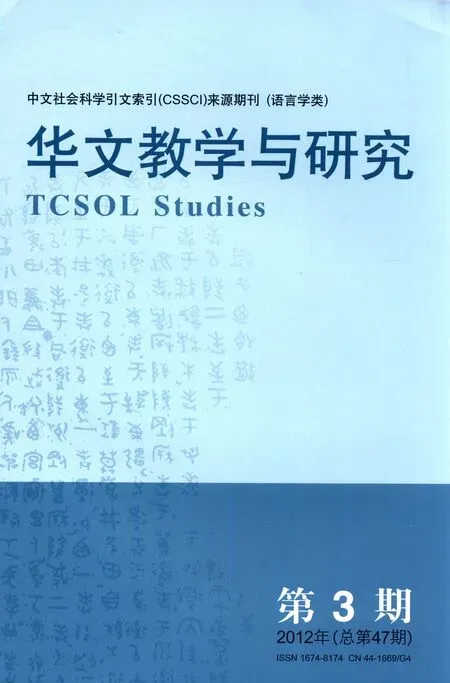语篇微观层面总分结构之语义研究①
邱冬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语篇微观层面总分结构之语义研究①
邱冬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总分结构;话语成分;量性特征;辖域
在微观层面的总分结构中,作为总提和分说的联系点可以是词、短语和句子等话语成分;总提项与分说项、各分说项之间存在多种语义关系小类;量性特征是这种总分关系组合的重要语义条件。
1.引言
1.1 语篇微观层面总分结构的研究现状综述
总分结构是常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篇章组织方式和形态,涉及篇章、章节、部分、段落等宏观层面,也存在于语段、复句等微观层面中,而后者更具基础性。
关于语篇微观层面的总分结构,即由小句与小句组合而形成的总分关系语段或复句,学界多专注于总分关系语段的研究。只有郑贵友(2002:223-224)将语段及复句层面的总分结构纳入语篇的微观功能结构中,但未作深入分析,只是描述了该类结构内部各直接构成部分之间的组合位置及各部分所发挥的总述和分述的表述职能。
就总分关系所涉及的语义范畴看,沈开木(1987:85)认为总说、分说关涉事物、事件。吴为章、田晓琳(2000:38)以为总分关系的叙述方法适于论述道理、说明事物。而刘焕辉(1983:280-297)、李宇明(2000:155)虽未作具体界定,但从其引例看,总提部分还涉及对本体性状特征的概说或评说。
就总说与分说之间的联系,有学者理解为一种照应关系。明代归有光就提出“前后相应、总提分应”之说。(李熙宗、刘明今等,1998:43-44)近代王梦曾则进一步指出“总提分应法、分提总应法……等等,都离不开意脉的相连和续接。”(宗廷虎、李金苓,1998:165)“总提分应、分提总应”应是总分关系的早期提法,其中的“应”就是“照应”之意。王聿恩(1986:72-75)、郑庆君(2003:161)论及总提与分说之间的照应关系。
1.2 本文的研究目标
关于微观层面中总说句与分说句之间的关联认识,学界已从模糊笼统的句际关联发展到具体的联系点②沈开木(1987:30)把语段中句与句之间实际发生联系的部分,双方都叫做联系点。,但未探究语义、语言形式规律。至于总提项和分说项是如何实现相互照应的,也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而语义关联是总分结构组织的根本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鉴逻辑语义及词汇语义系统的语义关系的相关理论,分析微观层面总分关系内部的语义组织规律及其语义照应方式。
①感谢审稿专家及《华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据考察,总分关系语段和复句还表现出明显的量性语义特征。本文借鉴现代汉语量范畴中关于表量手段、量值、量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考察在语篇微观层面总分关系结构内部的量性语义特征及其量的辖域,以期发现量性特征对总分关系结构组织的制约力。
1.3 语料收集
本文研究对象集中总分关系语段和复句,但由列举分承方式组成的总分结构不纳入研究范围,因为,从照应的形态看,该类结构表现为多项对多项的照应,而本文所研究的总分结构主要为一对多项的照应。语料来源涉及文学、新闻、科技及政论语体。本文共收集276例,其中210例取自《天涯》杂志(2008.1~2011.6),66例来自北大汉语语料库(CCL)网络版以及其他文章。其中,总—分结构有237例,占85.9%,而分—总结构有31例,总—分—总结构有8例,这表明,按先总后分的位序组合是语篇微观层面总分关系的主要结构模式。因此,本文的分析侧重于“总—分”结构模式。鉴于目前占有的“总—分—总”结构类语料少,为了使研究的论断更为单纯、简明,本文暂不讨论类似《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出现的“总—分—总”结构。
2.话语成分:语篇微观层面总分关系的联系点
据对语料的考察,在总分关系语段及复句内部,承担总提和分说的可以是进入话语表达中的词、短语或句子,我们把这些称之为话语成分。它们是总说句与分说句关联的真正“联系点”,包括总提项和分说项。所谓总提项,就是指具有语义涵盖包容力的话语成分;而所谓分说项,就是总提项所涵盖包容的话语成分(词、短语或句子)。充当总提项和分说项的话语成分比较灵活,可以是句子中的主题或者述题,或者是主题、述题部分的修饰成分,也可以是整个分句。
从句际语义的发展看,在“总—分”结构中,总说句是一个局部篇章话题句,句中的总提项可以视为派生并铺陈各分说项的语义生长点?①沈开木(1987:251)提出“生长点”是派生或引出别的语义的语义。。一般而言,总说句中包含一个或多个总提项,因而存在一个或多个语义生长点,在语义发展上形成常见的单线推进式和复线并进式。前者指总说句中只有一个总提项,后续句中仅有一组分说项与之照应;后者指总说句中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总提项,由两组或两组以上分说项分别与之相照应。例如:
(1)冬天,我学会了很多很多的游戏。捉迷藏、滚铁环、跳绳、打水漂、在厚的冰层打得碌,但我们最喜欢做的还是跳房子。②文中所引的语例,“总提项”和“分说项”分别用双下划线和单下划线标注。(《天涯》2008(6):146)
(2)喀什葛尔一带[A]出产奇花异果[B]。叶城a1的石榴b1,英吉沙a2的巴旦杏b2,伽师a3的甜瓜b3,疏附a4的阿月浑子b4,疏勒a5的榅桲b5,阿图什a6的无花果b6,吐曼河边a7的沙枣树b7,还有一种长得疙里疙瘩的化石模样的土梨b8,使人如数家珍。(《天涯》2009(4):147)
例(1)中,双下划线部分的话语成分为总提项,也是语义生长点,引出与之相对应的单下划线部分的分说项,两者形成照应关联——此为单线语义推进。例(2)中,话语成分A和B都是总提项,也是两个语义生长点,分别引出与之相对应的两组分说项,其中A与a1至a7对应、B与b1至b8对应,各自形成话语成分的照应关联——此为复线语义并进。
此外,语料中还发现少数由两个总提项对应一组分说项的情况。例如:
(3)在乡村,相骂是必修课,相骂是启智课。它让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乡亲们,认识了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方块字,一个个有情有貌、携手并肩的词和词组,还有一句句充满激情、旋律跳动的话语,一篇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天涯》2009(5):150)
上例中,单下划线部分的一组分说项同时与两个总提项“必修课”、“启智课”形成语义照应。
在“分—总”结构中,处于后文的总提项是前文各分说项的语义汇集点,它是在详述多个分说项的基础上所作的语义统合性表述。例如:
(4)杨炕生就时时瞅着祝云芬。祝云芬下地了,祝云芬收工了,祝云芬换新袜子了,祝云芬的发卡换了一个了,祝云芬的手腕上套了一个皮筋了……杨炕生眼角藏了祝云芬一切动静。(《天涯》2010(2):138)
例(4)中双下划线部分的话语成分为总提项,是前文单下划线部分的各分说项的语义汇集点,两者形成照应关联。
可见,总说句与分说句之间逻辑语义关系的搭建,是以话语成分的语义关联为基础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总分结构内部联系点之间的语义关系小类的重要前提。
3.总分结构内部联系点的语义关系小类
从语义范畴看,总提项包括事物(人、物、现象)、事件、性状(性质、状态),各分说是对其的具体铺排。二者之间的“照应”不限于指代性照应,还涉及非指代性的语义呼应关系。
总提项是上位层次,分说项为下位层次,它们之间形成多种语义关系小类。而聚合于同一总提项之下的各分说项之间也存在多种语义关系小类。下面按照总提项所属的语义范畴,描述总提项与分说项、各分说项之间的语义关系小类。
3.1 事物范畴
当总提项为事物性范畴时,与之照应的分说项则是其所指概念的外延。各分说项因来源相同、相异而构成不同的语义关系,也影响着总提项与分说项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
一是各分说项所指基本源于同一规约性语义范畴。
充当总提项的话语成分,或者是代表一类事物的上位范畴词,分说项是其所指范畴中的个体成员;或者是包含多个部件的整体事物名词,分说项是其所指整体的部件。从语料看,总提项与分说项之间是固定或相对固定的层级结构关系,所构成的语义关系主要表现为上下义/准上下义、集合—元素/准集合—元素、整体—部分/准整体—部分等关系类型。
若各分说项都源于同一语义范畴,属于上下义关系中的下位成员可形成同类、同(家)族及层序语义关系;属于集合—元素关系中的各元素,形成同集语义关系;属于整体—部分关系中各部分形成同体语义关系。如例(1)中总提项与分说项构成上下义关系,各分说项形成同族关系;例(2)总提项[A]与分说项a1至a7构成整体—部分关系,各分说项聚合成同体关系;总提项[B]与分说项b1至b8构成上下义关系,各分说项聚合成广义的同类关系,即分属不同小类,但仍属于同一大类。
若绝大多数分说项属于同一语义范畴,个别分说项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同一范畴,但与它们存在特定的关联,在属性特征上大致相同或相似,彼此可形成准同体、准同集、准同类及准层序语义关系。如上文例(3),分说项“词、词组、话语、文章”是语言系统各级单位,“方块字”则是语言符号,但与这四级语言单位存在关联,因此,五个分说项形成准层序语义关系,与总提项“必修课、启智课”构成准上下义语义关系。
二是各分说项所指分属不同语义范畴。
“一组词项,如果包含着相同的属性语义成分,就可以形成同属语义关系。”(周国光,2005:77-85)事物具有形态、质料、来源、功能、数量、地点等多重属性,而属性的多重性使得跨语义范畴的各分说项,它们所指的事物在特定情境中也有可能在某些或某一属性上存在相似性,从而聚合在同一个总提项之下,而形成同属语义关系。而充当总提项的名词性短语是个动态的集合表述形式,常标示各分说项具有的共同属性,我们把这类短语称为属性集合短语。①参照周国光(1990)提出的“属性集合名词”这一术语。总提项与分说项构成临时上下义关系。例如:
(5)真带劲儿,橱窗里的东西琳琅满目:有小人儿、带棱的色拉碟儿、没法用的长嘴瓶子、刀、叉、挂钟。(CCL)
(6)进取的路线图各式各样:有从钢琴班到书法班到英语班到奥数班到高考强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着蛇皮袋在马路边被工商税务追得尘土飞扬的;有搭便车——移民移入了钱柜、嫁人嫁给了元宝的;有破窗而入、翻墙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有凭着假证件居然蒙混过关的。(《天涯》2010(1):54)
例(5)中,分说项“小人儿、带棱的色拉碟儿”等所指属于跨类事物,表现出[+同空间范围]、[+商品]等属性的暂时性相同,彼此形成同属语义关系。例(6)中,分说项所述的是不同的社会现象,但总提项“进取的路线图”却标示了它们都具有表达者所理解的[+进取]的共同属性,从而聚合成同属语义关系。
3.2 事件范畴
这里所讨论的事件范畴是对多个事件的归类。充当总提项的上位形式,有的是对几个事件的合说;有的是对一类事件的概括;有的则是一个大事件,包含着若干个隐性的小事件。作为叙述具体事件的分说项表述形式多为动宾短语或包含行为动词的句子。从行为的角度看,不同事件可能存在行为方式、目的、性质等方面的属性相似性,由此构成同方式、同目的、同性质的语义关系;从行为关涉对象看,不同事件可以是由同一施事者实施或参与,它们由此形成同(来)源关系。这些语义关系小类可归入上一层级的同属语义关系,总提项与分说项之间构成“综合—具体”语义关系。如:
(7)今晚要燃放许多的鞭炮,去祠堂祭祖要放,吃饭时要放,睡觉前要放,祭灶神要放,起床后要放,出“天方”要放,不能乱了次序。(《天涯》2011(2):116)
例(7)中,总提项表“放鞭炮”这一类事件,分说项分述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放鞭炮的具体事件,它们因“放鞭炮”的行为方式相同,形成同方式语义关系。
又如,上文例(4)中,“下地、收工”属于劳动类事件,“换新袜子、换发卡、套皮筋”属于生活类事件,它们因相同的施事者而形成同源语义关系。
3.3 性状范畴
同一事物范畴的成员具有相同的性状,不同的事物也可能存在相同的性状。在总分结构中,表性状范畴的总提项往往就是这些相同性状的抽象概括,而与之照应的分说项则具体描摹个体成员或局部的性状、性状的表现方式及程度。总提项的表述形式包括修饰性定中短语、“的”字短语、限定性定中短语、形补短语、主谓短语。在语义关系上,各分说项描述的性状义中均蕴涵总提项所描述的整体性状义,分说项与总提项构成蕴涵关系。例如:
(8)再旁边是厨房[A],所有的一切,都年代久远[B],桌子a1苍白,如同一块大饼b1,灶台a2早已被熏得漆黑b2,高高的门槛a3,磨损得厉害,深深地陷下去了b3。(《天涯》2010(3):171)
例(8)中A组表事物范畴,“桌子、灶台”是厨房用具,“门槛”是厨房自身的构件,它们形成准同体语义关系;总提项“厨房”与分说项构成准整体—部分关系。B组表性状范畴,分说项b1、b2、b3均蕴涵着“使用时间长”的意义,是总提项“年代久远”的具体表现状态,因此,它们构成蕴涵关系,而各分说项之间因蕴涵义相同而具有同义关系。
通过对总分结构中联系点之间语义关系小类的分析,可进一步认识到分说项与总提项之间实现多项对单项的照应方式。表事物、事件范畴的分说项与总提项之间,表现为多个下位成员或元素照应某一集合,或以多个部分构件照应整体事物,这两类可统一归入上下义回指①徐赳赳(2010:249)将名词回指中的上下义回指分为“综合—具体”关系和“整体—部分”关系。。表以性状范畴的分说项与总提项之间表现为多个局部的性状描写义照应整体的性状概括义,这类语义照应可视为谓词性照应。据统计,总提项表事物、事件范畴有245例,占总量的88.8%,而表性状范畴的仅31例。这表明总分关系语段、复句内部的语义照应倾向于上下义回指。
4.总分结构中的量性特征及表量词语的辖域
4.1 总分结构的量性特征
语篇微观层面总分结构中的量性特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4.1.1 量性特征之一:总提项用语具有量性义
关于表事物、事件范畴的总提项用语,集中在以下两类:
一类是对应涵括多个体的体词性词语。词汇方面以表具体事物名词为主,比如:货物、木器、树林、花(朵)、村庄、展品、蔬菜、工具、豆子、山果、零食、作物、早茶。少数是抽象名词,如:表情、规矩。名词性短语包括固定短语,如:油酱铺、家常菜、农产品、办公用品。也有一些临时性自由短语,如:利益共同体、嘈杂的世相。
此外,“杂N”和“方所词+的+N”结构格式出现的频率也较高。比如,杂活、田里的活、舞台上的东西等。
另一类是包含多个部件的事物的体词性词语,以处所词为主,如屋子、厨房、房子、镇子、故乡、街等。少数是指称人、书、汽车、老家(方言:棺材)等实体的。
上所列举的词或短语的中心语都是上位范畴词,基本层次范畴词,或是临时生成的上层语义结构,它们均表现出[+涵盖包容力]或[+集合义]的语义特征,具有归类或“汇集功能”(collecting function)。(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2009:90)在现实世界中,一个整体事物包含的构件有限,一个集合包含的元素存在有限多个或无限多个。这反映在语言表达中,具有[+集合义]的体词性词语包含的成员也存在数量有限或无限的可能,但这些词语的“汇集功能”只能表明具有量性义,但具体量值还是隐性、模糊的。
关于表性状范畴的总提项用语,多由形容词及短语充当,如“忙忙碌碌、奇特、讲究、体面、雄伟、巧”等。这类词语虽是描写事物属性特征,但词义中含有量度义,并且大部分都能接受高量级程度副词的修饰,进行程度定量。
此外,还有少数评价人的词语充当总提项。如:多面手、多才多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些词语都带有表恒定大量的词汇语义。
4.1.2 量性特征之二:表量词语的高频使用
现代汉语量范畴中的表量手段极其丰富,但出现在总分关系语段、复句中的表量词语以词汇性手段为主,包括以下几类:
A.数词+量词+表物名词。可以是个体量词和度量词,如“15公斤的银首饰”表确量。集合量词仅限于不定量词,如“一叠账单”表多量。借用名量词,常见结构是“一量NP”,比如,一地东西、一身武艺,这种结构表主观大量。
B.约数词语。常见的有“好多、许多、很多、若干、好几、好些”等。
C.各+量、每一+量。这两类格式中的量词多为个体量词,数词限于“一”,用于修饰表物的具体名词或抽象名词。如:各种兵器、每一个细节。
D.满N、V满、全N、所有的N,这四类格式都表物量,如:满野、挂满、全村老幼、所有的空间。
C组和D组在量值上都表示全量,但视点不同,C组是散点式,把某个整体分解为多个个体,通过遍指其所有成员,由单个叠加成整体的全量;D组是以整体视点看某一场所或某一范畴,用总括性的语言形式表达整体总量。
E.空间词语,如四周、这里那里、到处等比较常见,表周遍义,量值为全量。它们作为事物、事件依存的空间因素,可以间接表物量。
F.副词。常见的是表最高级的相对程度副词是“最”,表极量和高量级的绝对程度副词“太、极其、极、很、非常、十分、特别”。范围副词主要有表全量的“全(是)、都、尽是、完全”。频率副词有表极高值的“总是、老”,表较高值“时时、经常”,表中度值的“不时”。时间副词,如“逐渐、陆续”,具有[+逐次推移义、过程义],表动态变化量。
G.语料中有一些形容词语,如“杂乱、不同的、繁多、齐全、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千姿百态”等,它们的词汇义中蕴含多量、全量或极量,并且表极量的多属于虚量。
少数动词,如堆积、堆叠等,词汇义中也蕴含多量值。
此外,还采用体词重叠手段表量,强调周遍、逐指,表全量。包括名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数量词的重叠,如:家家、样样、一盘盘、角角落落、哪儿哪儿、这样那样。使用特殊句法手段表量的仅限于少数表周遍性的构式,如“没一样不V、什么N都V/AP”等,表全量。如:没一样不吃,什么节目都看。
这些表量词语在量性上有多种形态:确量—约量,实量—虚量,客观量—主观量。根据表量词语在篇章中语义指向的对象所属的范畴,它们归属的量范畴主要为物量、性状量(包括程度量和变化量)和动量。这里的动量侧重与事件动作相关的频度量,由频率副词表量。这些表量词语的量值情况统计如下:

表1:量值统计表
表中合计数268,是276个总语例中出现的在量值上可辨认的表量手段总计数,共占总语例的97.1%,显示了表量词语在总分关系语段、复句中的高频使用。各类量范畴使用频率的序列为“物量>性状量>动量”。从上表可以发现,表量词语有明显的量值倾向,即物量倾向于多量和全量;性状量范畴中以程度量为主,在量值上倾向于极量、高量级;动量(时量)方面的表量手段较少,但量值倾向于极高值、较高值。
4.2 总分结构中表量词语的辖域
此表量词语的辖域指的是表量词语在总分关系语段、复句中所及的范围及作用力。
4.2.1 表量词语对总提项的作用力
从语料看,不管总提项自身是否具有量性义,借助总提项之外的各类表量词语赋量是很普遍的。它们的位置也很灵活,处于总提项所在句子的主语、小句主语、谓语、定语、状语、补语,是近距离的赋量;位于总提项所在语段、复句中的前后相邻小句中的表量词语,则是远距离的赋量。赋量手段可以单用,也可以多种手段连用。例如:
(9)石头间是杂乱的鞋印:橡胶水鞋的,胶鞋的,钉子草鞋的,布鞋的,偶尔还可以见着皮鞋的。26码的,36码的,42码的……说不清码数的。重重叠叠,杂乱无章。鞋印间星星点点地散落着烟蒂:叶子烟的,过滤嘴香烟的,平嘴纸烟的。(《天涯》2011(3):137)
例(9)中,定语“杂乱”、方式状语“星星点点”、谓语“散落”及后续小句“重重叠叠”的量性义均指向总提项——“鞋印、烟蒂”。离开这些表量词语的辅助赋量,“鞋印”就无法自足地充当总提项。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总分关系语段、复句中出现的表量词语对总提项的作用力:
ⅰ.当总提项为名词性词语时,表量词语作为它的修饰成分,使总提项成为“量化名词词组”(quantified noun phrase)(徐烈炯1990:247),直接量化并显化总提项的量性语义。
ⅱ.当表量词语出现在总提项所在句子的其他成分位置时,或当表量词语出现在与总提项所在句子邻近的句子中时,则使整个句子成为一个“量化句子”(quantified sentence)(徐烈炯,1990:247),其语义指向总提项,直接或间接量化、显化总提项的量性语义。
在表量词语以上述方式直接或间接量化事物、事件、性状的同时,其量值特点,尤其是多量、全量,极量、高量级的倾向提升了相关的词、短语的语义涵盖力。这恰是这些词语充当总提项的重要语义前提,使得位于分说项之前的总提项在语篇中能产生更明显的篇章启后功能。同时,表量词语的赋量使得充当总提项的话语成分所传递的信息更具概括性,这种表达还易激发接受者产生进一步了解关于总提项的具体内涵或外延的心理期待。可以说,表量词语的使用更突出了以分项铺陈的表达方式实现与总提项相互照应的合理性。
而位于各分说项之后的总提项,也需要由上述表量词语赋予一定的量值,这样方具有包容前文所列分说项的涵容力。
4.2.2 表量词语对分说项的管辖
分说项具有多项性,这既与总提项有关,也与表量词语的跨句管辖作用相关。分说项在项数上与总提项、表量词语形成一定的数量照应。吴为章、田晓琳(2000:38)认为在总分关系语段中总说和分说都用数量词语时,一般都有明显的数量照应。此处所谓数量照应,是指所列举的分说项数目,能够与总提项自身所含有的量性义或由表量词语赋予的量性义相对应。
据考察,表量词语对分说项的管辖作用与其位置存在关联,当其位于分说项之前时管辖力强,而位于分说项之后时则无明显管辖力。因此,表量词语对分说项的管辖更多地体现在“总—分”结构的组织中。不同形态、量值或量级的表量词语,对分说项的辖域能力也不同。从语料看,各分说项对总提项的数量照应的实现方式有以下两种:
一是全息排举式。当表量词语为数量词或约数词语,属于实量,并倾向于表少量值时,那么对分说项数有严格的限制,要求以全息排举的方式将总提项包含的成员逐一呈现出来。各分说项的总和与总提项自身应涵盖的子集数量完全一致的,形成等量照应。例如:
(10)现在他已经听出了四种雨滴声,雨滴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他感到是父亲用食指在敲打他的脑袋,而滴在树叶上时仿佛跳跃了几下,另两种声音来自屋前水泥地和屋后的池塘,和滴进池塘时清脆的声响相比,来自水泥地的声音显然沉闷了。(余华《现实一种》)
(11)歌舞厅里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很丰富:报社记者、电视台主持人、酒厂职工、卖服装的个体户。(《天涯》2009(2):136)
例(10)中,所排举的“屋顶上、树叶上、屋前水泥地、屋后的池塘”的雨滴声与总提项前面的表量词语所明示的量值相等。例(11)中,表量词语“几个”标示总提项表少量,不存在全息排举的困难,四个分说项应是足量的。
二是部分列举式。当表量词语是表多量、极量或高量级、极量级,并且倾向于虚量时,对分说项数的约束力稍弱。此时无法用全息排举方式呈现总提项所涵容的成员,分说项可以只列举总提项所表示的集合中的部分子集。部分列举式存在无标和有标形式。分说项后面出现“……”或列举助词“等、等等”,是列举未尽的常用标记。语料中,部分列举的分说项多以典型成员或显著度高的成员为择取标准,并且项数一般为三项或三项以上,只有多项代表性成员之间的加合,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表量词语与总提项所限定的量值。例如:
(12)王家卫的一部《花样年华》,叙述于发生在六十年代的香港故事。然而存留于人们记忆的,却全然是一幅物化的上海图景:喋喋不休的上海话,令人眼花缭乱的旗袍,收音机里也播放着周璇的老歌不绝于耳。(《天涯》2011(1):181)
例(12)中副词“全然”兼表程度和范围两方面的高量级,影片中呈现出的旧上海图景很多样,但影评人只择取最具代表性的“上海话、旗袍、周旋的老歌”等元素,并用“喋喋不休、令人眼花缭乱、不绝于耳”等描述语凸显其显著度。
当然,表量词语的量值对分说项的管辖力也存在一定的弹性,还受到其他因素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表量词语为全量值的情况。如果总提项所指范畴中包含的下位成员是有限多个,存在逐一排举的可能,并且在语篇表达者方面也有全息表达的需要,就必须用全息排举式呈现所有的分说项;反之,则可采用部分列举式。例如:
(13)晚年的父亲已经集天下男人所有的毛病于一身:酗酒、好赌、懒惰、几个月不洗澡和对老婆的傲慢,还不遮不掩地到陈村光顾一个四十多岁的贵州妓女的被窝。(《天涯》2009(3):98)
例(13)中表全量的“所有”对总提项“天下男人的毛病”进行全称量化,从语篇语境看,作者出于强调“晚年的父亲”令母亲厌恶、疏远的原因,而全息排举他父亲实际存在的毛病。
又如上文例(8),“所有的一切”表全量,但分说项要排举厨房自身的全部构件以及放置于厨房中的所有物件,操作有难度。“桌子、灶台”是厨房的典型用具,需求度和显著度都很高,“门槛”是厨房自身的构件,恒久度高。因此,仅描述这三个“点”的性状,就足以唤起读者想象“厨房”年代久远这一整体属性特征。
5.结语
在语篇微观层面总分结构中,总分关系实际上是各句或各分句中具有上位层级管辖能力的话语成分与若干下属的话语成分近距离地聚合。通过描述分析总提项与分说项之间、各分说项之间存在的各小类语义关系,我们发现,总提项与分说项之间存在的上述各类语义照应,各分说项在语义属性上的相同或相似关联,是构成总分关系的内在语义依据。
而语篇微观层面总分结构中的量性特征,是总分结构组织的重要语义条件,因为总提项的篇章启后功能,分说项的多项性及项数选择,都受到这一语义特征的制约。
限于篇幅,本文例析时未援引“总—分—总”结构类的语例,但上文所归纳的内部联系点的语义关联及结构内部的量性特征、表量词语的辖域等组织规律是带有普遍性的,对于微观层面的“总—分—总”结构的语义组织同样具有解释力。
刘焕辉1983《语段修辞初探》,载中国修辞学会(编)《修辞学论文集》(第一集),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宇明(主编)2000《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熙宗刘明今等1998《中国修辞学通史》(明清卷),吉林教育出版社。
沈开木1987《句段分析》(超句体的探索),语文出版社。
王聿恩1986《句群中的总说和分说》,载田晓琳(编)《句群和句群教学论文集》,新蕾出版社。
吴为章田晓琳2000《汉语句群》,商务印书馆。
徐赳赳2010《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徐烈炯1990《语义学》,语文出版社。
宗廷虎李金苓1998《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
郑贵友2002《汉语篇章语言学》,外文出版社。
郑庆君2003《汉语话语研究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
周国光1990《关系集合名词及其判断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2005《语义场的结构和类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2009《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彭利贞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宗世海】
《“华文教师证书”认证标准》审稿会在暨南大学召开
2012年9月18日,《“华文教师证书”认证标准》审稿会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召开。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李晓琪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马燕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齐沪扬教授,香港教育学院陈学超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李盛兵教授等12位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就认证标准中各子系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对评估体系逐条进行了评阅。专家组充分肯定了标准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议。
《华文教师证书》实施方案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委托暨南大学承担的一项重要科研课题,由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多名具有丰富教学及科研经验的教师组成课题组,时任暨南大学副校长贾益民教授任组长。2012年初,课题组向国务院侨办提交了认证方案初稿。半年多来,课题组就“认证标准”进行了专题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审稿会上,课题组负责人贾益民教授向专家组报告了工作进展,对“标准”二稿进行了具体说明。
国务院侨办文化司汤翠英副巡视员主持了此次审稿会。出席会议的还有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邵宜常务副院长、曾毅平副院长等。
(华文学院)
The Study of the Semantic Relations on General-specific Structure from the Micro-discourse Perspective
Qiu Dongm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631 China)
general-specific structure; discourse composition; quantity characteristic; scope
At themicro level in the General-specific structure,the points that connect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parts may be words,phrases,and sentences.There are a variety of semantic subcategories for the generaland the specific parts,and the all the specific parts.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 is the important semantic condition of this general-specific relationship.
H030
A
1674-8174(2012)03-0072-09
2011-09-01
邱冬梅(1972-)女,江西石城人,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修辞学、现代汉语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