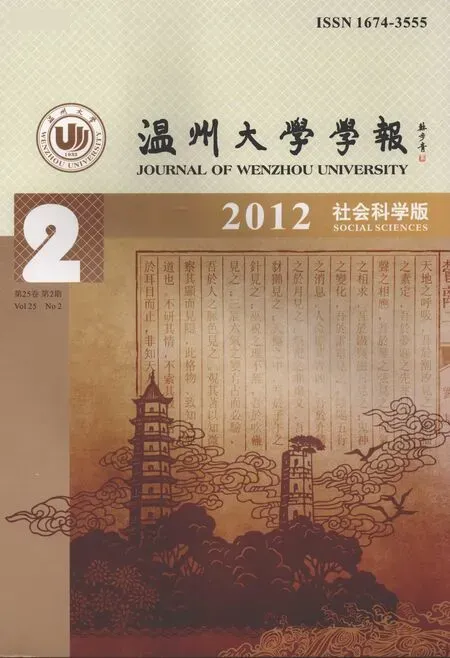透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看华人眼中的“美国梦”
肖丽花,程丽蓉
(1.浙江财经学院教务处,浙江杭州 310018;2.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透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看华人眼中的“美国梦”
肖丽花1,程丽蓉2
(1.浙江财经学院教务处,浙江杭州 310018;2.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的作品,充满对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处于多重困境之华人的人文关怀。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一位有着中西文化双重经验的作家自我心历的写照,通过“梦想:天堂美国”、“‘他者’:无根漂浮”和“碎梦:无路逃遁”三个层面对她那一代人的“美国梦”进行了描写和剖析,力图通过现身说法,让国人了解旅美华人的真实生活。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美国梦
美籍华裔作家於梨华祖籍浙江,1931年生于上海,1947年赴台,1953年台湾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之后一直留居美国,至今已近六十年。於梨华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从描写“无根放逐”的留学生,到塑造“觉醒的一代”,进而关注落地生根后的华人移民,以及近年的知识老人题材等几个阶段。她坚持用汉语写作,手笔细腻、满蕴乡情。她的小说涉及留美、旅美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精神状态,被誉为“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一代的代言人”。於梨华是最早开始以台湾旅美留学生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在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对她那一代人眼中的美国梦进行了深入的描写和剖析。
一、梦想:天堂美国
异域“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已是19世纪后期,出国留学成为潮流更是晚至20世纪初。日本是有志之士的首选目标,并于1896年掀起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高潮。1915年后日本的扩张政策导致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美国作为新兴强国受到了以胡适、林语堂、徐志摩等文人学者为代表的众多知识分子的青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和美国分属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国人留学美国的可能性。台湾则因与美国的特殊联系,大量吸收美国的先进科技文化,崇美的意识迅速盛行,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继 1896年以来的第二次留学高潮。不过,此时的留学目的及对美国的想象已与之前的学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留学美国进而移居美国是台湾民众的成功标尺,这源于对自由生活和美好前途的向往,也不乏崇洋媚外意识。由于美国传入台湾的信息都是经过择选的,处于强势地位的美国文化总是扮演引领者的角色,造成了美国什么都好的假象,加上受中国人在外“报喜不报忧”的信息的影响,使得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想象更如人间天堂般,也因此把能在美国留学、定居视为成功的象征。
於梨华亦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跨出国门、远赴美国并追寻梦想的。她最初是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接着美国、迎接着她的新生活的,在给林海音的信中她表达了赴美途中的喜悦:“……船上生活已将两周,终日凝望那片永不休止的海水未感厌倦,它的颜色日夜不同,在晚上,星光下虽觉更庞大可怕,但也更动人,我真恨自己笨拙的笔,写不出对它的喜爱来!”[1]《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本意虽不想出国,但不能辜负父辈的殷殷期盼,最终还是出国了。临行前,他独自去学校门前道别,并对着棕榈树许愿:要挺直、无畏而出人头地。於梨华借牟天磊的愿望表达出了当时人们的梦想。无论是於梨华还是牟天磊,二者手心里都攥着两个梦想——学成与业,都认为负笈去国便会前程如锦。
二、“他者”:无根漂浮
一切的辛酸在抵达美国的那一刻真正拉开了帷幕:跨出国门的华人,由于各方面的差异,尤其经济能力与在美国社会生存之需求的巨大差距,多数人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只能打工维持生活,且从事的都是比较底层的劳作,这样的状况去美国前何曾想到。加之两地历史文化的差距,“很多美国人,尤其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中国人,不,对东方人,就有一种歧视,当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有歧视,只是他们将它掩饰得不露一些痕迹而已。”[2]20-21这一切都影响了在美华人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置身于“他者”民族与异质文化环境中,此前的憧憬遭逢了现实境遇,这种反差、失落和痛苦折磨了一大批人。那一代留美学生,总是有着相似的经历和苦恼:刻苦地学习伴随着艰苦地打工生活,以及学成后不知路在何方的怅惘。
早年从中国大陆赴台而后又留居美国的於梨华,与一批美籍华裔作家一样,承载、背负着双重的身份。他们与原先熟悉的文化场域渐行渐远,而在新的地域里又难以融入主流社会,只能作为异质文明里的“他者”,心底或多或少都交织着多重无法言说的情怀。于是,敏感的作家开始寻找,寻找属于自身的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於梨华援引王维《桃源行》中的诗句“辞家终拟长游衍……不辨仙源何处寻”作为短篇小说集《寻》的楔子,以表达内心的希冀和诉求。“寻”纠缠于於梨华的灵魂深处,挥之不去,不仅表达了作家恍惚、迷乱、无从捕捉的无根心态,也是她们那一代留美学人寻找文化归属的内心写照。於梨华在作于 2000年的散文《三十五年后的牟天磊》中怀想了 35年后在美国固守着自身清高而又清贫的牟天磊。这时的牟天磊已经退休,他有的是“一份落寞、一份淡泊、一份远在声色享受之上的意境的开拓,一份‘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的出世心态”[3],这何尝不是於梨华对步入老年的自我人生经验的观照,也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她们那一代留美学人至此都与美国的主流文化存在着的疏离。
於梨华对美国的体验混合着复杂情感,虽然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她在多种场合都明确地表明自己是个中国作家。她也确实一直在坚持用汉语进行写作,并反馈给台湾和中国大陆读者。很多人在国外一住经年便会中文退步,於梨华却勤于中文书写,且一篇比一篇精彩,於梨华用汉语进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要缓解自身在故国之外,处于异质文化之中或多或少的身份焦虑。在文化认同上,美国文化一直作为异域文化而存在。反映到小说文本中亦是如此,《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没有办法认同美国主流社会那种只为金钱、贪得无厌而人情冷漠的情状,他选择了独处。牟天磊在与美国朋友交往时总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但是他并不觉得悲哀,“他有个安慰自己的念头:我在这里不过是暂时的,暂时的圈外人,有一天我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和自己的人在一起,我就不再会有这个孤独的感觉了”。可以说他的心不在此,他的文化根基依然在太平洋的那一端。
虽然於梨华不属于才华横溢型的作家,但她能用融铸了真情实感的现实生活、扎实的功底和有深度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人心。“在台、港留学生的书架上常常看到於梨华的小说。谈天的时候,大家也常常提到她书中的人物。”[4]旅美学者夏志清称赞於梨华是“旅美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求自己艺术的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5]人。马相武认为:“於梨华对中国文字的掌握,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她笔下所塑的人物,往往充满了一种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的真实感与生命力。”[6]半个多世纪留居美国使得於梨华对美国的认识全面、广泛而深入。或者可以说,在她身上已然有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双重印记。於梨华借小说人物说:“像我们这样的半吊子,一脑子都是矛盾的思想,又是中国的,又是美国的。”①参见: 於梨华. 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下文出现有关本书内容均出自该版本, 不再标注.於梨华们实际上已成为拥有中美双重文化经验的“两栖人”。於梨华曾著文回忆自己的旅美经历,言说中苦楚与无奈常相伴左右,然而她是坚强的,她说:“对某些人来说,得不到支持可能就会沉沦下去,可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你抓不住东西就得拼命想办法了,我是属于第二种人。”[2]4留美华人中坚强并获得不俗成就者毕竟是少数,大多都如牟天磊般虽获得了学位却无法真正站稳脚跟,也并不快乐,只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人物。於梨华通过文本《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还原了这类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孤寂。“北美的生活和文化视域无疑为於梨华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和关怀,而中国的文化经验与记忆则参与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学表达。”[7]不论她的作品关注的人群及写作样貌如何变迁,总有一条潜流隐含其中,那便是中国留学生或移民的认知方式与价值观与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难以融合的关系,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与之息息相关。
於梨华塑造的很多角色“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受到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冲击,产生认同的焦虑,成为亦此亦彼又非此非彼的边缘人”[8]。小说《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作于1965 –1966年间,其故事发生的背景在台湾,但又无时无刻不与“美国”发生多方联系,小说情节也是在中美两种文化甚至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间展开的。文本通过描写身处异域的中国人的生存压力与文化困境凸显出混合着作家复杂情感的美国形象。
通过主人公对故土无尽的怀念反衬作家对美国的失望。牟天磊回国对父母的话可见一斑:“其实美国并不是象许多人想的那样天堂。我从前看美国电影,总以为在那边,每家房子都象贝佛来区里的房子一样,风景都像日落大道一带一样。一切都是电,每人都有钱,事实上才不是那样呢!芝加哥三十几街到四十几街一带的脏和穷,比我们这个巷子里还胜十倍。”被孤独寂寞摧残着的牟天磊怀念着十年前在台湾的美好生活,追忆着失落了的爱情,感到虽然“拿到了钱……失去的却全是天真的幻想美梦,以及美梦才能带来的陶醉……得到的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给他的东西,而失去的,却永远的失去了。”这里表现的“无根的一代”的无奈与惆怅。
三、碎梦:无路逃遁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的结尾没有直言牟天磊的去留,太平洋两岸间的何去何从实难决断。在美国十年,父母骨肉难相见,相爱恋人各自飞,而亲情和爱情恰恰是牟天磊甚为看重的,他在美国虽学成也有了工作,但是内心的期待却全然失落,只余空虚。然而台北在他出国后的十年中也变了,牟天磊对精神故土的皈依也失却了。遭逢了双重的打击,精神变得无处逃遁,十年的美国经历不仅敲碎牟天磊的美梦,而且对故土也变得陌生了。
当被出国大潮裹挟着来到陌生的美国时,於梨华内心并非有很明确的理想,出人头地的愿望暗藏在心,但又不是那么清楚。其散文《归去来兮》的楔子:“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9]就彰显了她从在美国历经挫折以及回国后倍感失落的经历中深切体会到的迷惘的心理。在她的作品中,这一点也得以反映。当被妹妹问及在美国学了什么时,牟天磊不假思索地说:“学到了不做梦。”十年的美国生活掏空了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和情怀,而妹妹也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变化——饱经世故。牟天磊在美国觉得是局外人,可是回到台北后“融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忽然有股难以解释的悲哀与落寞,将他紧紧地裹着。……他仍像个圈外人一样地观看别人的欢乐而自己裹在落寞里,不是他不愿意融进去,而是十年在海外的孤独生活已僵化了他……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回来的当晚,牟天磊就被各式各样崇美的因素包围,他很苦恼,他想诉说“他在美国十年所尝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苦。以及他回去之后体会到的意想不到的喜,以及喜里的悲。”而他自己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无家可归,什么是精神无处皈依。
四、结 语
上世纪50 – 70年代的旅美华裔台湾作家群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旅居海外,但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政治潮流和历史变动,对他们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热切关注中国民族和文化前途和命运”[8]。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对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心理进行了冷嘲热讽,将美国视为“背景”来观照处于其间的中国人,也观照对美国充满幻想的中国人,并意图将切身感受传输给现实中的人们。20世纪70年代於梨华回到祖国大陆看到崇洋心理在很多青年中弥漫后,即刻责无旁贷又义愤填膺地说:“难道在经过了百年屈辱,终于站了起来,挺直地站了三十年后的中国人,又要在洋人的面前低声下气了吗?!”[3]27於梨华身在美国,心却常念祖国,她通过《人民日报》语重心长地向青年朋友讲述了自己的留美经历,想要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打破文化殖民,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知道一个客观的美国。
[1] 林海音. “野女孩”和“严肃先生” [C] // 於梨华. 情尽.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9: 2.
[2] 於梨华. 人在旅途: 於梨华自传[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
[3] 於梨华. 三十五年后的牟天磊[C] // 於梨华. 别西冷庄园.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221.
[4] 杨振宁. 序[C] // 於梨华. 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4: 2.
[5] 夏志清. 序[C] // 於梨华. 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2.
[6] 马相武. 序一[C] // 叶枝梅. 海外华人女作家评述.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 3.
[7] 刘桂茹. 在中国记忆与北美经验间游移: 於梨华小说里的华人离散群体[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2007, (4): 102-107.
[8] 朱立立. 在美国想象与中国想象之间: 冷战时期台湾旅美作家群的认同问题出论[J]. 文学评论, 2006, (6):186-192.
[9] 於梨华. 归去来兮[C] // 於梨华. 别西冷庄园.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15.
Study on “American Dream” of Chinese through Yu Lihua’s Novel Seeing the Palm Once More
XIAO Lihua1, CHENG Lirong2
(1.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China 310018; 2. Literature Department,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 637002)
Chinese-American writer Yu Lihua’s literatures overflow with humanistic care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who were in the plight of the multi-cultural encounter. Yu Lihua’s novel Seeing the Palm Once More reflected the inner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writer with double cultural experience (experience of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novel, the writer’s generation’s “American Dream” was described at full length and analyzed in greater depth through three levels: “Dream (America is a Heaven)”, “the ‘Other’(Restlessness in America)”, and “Broken Dream (Belonging to no Society)”. Through the novel, Yu Lihua tried to make Chinese Youth have an objective knowledge of America with the real experiences.
Yu Lihua; Seeing the Palm Once More; American Dream
I206
A
1674-3555(2012)02-0066-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2.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周斌)
2010-03-09
肖丽花(1981- ),女,江苏海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