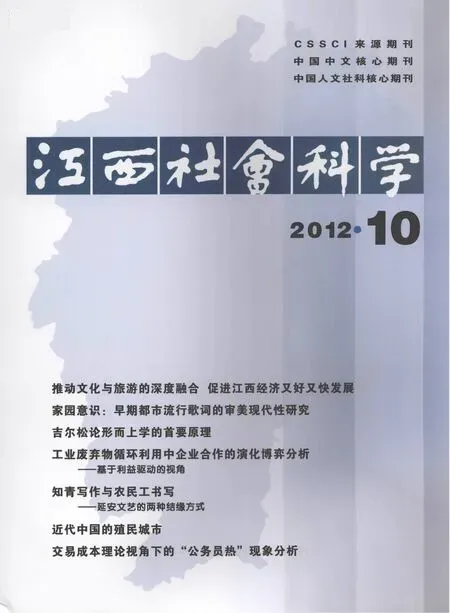经典与商业的结合:托尼·莫里森的文化市场开拓及其启示
■史鹏路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1988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93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12月亮相“奥普拉读书会”之前,莫里森已经在世界文坛拥有稳固的地位。在论述文化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时,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艺术上的成功必然导致市场的缺失。然而,托尼·莫里森却成为反证这一论断的典型范例。她在保持经典性的同时,通过与奥普拉的合作积极开拓大众文化市场,使作品扩展方向更为广阔的受众。
对于开拓精英文化以外的读者群和文化市场而言,作家的态度是不同的。许多已经确立了经典地位的作家更愿意保持自己的纯文学地位,不愿与大众文化有过多交集。这其中白人男作家最具代表性。长久以来,白人男性代表了美国经典文学,他们无须迎合市场便可保持自己的经典地位。其中典型代表有J.D.塞林格 (J.D Salinger)和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两位男作家过着神秘的隐居生活,但是对名声和聚光灯的远离反而令媒体对他们保持着强烈而持久的兴趣。他们与大众的隔绝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经典作家是不可推销的。但是黑人女作家却不能采用这种低调的策略。对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建立经典地位,但对于在图书市场的商业价值还不突出的黑人女作家而言,则必须通过与大众媒体的合作来达到深化作者身份和扩大市场影响。莫里森以“奥普拉读书会”为平台来进行市场拓展。在与奥普拉的合作中,她的目标受众既不是像学者、批评家一般的精英文化代表,也不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只读小报的阶层”,而是具有一定学识素养的主流读者群。[1](pxii)作者将这一读者群界定为平眉读者群 (middlebrow)。国内有学者把“平眉”译作“小资”或“中产阶级趣味”,是指那些并非真正追求严肃艺术但却喜好附庸风雅的群体。在文化等级中,平眉处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尴尬地带。
捍卫精英文化的先锋派在传统的文化等级中已占据领导地位。根据布尔迪厄对文化场域的论述,掌握了文化资本的个人和单位在文化场域中占领了有利地位,因此获得了合法性。新成员必须通过合法性审核才能够进入这一场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正是文化场域博弈的写照。另外,将精英文化设定为一个封闭的领域,可巩固占领领导地位群体的权威地位,抑制了边缘文化与边缘群体通过非权威机构实现经典化的进程。非洲裔女性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历史并不长,与无须通过大众传媒的助推便自然拥有确定的“作家身份”的白人男作家相比,在公众意识中非洲裔女作家的作者身份并非明确且深入的。且黑人作家要面对詹姆士·威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所说的“一般作家一无所知的特殊问题——双重读者”[2](P247)。因此,在对待平眉,即拥有中产阶级趣味的主流读者的态度上,莫里森采取的是开放的态度。
一
为了克服身份焦虑和双重读者问题,莫里森不得不采取与白人男作家不同的文化市场策略,即打破文化等级,拥抱主流读者。那么这种身份焦虑问题从何而来?通过对黑人女作家在创作和出版界的地位进行一番梳理,便可窥得一二。莫里森在兰登书屋做图书编辑时就已开始逐步进入写作和出版这一白人男性统领的公共领域。她说,编辑生涯“减少了我对出版界的敬畏”[3](P91)。她在兰登书屋工作的18年间发表了三部小说,但她却从来不称自己是作家。她说:“说出‘我是个作家’,在那个年代是一件男性化的事情,我觉得,从心底感觉,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这件成人的事情。我说,‘我是个写作的母亲’或‘我是个写作的编辑’。对我来说,‘作家’一词太难说出口了。”[4](P73)在女性创作的历史中,女作家一直怀有这种把男作家等同于职业作家的看法。即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出版体系,但写作和出版仍被视作男性的文化场域。虽然非洲裔男作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并已确立经典地位,但非洲裔女作家依旧游走在边缘。
在莫里森的事业早期,她认为作者身份是“介入一个你不熟悉的领域——一个你没有任何出处的领域。那时我个人的确不认识一个成功的女作家,这看起来很像是一片男性保留地”[3](P96-97)。莫里森后来成为兰登书屋的高级编辑,她是这家出版社成立以来担任高级编辑一职的第一位非洲裔女性。除了莫里森,直到1986年为止在主要出版社没有其他非洲裔女性担任该职务。[5](P223)当时在诸多非洲裔女作家中,托尼·莫里森也几乎是唯一一位在图书市场有一定销量的作家。她在1981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过这一点:“当我出版托尼·凯德·班巴拉 (Toni Cade Bambara)的作品时,出版盖尔·琼斯(Gayl Jones)的作品时,如果她们能跟我的书一样〔销量好〕,我就会非常开心。但市场只能接受一两个〔黑人女作家〕。要面对五个托尼·莫里森就有问题了。”[5](P133)黑人女作家在面对文学创作和市场接受时的身份焦虑在上述事例中可见一斑。
尽管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黑人文艺复兴”为黑人文学创作尤其是黑人女性文学创作赢得了学术界和出版商短暂的关注,但出版社的理念仍然是把白人读者作为目标受众。在莫里森开始写作的70年代,双重读者仍然是黑人作家在面对受众和市场时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一次采访中,莫里森说:“在我发表了《最蓝的眼睛》之后,人们常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为白人读者写作的吗?’这个问题让我很吃惊。我记得问过克诺夫出版社的一位白人女士:‘白人会说,我知道这本书不是为我写得,但我很喜欢它。当他们这么说时,他们是什么意思?’……这位女士解释道,白人读者还不习惯阅读关于黑人的书,那些中心焦点不是关于白人的书。”[4](P73)莫里森的作品在70年代得以出版只是她进入公共领域的标志。而要解决“双重读者”问题,迈入主流市场,彼时的莫里森尚有一段路要走。
二
虽然图书出版界保持着一贯的对白人作家的青睐,但奥普拉的读书会为莫里森等作家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于1996年9月17日创办“奥普拉读书会”(Oprah’s Book Club)。“奥普拉读书会”每月一期,其做法是先在节目尾声宣布自己选中的书,给观众一个月的时间阅读。接着,数百万观众便会涌向书店购买纸质小说,或在线购买电子版本,等着一个月之后奥普拉读书会的开播。读书会共做过65本小说。每一本读书会选中的书籍都会立即成为畅销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的时间平均为17周。读书会创办头三年,在奥普拉读书会出现过的小说平均销量为140万册。[6](P2)
“奥普拉读书会”的成功在于其本已拥有庞大的观众群。“奥普拉脱口秀”的观众比较多样化,有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也有大学生。根据电视评价权威尼尔森市场调研的调查,奥普拉的观众群的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悬殊。也就是说,她的观众来自美国各阶层人士。[7](P31)在1996年创办“奥普拉读书会”之际,没有人确定它会受欢迎。奥普拉旗下企业哈勃传播公司的总裁蒂姆·班内特担心收视率会在这一环节下滑,但统计数据证明,读书会从一开始就取得了成功。奥普拉读书会奉行的口号是“让美国重新开始读书”。在一期节目接近尾声时,奥普拉大致向观众介绍了节目新增添的环节——读书会。她说:“如今,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阅读一本好书,并且知道在读完这本书之后还有另外一本特别特别棒的书等着我去读。”[8]她宣布一个月之后将与大家一起讨论杰奎琳·米特查德的《海洋深处》。她反复强调,这个故事“对所有母亲来说都是最恐怖的噩梦”[8]。《海洋深处》是一本故事性强、易于阅读的小说。根据时代周刊的统计,此书入选奥普拉读书会三个月后,出版商发行了850万册。10月6日,该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并在榜单上停留了29周。这是一个骄人的成绩。奥普拉读书会的第二个选择是《所罗门之歌》。这部小说于1977年出版,次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Critics’Circle Award),但却从来没有在市场上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与奥普拉读书会第一部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所罗门之歌》引经据典、艺术手法丰富,是一部严肃文学。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奥普拉的推荐下,这本书在问世19年后,也登上了畅销榜。“奥普拉读书会”首先选择一部大众读物,接着转向有深度的经典文学,这并不是偶然,而是该节目的策略。从“奥普拉读书会”之后选择的作品来看,即可归纳出该节目选择作品的模式,即:“先向低眉倾斜(如《海洋深处》),再快速转向高眉(如《所罗门之歌》)。”[6](P39)这种“倾斜”和“转向”便是平眉读者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间的模糊游走。不管“读书会”讨论的作品向哪一端倾斜,平眉读者的讨论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获得乐趣,同时积累文化资本。
在1996年12月首次亮相“奥普拉读书会”之前,莫里森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那时她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美国文学中拥有崇高地位。文学作品在美学价值上取得的成就,从来就不是销量的保障。尽管莫里森的作品一直是有市场的,但却是在与奥普拉携手之后,她的作品才得以畅销。《所罗门之歌》在1996年被奥普拉选中时,距离初版已有19年的时间。奥普拉在节目中宣布下一期读书会的作品是《所罗门之歌》后,出版商加印了98.5万本。随后,这本书进入了畅销榜。莫里森的另外三部作品《天堂》、《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索拉》(Sula)分别于 1998、2000 和 2002 年成为奥普拉读书会的讨论作品,且都因此进入了畅销榜。
借助奥普拉的商业力量,莫里森的作品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文化策略便在于借助“奥普拉读书会”这一平台达到了整合双重读者的目的。奥普拉非常了解自己的观众群主要以中产阶级为主,因此,她的号召和措辞旨在引起这些背景各异、具有一定学识素养、但并非真正懂得严肃艺术这一群体的共鸣。奥普拉脱口秀一期节目为时一个小时。开播初期,读书会仅占一期节目的最后15到20分钟。他们的做法是,首先,制作团队会从读者来信中挑选出内容感人、评论中肯或是生活经历与小说情节相关的4至5位读者,然后这几位读者会获得与奥普拉和作者一同共进晚餐的机会,制作单位再将这个过程录制下来,在节目中播出。晚餐地点一开始设在奥普拉家中,之后转移到一间特意为读书会打造的书房。读书会的场景一直是这个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室内装修豪华,几位女士精心装扮,在摆放精美食物的餐桌上一边品红酒一边对话。
奥普拉是一位出身平凡、成长道路坎坷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奋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媒体帝国。她的经历几乎是“美国梦”的翻版,美国人认同她所传递的价值观,因此博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奥普拉所代表的丰裕的物质生活以及莫里森所代表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是时尚的生活方式,是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在读书会中,观众通过追随与模拟,在心理上达到与奥普拉的亲近,表达对其价值观的认可和生活方式的向往。在读书会中,奥普拉与以托尼·莫里森为代表的群体是两个不同但却完美结合的意象。托尼·莫里森是经典的化身,她的形象满足了观众对精英文化的追随与诉求。奥普拉是商业成功的典范,为观众展示了物质丰裕的优质生活。包德里亚认为,读物扮演着联络符号的角色。在托尼·莫里森与奥普拉这一案例中,文学作品就是联络符号。观众通过参与节目和阅读托尼·莫里森等作家的潜在集体进行着联络。“读者梦想着一个集团,他通过阅读来抽象地完成对它的参与:这是一种不真实的,众多的关系,这本身就是‘大众传播’的效应。”[9](P125)因此,在奥普拉读书会节目中,托尼·莫里森的读者群不再是靠肤色划分的。而是通过媒体的编排,幻化为一种晋升符号,感召着怀有晋升希望的阶级——即后现代的小资文化与大众文化受众。
三
虽然奥普拉脱口秀的主要观众群是白人女性,但“奥普拉读书会”介绍过的65本小说中有10部是非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由此可见,奥普拉在“读书会”这一节目中注入了一定的种族政治性诉求。莫里森以电视节目为渠道,借助奥普拉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在种族与文化杂糅的普通读者群体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以“奥普拉读书会——《最蓝的眼睛》”这期节目为例,便可了解奥普拉的跨种族策略如何帮助莫里森达到整合双重读者的效果。“读书会——《最蓝的眼睛》”一开始,奥普拉就告诉观众,“这是我们进行过的图书讨论中最棒的一次”。接着,她开始呼吁观众:“不管你正在做什么,放下手头的事情,听好了。我尽量不这么要求你们,但如果接下来的20分钟你可以把账单或晚餐放在一边,你将收看到的内容会充满力量,十分美妙——尤其如果你是随便哪种孩子的母亲的话,更是如此。”[8]
面对这样充满煽动性的号召,奥普拉的粉丝怎能抗拒。在事先录制好的片段中,莫里森表示,在她创作《所罗门之歌》的60年代,种族主义是“对孩子的虐待,伤得很深,令人绝望”[8]。以此为背景,读书会前半部分内容便使观众充分理解了白人至上的美国文化如何通过种族主义给非裔美国人造成创伤,尤其是成长在这种文化中的儿童会产生自我厌恶感,这是最具毁灭性的后果。接着,奥普拉说道:“不管你是什么肤色,许多女人都是以别人对她们的看法来审视自己的。”奥普拉呼吁所有种族和文化的女性都应与小说主人公佩科拉产生共鸣。“对我来说,这本书的美妙在于,佩科拉,以及世界上所有像佩科拉一样的人,最终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8]她使用了“我们的生活”,这意味着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分子。我们都像书中那个被虐待、感受不到爱的黑人孩子一样曾被错误的评判体系伤害。奥普拉以其惯常的亲密无间的风格抹去了非洲裔观众/读者和白人观众/读者间的界限。
接着,奥普拉、莫里森和几位客人都分享了自己与佩科拉类似的个人经历。奥普拉回忆起祖母慈爱地抱着一个白人小孩的照片。从照片中奥普拉得出与佩科拉类似的结论,即“如果你是白种人,别人会更爱你”。肤色略深的斯蒂芬妮·古德曼(Stephanie Goodman)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她与大家分享了“纸袋测试”的故事。在新奥尔良,如果黑人想要加入一些精英沙龙,肤色必须比一种棕色纸袋浅才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朱莉·瓦伦丁(Julie Valentine)回忆起曾经参加的教会合唱团都是清一色的黑人,但是她读的私立学校却几乎都是白人。她往返于二者之间,心理上有着微妙的起伏。戴安娜·布里斯(Diana Bliss)告诉大家,她曾参加“天使”一角的试镜但最终被淘汰。工作人员告诉她,虽然她是白人,但却不是金发,因此不能胜任这个角色。罗斯·霍夫曼(Ruth Hoffman)是一位白人女士,她有一位非洲裔养女。她向大家讲述道,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帮助女儿建立起自信,让她相信自己是个美丽的孩子。莫里森认同她的教育理念并告诉大家,以前她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时,总是面露批判的神情。她总是在审视他们是否衣着得当,头发是否干净整洁。后来她做出了改变,变得尽量让儿子们能够感觉到她有多爱他们,并肯定和欣赏他们。[8]
在《最蓝的眼睛》这期节目中,作为知名教授和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莫里森传授的课程虽然与文学本身关联不大,但却具有启发意义。她说道:“你知道了一个人的种族,相当于你什么信息都没有掌握。你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真正的信息在其他方面。”与莫里森之前参加过的“奥普拉读书会”不同,这一洞见并不是教导观众如何阅读小说的,而是教大家如何生活的。同时,莫里森还与大家分享了她对美德和美丽的看法。她说:“在一切美德中,美丽并非其中一员。美德并非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的。美德是你为之奋斗的事物,坦诚、有教养、能自我约束、知书达理、健康、优雅,让你的身体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这些是你可以奋斗得来的品质。”[8]
莫里森、奥普拉和几位女嘉宾以自己的个人经验为出发点,以小说主人公佩科拉为中心,审视了美国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因素。在节目尾声,奥普拉问莫里森,为什么要为主人公设定一个发疯的结局。莫里森没有像前几次参加“奥普拉读书会”时那般拒绝为自己的作品提供明确的解读。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因为没有其他出路。她没有一条出路,所以她就给自己创造了一条出路。那就是疯癫。”[8]
在《最蓝的眼睛》的讨论过程中,奥普拉及其强大的制作团队几乎完整地呈现了读书会最成功的元素。在这期节目中,不仅包含针对社会问题、个人经验、文学洞见等讨论,还展现了莫里森的智慧与正直以及奥普拉的热情和开放。最后奥普拉宣称,如果每个人都读过《最蓝的眼睛》,那么“这个世界将会不同”[8]。
奥普拉把种族主义这一概念扩大到社会偏见、性别偏见的范畴,又将教育、道德等话题加入讨论,通过节目的编排,传递出不论哪个种族的观众和读者都在生活中遭遇此类偏见的信息。她的跨种族策略把观众和读者视为不分肤色的一个整体。莫里森在这一基础上,得以突破文化等级的界限,不仅把受众扩大到平眉读者群,也在克服双重读者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将高端文化形式与具有“中产阶级趣味”的主流读者结合是非裔美国女作家在公共领域确立作者身份的关键步骤。“奥普拉读书会”的现身强化了消费者和读者对莫里森的可见度,驳斥了“作者已死”这一论断。南希·米勒(Nancy Miller)论证道,作者已死这个论断忽视了女性作者身份与男性作者的差异。“毕竟是被载入文选、得到体制化的作者通过他的经典性在场排除了女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不知名的作品,通过他的权威使这一排他行为合理化。”[10](P104)莫里森致力于把自己塑造成在精英文化和流行文化中有所平衡的作家。她曾说道:“我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做到两件事,像我希望的那样深奥、需要人们认真研读,同时像爵士乐一样以感情赢得大众的接受。”[4](P75)通过借助奥普拉的商业力量和大众文化领导力,莫里森做到了这一点。
四
莫里森的文化市场开拓对中国作家以及国内文化产业具有一定启示意义。2012年10月11日,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商业市场对作家得奖的反应十分迅捷。“作家”莫言立刻成为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商品”莫言。作家作品获奖后会增加知名度,读者会竞相购买受到权威文化机构认可的作品。因此,获奖作品对出版社而言意味着巨大利润。根据雅虎财经、人民网、搜狐等多家门户网站的报道,获奖后,莫言的作品在网上和书店中热销,出版社紧急加印,且诺贝尔奖概念股在股市的表现不俗。文学奖项带来的经济效益从中可见一斑。国内的影视市场与文学作品的合作业已成熟。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定会有更多制片商乐于将莫言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
经典文学作家创作的是严肃文学,严肃文学的受众是少数的精英知识分子。如果想要开拓精英文化领域以外的市场,势必要迎合大众文化市场的需要。严肃文学在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或其他形式的文化产品后,会丧失原作中的美学价值和文学性,成为具有娱乐性、商业化的产品。但这种快餐式的文化产品却可以大规模复制,快速传播给广大受众。中国的严肃文学作家如果想要扩大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像莫里森一般积极投身大众文化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1]Joan Shelley Rubin.The Making of Middlebrow Culture.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2]James Weldon Johnson.The Dilemma of the Negro Author.The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of the New Negro Literature.Cary D.Wintz Ed.New York:Garland, 1996.
[3]Elissa Schappel. Toni Morrison:The Act of Fiction CXXXIV.Paris Review128(1993).
[4]Claudia Dreifus.Chloe Wofford Talks About Toni Morrison.New York Times Magazine 9 Sep.1994.
[5]Danille Taylor- Guthrie.ed.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UP of Mississippi, 1994.
[6]Cecilia Konchar Farr.Reading Oprah:How O-prah's Book Club Changed The Way America Read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7]Gayle Feldman.Making Book on Oprah.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 Feb.1997.
[8]“奥普拉读书会”节目字幕(BurrellesLuce Transcripts,Livingston,NJ)和弗吉尼亚大学《奥普拉脱口秀》馆藏 DVD[M/CD].
[9](法)让·包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Nancy K.Miller.Subject to Change:Reading Feminist Writing.New York:Columbia UP,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