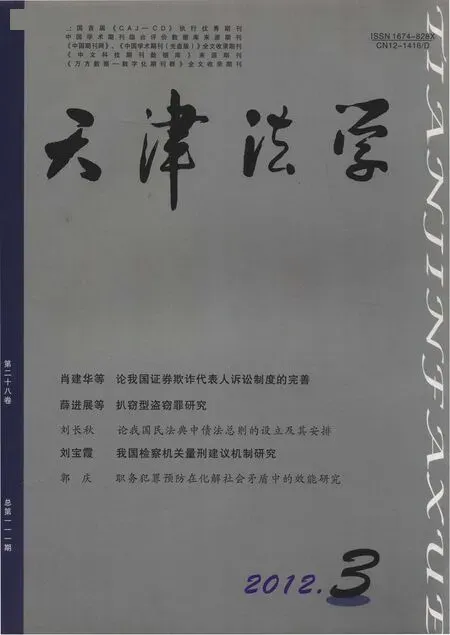扒窃型盗窃罪研究
——以《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为背景
薛进展,蔡正华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100062)
扒窃型盗窃罪研究
——以《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为背景
薛进展,蔡正华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100062)
扒窃型盗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盗窃罪独立定罪类型,也拓宽了扒窃行为入罪的评价路径。刑法上的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扒窃都可以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只有符合“公共场合”、“从他人身上”以及“取得”等标准的扒窃行为才能构成扒窃型盗窃罪。扒窃型盗窃罪作为内涵最为丰富的盗窃罪定罪类型,其外延受到的限制最严格,所以当出现多种类型盗窃罪竞合时,理应首先认定行为是否构成扒窃型盗窃罪。
扒窃型盗窃罪;盗窃罪;定罪类型
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修(八)》),首次将“扒窃”一词引入刑事立法。虽然这一举措丰富了立法层面盗窃罪客观行为的类型,但是也为司法实践中的犯罪认定提出了挑战。一般来讲,扒窃是盗窃行为的一种,但并不是刑法的常规用语,《刑修(八)》实施前其更多的运用在侦查学等学科中。对于扒窃一词直接作为刑事立法用语是否存有法理基础的争论,随着《刑修(八)》的正式颁布趋于结束。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刑法用语,扒窃一词在刑法上的内涵界定工作却才刚刚开始。正确界定盗窃罪项下的扒窃用语内涵,不仅仅是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哪些行为属于扒窃型盗窃犯罪的需要,更是理顺盗窃罪刑事立法体系的需要。
一、“扒窃”概念的辨析
“扒窃”一词首先进入刑事法制领域,可考的是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解释第4条规定,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由于是被用来解释1997年刑法中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多次盗窃”的刑法含义,所以“扒窃”一词本身的含义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而事实上“扒窃”一词属于那种大家不细致考虑感觉都知道其含义,但是深究却不知道如何准确界定的词语。然而成文刑法的一种特点就是都有必要进行解释[1]。由此,准确解释“扒窃”的概念是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根基和前提。当前,对于“扒窃”一词的含义,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扒窃是指“采用割包、掏宝的方式窃取随他人随身携带的财务”的行为[2]。第二种观点认为扒窃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3]。第三种观点认为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不同的掩护方式,采取一定技术手段或者其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公私财物的行为。[4]”
以上几种观点对扒窃的本质含义应当不存在分歧,其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要明确扒窃行为的空间特征、非法占有目的和特殊行为方式。笔者认为,由于特殊行为方式属于外延的范畴,并且解释并不是立法条文的直接表述,所以对于界定特定刑法用语的内涵本身不具备必不可少的现实意义,因此是可有可无的。并且,从语义学角度讲事物内涵和外延的范围成反比,如果我们仅仅以封闭的列举方式解释“扒窃”的含义还可能不当限缩其可能具有的立法含义,也不利于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对其进一步进行解释。所以作为对刑法用语的解释,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学理解释,都不应当越俎代庖式地为“扒窃”的含义划地为牢,而使刑法用语含义本身失去发展可能性。而对于是否有必要在扒窃的概念界定中纳入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持肯定态度: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盗窃罪的概念中包括非法占有之目的,而无论是《刑修(八)》颁布前刑法条文未明列扒窃型盗窃罪,还是如今扒窃型盗窃罪已经明列,其都只属于盗窃罪规制的客观行为,理当也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如果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则只能考虑是否符合其他个罪。
以上关于扒窃概念的几种观点的分歧中,最具有区别扒窃型盗窃罪与其他类型盗窃罪以及罪与非罪意义的当属是否必须具备“公共场所”的空间条件。笔者认为并不需要在扒窃的概念中特别强调公共场所的空间条件,理由主要如下:
第一,“扒窃”一语的语义学含义不包含空间要求。任何刑法用语在刑法上的含义都必须以其本身的语义学含义为基础,这是坚持文理解释在刑法解释中的首要地位的需要,更是遵循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根据较新的《现代汉语词典》,“扒窃”被解释为“从别人身上偷窃财物”[5]。从纯语义的角度看,“偷窃财物”是这一词组的核心,揭示了扒窃的本质属于偷窃,这也是之所以在刑法层面将其纳入盗窃罪规制的原因;“从别人身上”则属于“偷窃财物”的限制性修饰语,属于状语的成分。如果按照前述支持者的观点,扒窃需要限制“公共场所”的空间场合,那么就只能考察“公共场所”和“从别人身上”二者是否具有等同的可能。然而显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二者都是限制“偷窃财物”行为的状语,但却并不都具有表示偷窃的场所的含义:其中“公共场所”表示行窃的空间没有异议,但是“从别人身上”更多的是表示行窃时“财物”的存在位置,二者不能等同。所以,从扒窃的语义学含义角度看,其不需要限制行窃空间场所,而只需要限制财物所在位置。虽然刑法用语的含义与其语义学含义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但是当该用语在语义学上仅仅具有这一种解释时,这一解释对该用语的刑法解释具有提供线索和限制意义的机能,没有特殊理由就应当将该用语在刑法上的含义与语义学解释等同;即便是有特殊理由需要依赖其他解释方法扩大或者限制该刑法用语的含义,也必须遵循该用语语义学上的这一唯一解释,否则就会因超越国民预测之可能,而具有违背罪行法定原则之嫌疑。
第二,本身就存在“在公共场所扒窃”和“在非公共场所扒窃”两种情况。正如前文所述,扒窃一词本身并不当然具有对空间场所的要求,更勿论是特定的“公共场所”。现实生活中事实上既存在在公共场所扒窃,也存在不在公共场所扒窃的情况;前者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扒窃,后者比如在尾随被害人进入办公室从其身上偷走财物。这一观点也为我国的司法解释所坚持,根据前述《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一年内在公共场所扒窃”的认定为“多次盗窃”。根据其“在公共场所扒窃”的用语,表明该解释并未将“公共场所”作为限制扒窃概念的必要条件,而是作为扒窃行为的概念之外的修饰用语。虽然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而行不通。但是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立法原意只有立法者知道,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必然具有现实的妥当性(立法原意存在缺陷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常常是那些没有论据论证自己观点的解释者,才声称自己的解释是立法原意”[6]。事实上立法原意即便存在,也只是影响刑法用语含义的众多因素之一,除此之外,对于刑法用语含义的确定更为关键的应当是刑法的表述、立法的背景、客观的需要等等。所以,笔者并不认为刑法条文确立之后,应当排除刑法条文和客观环境,回溯追究立法原意;更不能就此认为前述司法解释的观点就是违背“扒窃”用语的一般含义范围,因而否认根据司法解释的观点推导出存在“在公共场所扒窃”和“在非公共场所扒窃”的结论也是符合刑法的解释要求的。
第三,承认扒窃概念本身不需要空间场所的限制更能解决当前刑法适用中的困境。《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罪状做了修改之后,就扒窃型盗窃罪而言,司法实践中就面临着这样的疑问:是否所有的扒窃都应入罪?根据当前我国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违法犯罪二元机制的法制现状,答案必然是否定。我国法制的这一特征决定了任何侵害法益的行为都具有入罪的标准,即便是通说的举动犯也存在着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这一出罪路径。那种由于社会危害性未达到一定程度而不具备刑罚可罚性和必要性的法益侵害行为,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但是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扒窃型盗窃行为入罪没有法定的“较大数额”、“多次”或者“携带凶器”等要求,所以我们确定盗窃罪范畴内的扒窃行为和治安处罚法项下的扒窃行为就无法适用此类标准。很多学者因此就折戟而返,认为既然此路不通,我们就回溯探究扒窃行为是否存在刑法和治安处罚法规制的分类。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但是不符合刑法解释学尽量解释的要求,而且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上的消极表现。当我们以一种路径无法解释刑法时,不应当就此放弃,而应当另觅他途。由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要是中国的刑事立法(至少是财产犯罪的立法)并未做好观念性和体系性变革 (变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违法犯罪二机制为刑事制裁一元机制)的准备”[7],那么我们就应当遵循这种法制现状,探寻扒窃型行政违法行为和扒窃型盗窃罪的临界标准。此时,笔者认为在承认扒窃本身具有“在公共场所扒窃”和“在非公共场所扒窃”两种类型就是一种可以尝试的解释路径。承认扒窃行为可以做如此划分,就可以扒窃行为实施的空间场合的差异认定其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还是刑事违法行为,不但符合了当前法制中“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违法犯罪二元机制①”的要求,也因为“不在公共场所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不认为是犯罪,符合了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为此类行为的出罪提供了出口。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扒窃并不需要秘密进行,公然扒取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扒窃型盗窃罪[8]。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因为通说认为秘密性是盗窃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也是区别于抢夺等其他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一大因素,因此扒窃型盗窃犯罪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形式,理所当然应当具有一定程度秘密性要求。
综上,本文认为,“扒窃”这一刑法用语概念的界定,应当在语义学概念的基础上,加上盗窃罪客观要件的必要因素。具体讲,刑法上的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
二、扒窃型盗窃罪的立法地位
扒窃虽然在《刑修(八)》中才首次进入刑法条文,但扒窃行为入罪却并不是《刑修(八)》的发明,作为盗窃方式的一种,扒窃行为符合修正前刑法关于“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等情节时,也理当认定为盗窃罪。《刑修(八)》只是将扒窃在立法条文中独立列出,这种单单列举的意义主要在于:
第一,确立扒窃行为新的入罪路径。根据修正前的刑法第264条第1款的规定,盗窃行为入罪必须符合“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条件。其中对于数额较大标准,无论行为人以何种方式实施盗窃行为,只要达到了该数额标准,都可以适用此标准入罪,作为盗窃之一种的扒窃也不例外。而对于“多次盗窃”的入罪标准,根据《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是指“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情形。扒窃行为根据此入罪标准入罪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者是“在公共场所”;二者是“三次以上”。由此可见,彼时扒窃行为入罪有两种方式:方式一是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时,认定为盗窃罪;方式二是符合“公共场所”的空间条件和“三次以上”的次数条件时,认定为盗窃罪。但是随着《刑修(八)》的颁布实施,扒窃行为的入罪路径就此改变。根据《刑修(八)》第39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此规定为盗窃罪设计了数额较大、多次、入户、携带凶器以及扒窃等五种入罪标准。至此,扒窃行为入罪的路径形成多元化,即独立的“扒窃型盗窃罪”入罪路径和“数额较大”、“多次”等入罪路径。其中,从刑法角度评价扒窃行为时,扒窃型盗窃罪的入罪路径具有优先性,亦即只要行为人一旦实施扒窃行为,并且符合扒窃型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时(此标准内容在下文详细论述),即构成扒窃型盗窃罪。只有在此路径无法将特定扒窃行为认定为盗窃罪时才存在其他入罪路径标准适用的可能,并且其他路径标准适用的结果将导致此扒窃行为不再被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而应当认定为其他对应的盗窃罪类型。
第二,建立新的盗窃罪类型。《刑修(八)》对盗窃罪罪状进行修正后,一般认为是增加了刑法上盗窃罪的种类。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扒窃不是盗窃罪独立的定罪类型,只有携带凶器扒窃才是盗窃罪独立的定罪类型。该学者从有利司法实际操作的层面,试图将前述《刑修(八)》第39条关于盗窃罪罪状的表述解释为“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携带凶器扒窃的”行为[9]。面对其他学者“携带凶器扒窃是‘携带凶器盗窃’这一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它被‘携带凶器盗窃’所包含。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却把它并列地描述在罪状中,显然是一种逻辑混乱的表现[10]”的质疑,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将“携带凶器扒窃”视为法律的注意性规定而非创制性规定,就不存在前述逻辑上的问题。对于此种观点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首先从条文文理角度根本无法解读出只能将“携带凶器扒窃”认定为盗窃罪的含义,这一点前述学者自己也已经意识到。其次,如果非要在扒窃前面加上携带凶器才构成盗窃罪,那么“数额较大的扒窃”、“多次扒窃”等则又成为与“携带凶器扒窃”相并列的扒窃行为入罪的路径标准,而不存在独立的扒窃型盗窃罪类型,导致刑法条文修正过程中单列扒窃的意义荡然无存。当然按照前述学者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认为将“携带凶器扒窃”认定为盗窃罪独立的定罪类型,则其他类型的扒窃行为不再认定为盗窃罪。但此时将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因为不但“携带凶器扒窃”可以为“携带凶器盗窃”所包含,而且仅保留“携带凶器”这一入罪口径,使得刑法修正前扒窃入罪的“数额较大”和“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入罪口径被堵塞,极大地限缩了扒窃行为入罪的可能,这与加大对此类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以利于保护社会法益的通说观点背道而驰。事实上,刑法解释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能超出刑法条文本身可能具有的含义,这是合理解释和错误解释之间的本质区别。《刑修(八)》在盗窃罪罪状中单列扒窃的做法,无论如何解释都应当在尊重将扒窃作为与“数额较大型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以及“携带凶器盗窃”等相并列的盗窃罪类型的基础上进行。而且,正如前文所述,扒窃行为入罪现在虽然存在多种路径,但是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这一路径具有优先性,如果对这一路径加上盗窃罪其他定罪类型下的诸如数额、方式等标准进行限制,则会出现不仅数额较大型盗窃罪要求数额标准,扒窃型盗窃也要求数额标准或者不仅携带凶器型盗窃要求携带凶器,扒窃型盗窃也要求携带凶器的情形,导致扒窃行为入罪口径标准的混乱,从而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的正确适用。
三、扒窃型盗窃罪的司法认定
正确界定了刑法上扒窃的概念只是正确适用刑法的第一步。刑法作为社会控制最后防线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任何刑法用语的真正适用都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界定,比如:刑法分则上的故意杀人行为,如果不经过刑法总则的进一步规范界定,直接运用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则可能会将很多诸如正当防卫、职务行为或者其他社会危害性极低的行为也认定为是故意杀人罪。但事实上经过刑法总则规定的适用和刑法理论对刑法用语在犯罪论层面外延的进一步界定,很多符合刑法分则上故意杀人行为概念的行为,最终都未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扒窃行为作为刑法分则新近创设的用语,其进入司法实践操作之前也必须经历这样的界定过程,进一步规范其内涵和外延,方可以正确适用。
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与刑事处罚的必要性成正比[11],而决定刑事处罚必要性的就是其社会危害性。因此,只要行为人一旦实施扒窃行为,并且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具有刑罚惩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即构成扒窃型盗窃罪②。因此扒窃型盗窃罪的司法认定中最急需的是界定哪些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具有刑罚惩罚的必要性。虽然一般来说犯罪方式方法、时空条件等都可能处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之中,所以进行规范性界定几乎不可能,但是笔者认为针对扒窃型盗窃行为,考察期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具有刑罚惩罚的必要性则可以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
第一,是否在公共场所。虽然笔者赞成扒窃不一定要在公共场所实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空间场所的差异却是体现扒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扒窃概念本身的空间非限制性并不必然导致刑法惩治的扒窃行为就不需要具有空间限制性。事实上,不是在公共场所实行的扒窃行为与一般盗窃或者入户盗窃是相近或者等同的,不具有特殊性,也不构成刑法修正过程中单列扒窃型盗窃罪的理由。而在公共场所实行的扒窃行为,由于其不但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益,而且因为其涉及面广、防不胜防以及可能对被害人人身造成进一步侵害等特点[12],对公民的公共安全感造成了侵害。应当认识到,这种侵害法益的扩大化是修正案单列扒窃型盗窃罪的法理基础之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其他条件一致时,可以认为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扒窃行为构成扒窃型盗窃罪;而在非公共场所实施的扒窃行为要么不构成犯罪,要么构成其他类型的盗窃罪。当然,适用此标准时,对公共场所的界定就成为一问题。有学者为了否定扒窃既可以在公共场所施行、又可以在非公共场所施行的观点,认为“小偷在机关单位的走道、电梯中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也认定为是在公共场所扒窃[13]。笔者认为这种牵强的论述只能徒增司法适用的混乱,而无法明确认定公共场所的统一标准。公共场所是我国刑法中的惯用语,其认定一般坚持地点和人群两大因素[14]。其中公共场所的地点因素是指必须是社会公众共通进行公共活动的地方;而人群因素则是指必须具有人群集聚的事实[15]。只有在采取实质解释的情况下,仍然同时具备了这两种因素,才可以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否则就应当认定为无罪或者其他类型的盗窃罪。
第二,是否从被害人身上窃取。如前文所述,扒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是如何认定随身携带在学术界却一直是争议热点。有观点认为随身携带是指“在从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16]”也有观点认为随身携带应当“仅限于受害人放置在身上的财物,除此之外,随在其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并没有放在身上的物件,不能以此称之。[17]”更有学者从实质解释的角度认为随身携带“意味着一种非常现实、强烈的占有。[18]”这几种观点的分歧关键在于对扒窃的对象财物是否必须在被害人身上。笔者认为从随身携带的字面含义来看,前述采实质解释立场学者的观点正确揭示了随身携带的认定标准,也告诉我们并不是只有拿在手里、放在衣服口袋里或者戴在脖子上才能构成随身携带。那种拎着口袋上公交车,然后将口袋置放在身边座位上的情形也应当认定为随身携带。但是这种“非常现实、强烈的占有”应当具有一个界限,还以公交车上的乘客为例,不能认为坐在长途公交车最前排的乘客在司机要求下,将大件箱包置放在车底专门区域的场合也属于随身携带。事实上我们必须区分携带、乃至运送和随身携带的差别:前两者一般人和物分离,并且人并不能做到每时每刻,只要愿意,都可以伸手触摸到物;而后者却可以满足这一要求。或许这也可以成为认定是否属于随身携带的一般标准,即扒窃的对象财物并不必须在被害人身上,但是却必须是被害人伸手就可以控制的财物。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刑法必然将符合窃取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笔者认为,为了体现犯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为了符合“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违法犯罪二元机制”,在扒窃对象所处的不同空间位置场合,我们仍然需要区分构成犯罪的扒窃行为和一般行政违法型的扒窃行为。而最简单便行的方式就是,将直接从被害人身上窃取财物类型的扒窃行为认定扒窃型盗窃罪;而将窃取被害人伸手可控空间内财物类型的扒窃行为认定为其他类型的盗窃罪或者不认为是犯罪。
第三,是否必须既遂。《刑修(八)》实施后,有观点认为,“扒窃行为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单独成罪的较重的行为类型,立法者重在惩罚扒窃行为而非扒窃数额。因而只要行为人实施扒窃行为,就符合了盗窃罪的既遂条件,不以对财物的控制为必要。[19]”这一观点否定了扒窃行为具有停止形态的可能,认为处于任何阶段的扒窃行为都应当构成扒窃型盗窃罪。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孤立地解读法条的结果,而未能从盗窃罪现有五种定罪类型相互协调的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已经确立起只有在公共场合、直接从他人身上窃取财物的行为才可能构成扒窃型盗窃罪。但是这样的入罪标准是否已经完备?是否已经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所有情形的处理?比如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扒窃行为只处在刚刚着手阶段即被发现,此时是否一概应当直接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这是因为扒窃行为完全可能在处于预备和未遂的阶段时被发现和制止。当然也有观点根据举动犯或者行为犯理论,认为扒窃型盗窃罪一旦实施即构成既遂。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不符合人们对盗窃这一行为必须达到对财物进行必要控制的认识,是一种违背常识的刑法解释,超越了公民对盗窃罪含义的一般认识范围,是不可取的[20]。但是承认了扒窃行为可能在未遂或预备的阶段被迫停止,并不是说刑法就肯定既惩处其既遂形态、又惩处其未遂形态。基于前述确立扒窃型盗窃罪的“在公共场所”和“从他人身上”构成要件同样的理由,笔者认为有必要确定扒窃型盗窃罪只是指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情形(取得财物的多少则不论),行为人未取得财物的扒窃行为也应当认定为不构成犯罪或者构成其他类型的盗窃罪(可以是既遂也可以是未遂)。
综上,扒窃型盗窃罪是指在公共场所,从他人身上窃取并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并且,我们以既遂形态的标准划分盗窃罪的类型,扒窃行为不一定属于扒窃型盗窃罪,只有符合扒窃型盗窃罪既遂标准的扒窃行为才属于扒窃型盗窃罪,其他扒窃行为则要么属于其他类型盗窃罪,要么不构成犯罪。
四、扒窃型盗窃罪与其他类型盗窃罪关系的厘清
盗窃罪独立定罪类型从修正前的两种发展到如今的五种,加大了司法认定准确认定的难度。修正前,“数额较大”一般被认为是盗窃罪最基本的独立定罪类型,而“多次盗窃”则被认为是补充“数额较大”的定罪类型。根据这一思路,当一盗窃行为接受刑法评价时,首先判断其盗窃数额是否已经达到较大的标准,如果达到较大标准则直接定罪。如果达不到较大标准,则并不当然无罪,而是要接受“多次盗窃”路径的筛选,如果虽然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但是符合“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次数标准的,依然应当认定为盗窃罪;如果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也不符合“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次数标准,则就不可能认定为盗窃罪。由此可见,修正前盗窃罪认定存在一种二次评价的工序,有力地保障了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正确认定。但是面对盗窃罪的五种定罪类型,我们是否需要根据传统的认定模式,采取五次评价的方式进行认定?笔者持持怀疑态度。这主要是因为五种定罪类型较之前的两种明显增多,建立五次评价的认定工序实在太繁琐。但是究竟如何实施则又是一宏大的课题,所以笔者仅仅从厘清扒窃型盗窃罪与其他类型盗窃罪的关系的角度就几个具体问题进行阐述:
第一,扒窃型盗窃罪在五种定罪类型中的认定顺序。现行立法对于盗窃罪的定罪类型趋于精细化,导致一行为很可能符合其中数种定罪类型的标准,从而出现同种罪名下不同种类型的竞合现象。对于此种情形的处理,鉴于并不直接影响罪与非罪或者此罪与彼罪的定性,所以一直未有人关注。然而事实上此种竞合的处理规则,虽不涉及罪与非罪以及此最与彼罪的定性区分,但是却关涉到同一罪名项下不同定罪类型关系的处理,并最终限制各定罪类型的具体内涵和外延的实际范围,所以有必要厘清处理规则。由于前文从实质解释的角度,严格限定了扒窃型盗窃罪的内涵,导致了构成此种盗窃罪的外延行为数量范围大大缩小。因此,笔者认为在具体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时,首先应当从是否在公共场所、是否从他人身上扒窃、是否实际取得财物等角度判断该行为是否构成扒窃型盗窃罪;满足上述条件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则不能认定为扒窃型盗窃罪,而应当再依据特定顺序考察是否符合“数量较大”、“多次”、“入户”或者“携带凶器”等类型盗窃罪标准。这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行为类型优先界定的方式势必有利于提高司法适用的效率。
第二,扒窃未遂如何处理。符合条件的扒窃既遂构成扒窃型盗窃罪是刑法条文文义解读的直接结果。但是扒窃未遂的行为如何处理?有观点担心如果扒窃型盗窃罪只惩罚既遂型扒窃,那么对于未遂的扒窃行为则就无法规制。笔者认为此种担忧在如今盗窃罪已经具有五种定罪类型的情况下是极其不必要的,我们排除扒窃未遂构成扒窃型盗窃罪的可能,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认为扒窃未遂就不构成盗窃罪的结论。事实上,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进而具有相当的刑罚惩罚必要性的扒窃未遂行为,我们可以按照盗窃罪其他的定罪类型标准进行规制:比如,根据《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如果扒窃未遂情况下,行为是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扒窃目标的,仍然可以认定为“数额较大”型盗窃罪。再比如,根据《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一年内入户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如果扒窃未遂的情况下,行为人在一年内入户扒窃了三次以上的,则就可以认定为“多次”型盗窃罪。这一适用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对不符合“在公共场所”或“从他人身上”等条件的扒窃行为的处理。
第三,法定刑幅度对应标准的适用。《刑修(八)》第39条为盗窃罪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及“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等三个法定刑幅度,并设置了对应的适用的标准。必须注意的是,修正后的刑法虽然对盗窃罪的定罪类型进行了丰富,但是在这三个法定刑幅度内对应的使用标准仍然以“数额”和“其他情节”为基础。修正前的刑法中,盗窃罪只具有数额和次数两种入罪路径,也就只存在两种路径的量化“数额较大”和“多次”这两种定罪类型(由于修正前刑法中的关于死刑法定刑幅度已取消,所以不再讨论)。彼时的法定刑适用标准和定罪类型的数量是基本对应的,这也是定罪和量刑相衔接的表现。但是修正后的刑法中,盗窃罪具有五种定罪类型,法定刑适用标准却仍然只有两种,此时是否存在适用上的障碍?笔者认为这一现状对于盗窃罪条文适用中的定罪量刑没有障碍,定罪和量刑作为刑法适用的两个阶段,虽然必须保持某种衔接,但不必须在衡量标准上就是一一对应的,定罪情节一定是量刑情节,但是量刑情节却并不一定都是定罪情节[21]。在盗窃罪中,任意法定刑幅度都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盗窃罪类型,这就必然导致与法定刑幅度一一对应的适用标准也必然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盗窃罪类型。总之,虽然修正后的刑法条文在法定刑使适用标准中,保留了盗窃罪以数额犯为主的特征,一方面,数额标准不但可以适用于“数额”型盗窃罪,也可以适用于包括扒窃型盗窃罪在内的其他盗窃罪类型;另一方面,极具包容性的“其他情节”标准,也可以适用于任何种类的盗窃罪情形。
盗窃罪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犯罪类型,这类犯罪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侵害。以全国公安机关2005年至2008年立案数为例,盗窃罪立案数占到所有刑事立案的68.3%[22]。《刑修(八)》对盗窃罪罪状的改变为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有益的契机。但是如何正确适用刑法的规定则直接关系到这一目标能否实现,更关系到刑事法治水平的提升。我们对刑法的解释应当不断深入,而不能机械地从刑法条文文字表面武断地下结论。本文对扒窃型盗窃罪内涵的界定思路,可以延伸到对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扒窃等盗窃罪定罪类型的界定中,并最终实现盗窃罪内部各定罪类型路径和标准的互相衔接,构建打击此类犯罪的严密而又具有可操作性和符合刑法适用原理的刑事法网。
注 释:
①这种二元机制的存在应当解释为一种既存的法制事实,并切实影响着我们的法治实践,拥有了一定的生存土壤。但是,这种现实存在从法理角度讲是否就是合理的,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②有观点认为修正后的刑法中扒窃型盗窃是举动犯,一旦实施扒窃行为即构成盗窃罪。笔者认为,不受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约束的绝对的举动犯是不存在的,任何类型的犯罪都存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这一公共出罪路径。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2。
[2]陈兴良.口授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3。
[3][13][18][19]陈家林.论刑法中的扒窃——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与解读>[J].法律科学,2011,(4):95-101.
[4]贾立岩.浅谈对公交车上扒窃犯罪及法律适用的几点认识[J].今日科苑,2009,(24):179.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014.
[6]张明楷.刑法学研究中的十关系论[J].政法论坛,2006,(3):3-19.
[7]付立庆.让立法远离浪漫主义的迷雾[J].法制日报,2011-3-30(3).
[8]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1.[9]李 翔.新型盗窃罪的司法适用路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113-120.
[10]欧瑶刚.携带凶器扒窃不是盗窃罪独立的定罪情形[DB/OL].正义网:http://www.jcrb.com/jcpd/jcll/201103/t20110325_517885.html,2011-11-26.
[1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5.
[12]吴加明.〈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司法实践认定[J].中国检察官,2011,(7):23-24.
[14]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册)[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1280.
[15]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318.
[16]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20.
[17]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318.
[20]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8.
[21]邱兴隆,许章润.刑罚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273.
[22]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盗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研报告[J].山东审判,2010(5):22-26.
Study on Pick-pocketing Theft——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to the Eighth Criminal Law Amendment asBackground
XUE Jin-zhan,CAI Zheng-hua
(Graduate School,South Ea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100062,China)
The pick-pocketing type Theft is a new type of independent theft in the"eighth Criminal Law Amendment",which at the same time clear the way of incorporating pick-pocketing behavior into crime.Pick-pocketing in the criminal law referred to those behaviors which are for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nd by means of stealing others'property carried with in secret.However not all of pick-pocketing may constitute of pick-pocketing type theft,only those which are conducted in the"public places",from others'body and acquire may meet the definition.Pick-pocketing theft criminal type,who is the richest in connotation,hasalso the strictest restriction in itsepitaxial.So when we meet multiple typesof Theft competing,pick-pocketing type theft shall be considered in the first.
pick-pocketing theft;theft;typesof conviction
DF623
A
1674-828X(2012)03-0005-07
(责任编辑:郭 鹏)
2012-05-17
上海市高水平特色法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5。
薛进展(1956-),男,上海市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刑法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刑法、知识产权犯罪等研究。蔡正华(1985-),男,江苏盐城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刑法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刑法,金融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