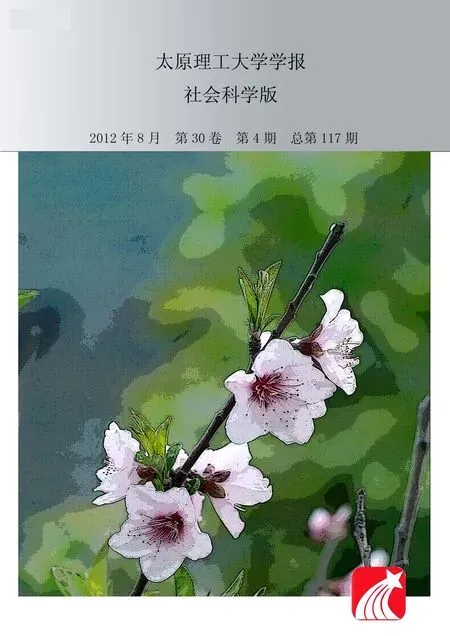论“真”之概念主导下的语言分析之路
——重释弗雷格的“指称”理论
肖福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一、弗雷格的“Bedeutung”与“指称”
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里,他将语言的意义作为了自己的关注的重点。为此,他特别地在德文中选取了“Bedeutung”一词来加以表达。德语的“Bedeutung”是由其动词形式“bedeuten”转变而来,在经过人们的翻译之后,它又成为了英语中的“reference”和“meaning”,成为了汉语中的“意义”和“指称”。不论是“reference”和“meaning”,还是“意义”和“指称”,“reference”不能等同于“meaning”,“意义”也不能等同于“指称”,那么,在同一种语言的介绍中为何会出现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弗雷格的“Bedeutung”呢?其主要原因应该在于语言之间的差异,“Bedeutung”在德语里所表达的并非是一种单独之意,它在使用中有时表达“指称某个对象”,强调语言使用中的行为过程存在,有时又表达“指称的对象”,强调语言使用中有关“物”的存在;这样的表达功能对于德语而言就是一种正确而自然的情况,而且也不会带给德语言说者任何歧义,然而,一旦涉及使用其他语言来表达,如英语和汉语,“Bedeutung”的表达功能就变得有点不一样。如果我们要在英语或汉语中寻找出一个具有类似功能的词,那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也许就不会存在了。在人们要求“单词—单词”或者“概念—概念”的情形下,与“Bedeutung”对应的也应该是一个词、一个概念,其结果就是“Bedeutung”要么对应于“reference”,要么对应于“meaning”,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汉语的翻译表述中,其结果就是“Bedeutung”意义的某种缺失。如果我们强调“指称某个对象”,我们有关于“meaning”或“意义”的选择;如果我们侧重于“指称的对象”,我们则有关于“reference”或“对象”的选择。不管怎样的选择,我们的选择结果都存在着与德文“Bedeutung”之间的意义认同差异。
不管我们在“Bedeutung”的翻译中使用何种形式的表达,“Bedeutung”在弗雷格的眼里既是在“指称”,又是在明示指称的对象。然而,人们却更愿意选择指称的对象或“referents”,这是因为在概念和自然物之间、在内在和外在之间、在心灵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在行为本身和行为对象之间,人们更多地容易接近后者,接近那些感性直观的存在,接近那些作为对象存在的语言意义之源;人们与其说在关注“Bedeutung”的本身之意,不如说在关注“Bedeutung”的指称对象或“referents”之意。当然,这样的选择性趋向也合乎弗雷格在语言哲学研究中所主张的“反洛克观念论”,即,语词的意义不在于洛克式的“观念”里,而在“观念”外的实在世界之中。于是,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在“Bedeutung”之意的选择上所具有的有效性,而且,这样的选择不违背弗雷格的经验实在观。 在弗雷格看来,不论是数学的数字符号,还是语言的文字符号,它们都应该被视为与人们所关注的对象相关联的符号标记;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存在于世界之中,或为自然物的,或为心理现象的,当然,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观必然导致了他对于心理世界对象的拒斥,也必然地导致了他对洛克的“语词—观念”论的完全改造。一旦关于语词意义的“洛克论”转变为“弗雷格论”,语词的意义之源就从心灵的主观世界转向了心灵之外的自然世界,结果,语词意义的指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洛克的语词意义指向观念,弗雷格的语词意义指向事物。为此,“观念”与“事物”的分野决定了语词意义产生源泉的截然差异。
二、数学思维的表达形式与弗雷格的语言分析
“Bedeutung”在联系到“指称”之意,且指称个体对象时,指称的语词在弗雷格看来就是一种单称词;单称词在对应个体对象的存在方面非常直观明确,它从一个语言世界的最基本的意义表达单位指向了一个非语言世界的基本个体对象,当然,这样的非语言的个体存在世界在弗雷格那里只能是经验实在的。同单称词指称个体对象的情形比起来,含有单称词的句子或谓词在其指称的对象方面就会显得复杂得多,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句子和谓词不能像单称词那样具有确定的外在个体对象,语言句子或使用的谓词不仅要涉及关于世界的对象存在,更要涉及关于世界的关系存在,以及关于“对象”与“关系”之如此形成的原因存在,等等。在单称词与句子或谓词的关系上,弗雷格的句子表现为单称词对于谓词的填充,谓词表现为关于单称词的叙说和描述。认识弗雷格的句子,我们还得面对他的谓词指称。根据弗雷格的语言逻辑思想,如果要确立谓词的指称对象,我们就要凭借一种“形式”,一种可以将单称词和谓词结合成句子,并带来关于句子之“真”与“假”的“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什么呢?弗雷格认为,语言表达中的这种“形式”同数学中的“函数形式”可以进行类比,它可被视为一种“函数”。在“函数”的概念下,我们所拥有的就是一种关于语言世界的数学视角。结果,语言的句子真值,以及专名与谓词的关系就被转变成了一种数学中的函数关系,由此,语言句子的传统主谓结构认识或“S(不)是P”的判定形式就被弗雷格改造成了一种函数式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数学改造,关于语言逻辑或现代逻辑的研究才真正地获得了走向“形式化”的起点。
作为一位数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弗雷格推崇形式化的符号语言。在弗雷格看来,自然语言在其语形和语义逻辑上存在种种缺陷,要想克服这些缺陷,自然语言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造,将自然语言所涉及的真值问题通过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表现出来,它就是数学的方法,一种使用函数的表达方法。在数学的函数F(x)里,只要自变量存在或出现,函数就会出现一个对应的值域,具体而言,一旦我们确定了一个自变量,函数就有一个值;对于函数表达式x+2而言,只要我们将2放入x的位置,我们就能够获得一种关于数字4的说明,一种关于4的由来过程的说明。所以,从数学的意义上看,如果说弗雷格的谓词属于某个符号形式,那这样的符号形式就相当于上面所提及的函数(表达式);这样的函数既是关于自变量的函数,又是关于值的函数,它总是表现为一个开始于自变量的确定到其拥有真值的过程。当然,弗雷格关于谓词的数学联想不仅仅是要借用数学的形式符号,他这样做的目的还在于将函数表达式或谓词指称视为概念,即,谓词(函数)对应于我们所说的概念存在,因此,在弗雷格看来,谓词又可称为概念词。不可否认,概念词属于语言符号层面的对象,弗雷格进一步要求区分概念和概念词,概念词是标示概念的语言表达式,概念本身属于客观的东西,不是语言符号的组成部分,更不是属于索绪尔所指的那种心理活动或内心的观念。只有关于概念的理解过程才属于心理活动范畴。“概念词的意谓是概念,因此无论它出现在句子中主词还是谓词的位置上……”[1]
在关于谓词的指称或意义问题上,弗雷格通过赋予谓词空位以对象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对于任何一个函数或谓词而言,它的值(真和假)的取得必须依靠自变量的确定或指称对象的确定,于是,这种谓词意义的取得方式就一定要建立在谓词自身的“空位”被指称对象填充的基础之上。如果转换到句子的情形,那就是句子的部分决定着句子的意义存在,那么,这样的情形应该说违背了弗雷格自己所提出的“语境原则”而更多地接近了他的“合成性原则”(关于“二原则”的分析,下文将进行专门的讨论)。
三、谓词与概念词下的指称对象情形
在弗雷格的谓词—函数论中,他在关注谓词意义时,也在关注单称词(或自变量)。不论是相当于函数的谓词,还是相当于自变量的单称词,它们都是作为语言表达形式的存在。单称词与谓词形式具有不同的指称对象,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世界应该具有不同层次,以及具有不同的特征。弗雷格认为,单称词指称“对象”(物),而且,这样的单称词总是体现为完全的、饱和的存在状态,仅仅依靠它自身的存在或出现,它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就是确定无疑的;相对于单称词的对象指称,弗雷格的谓词指称(王路称之为“谓词的意谓”[1]112)概念,这样的谓词或概念是不完整的和不饱和的,“概念是不完整的,需要对象来补充”[1]125。于是,在单称词与谓词之间,在饱和与不饱和之间,从数学到(语言)逻辑的对应关系就有一个清楚的展开:弗雷格使用了数学中的函数同逻辑中的概念进行了类比,从而将单称词的对象与谓词的概念进行区别,并取代了传统逻辑中主词与谓词的划分,结果,单称词与对象(物)相对应、谓词或函数与概念相对应。由于数学的函数本身不指称任何确定的数,只有以确定的自变量代入函数时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否则,它是不完整的和不饱和的;谓词表达的概念也具有函数的这种性质,所以,它也是不完整的和不饱和的。谓词在弗雷格那里有两种称谓,他有时使用谓词称之,有时使用概念词称之。一方面,他在分析谓词的时候,认为概念的功能就相当于谓词的作用,“谓词的指称对象就是概念”[2],于是,概念词与谓词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分析概念词的时候,他又称概念词的指称对象是概念;于是,在弗雷格看来,谓词与概念词的称谓属于具有同一指称对象的表达形式。关于谓词或概念词的指称情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句子的分析来加以说明:在句子“地球是行星”中,我们可以将句子分析为“地球”和“x是行星”两部分,“地球”是个单称词(专名),它所指称的是一个对象,而“x是行星”是一个谓词,它所指称的是“行星”这个概念。根据弗雷格的观点,“x是行星”相当于一个函数,它以地球作其自变元,并得到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具有完整的、饱和的意义,它具有“真值”而且为“真”。此外,依据单称词(专名)占位的多少,我们可以对谓词加以分类,使得谓词也有“一元”到“多元”谓词之分。如果把谓词视为函数,我们就有F(x)、F(x,y)等形式,这样的形式“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简单命题的内部结构”,从而“脱离”传统语法结构的制约[3]。
在我们如此遵循弗雷格的谓词指称理论的时候,总是会意识到谓词的存在要指称某个对象(概念),而这样的对象似乎又要具备它的特殊之处,似乎又要使我们回避关于对象的单称词定义常识。弗雷格提出过这样一个例子,其目的就是要说明概念“马”,如果我们要把概念“马”看成是谓词的指称,那指称这个概念的谓词就是“x是马”或者“( )是马”。在此,概念“马”不同于个体对象存在的“马”,它只是一种可以理解为谓词形式的存在,具有一种不完全、不饱和的特征,而作为个体对象的“马”则相当于单称词的指称对象,只有当个体对象的“马”对概念的“马”进行描述时,概念的“马”才会变得有意义、有真值。在这里,对象和概念到底有什么差异呢?“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概念之间所有关系都可以划归为这种关系”[4]。显然,概念只要得到了个体对象的补充,概念才会变得完整,才会具有真或假,所以,概念的“马”与个体对象的“马”之间的关系同样对应于弗雷格的“函数与自变量”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概念的“马”进行特指(变为限定性摹状词),使其成为“这种概念的马”或“那种概念的马”,那它就相当于一个专名的存在了,那它一定有自己的指称对象,它同样要区别于作为概念的存在。总之,“(单称词的)对象与概念是不同的”[1]116。
弗雷格不仅在讨论谓词时提到了指称对象,而且在讨论句子时也提到了指称对象。那么,在弗雷格眼里的句子指称又是什么呢?句子的指称(对象)当然也不会是单称词所指称的那种对象,根据弗雷格的逻辑理论,他在句子的指称方面所思考的对象就是句子的真值,即句子意义的真或假。“弗雷格的逻辑理论是一阶谓词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典型的外延的和二值的,因此他对句子的说明必然带有这种理论的特征。”[1]117
四、作为“原则”的分析和句子的指称
弗雷格将真和假看成了句子指称的对象,而且,真与假同句子的意义展示联系在一起。要获取弗雷格的这种真值与意义的联系,我们还得回到“Bedeutung”的理解上去。如果我们在考虑弗雷格的“语境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指称理论时理解“Bedeutung”,“Bedeutung”自然就要涉及语词和句子的意义,涉及指称之意,涉及语词意义决定于句子语境之意,等等,唯有如此,我们对于“语境原则”、“合成性原则”等的理解才会更接近弗雷格之意,我们所遵循的标准才会是“Bedeutung”本意。尽管我们在表达弗雷格思想时不可能同时使用两个或三个语词的表述来理解“指称”,但我们所言说的弗雷格“指称”应该是“Bedeutung”意义上的指称,它的外延和内涵之意应该合乎于弗雷格式的“指称”要求。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是作为其语言哲学思想形成的基本概念之一而存在的,因此,回到弗雷格的“指称”本意上,我们就会取得一种正确理解弗雷格语言分析理论的方法,如对“语境原则”和“合成性原则”的分析与理解。
“语境原则,即要结合句子语境来确定词的意义。”[5]因为弗雷格在“语境原则”里主张:永远不要去询问一个孤立语词的指称意义,语词的指称意义只能存在于句子这一语境之中[6]。换言之,只有句子语境的存在才能最终决定语词的指称意义是什么,语词的语境缺失就是语词指称意义的缺失。而在“合成性原则”,他主张:就句子的指称意义而言,它由语词的指称意义所决定,句子构成于语词及其语词的排列方式。弗雷格的“合成性原则”主张刚好走向了“语境原则”的对立面。在“二原则”的对立出现时,它并非要表明弗雷格在同一问题上的“既是又不是”的回答,“二原则”是基于不同问题(对象)的不同结果。具体而言,“语境原则”依据世界中的“事实”(意义存在的基本单位),对应于最小语言单位来说,它就是句子;而“合成性原则”只是就语言意义存在的自身系统而言,它不仅对应“事实”的意义,而且关注句子自身构成部分的意义规定。
在“语境原则”上,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指称”一文中指出,单称词具备自己的指称对象非常重要,可是,这样的指称对象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于单称词的个体存在,单称词指称对象的重要性只是在我们所使用句子为真或为假的时候才被赋予,所以,不管如何强调单称词指称对象的意义或重要性,句子是否具有真值的“指称”在这里始终是一个前提。同时,在“语境原则”之外,弗雷格也使用“合成性原则”来思考语词意义和句子意义的关系。根据“合成性原则”,如果我们使用指称意义相同的语词来替换句子中的原有语词,句子的指称意义保持不变。比如,“《概念文字》的作者”和“弗雷格”的指称意义相同,于是,对它们进行互换,我们就可以从句子“弗雷格是语言哲学家”得到另一个句子“《概念文字》的作者是语言哲学家”,句子指称的真值没有发生变化。可以说,在“合成性原则”里,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句子指称真值”的结果。不论是在“语境原则”下的句子指称情形,还是在“合成性原则”下的句子指称情形,真值成为了它们共同的指称对象,只不过“语境原则”强调的句子真值指称以“事实”得以表现的基本对象为依据。
当然,弗雷格所言的句子指称真值并非要终结句子指称的其他可能性。如果我们扩展弗雷格的指称理论,句子的指称就会具有某些非真值对象的表达,如:把句子所对应的事件或事实存在看作句子的指称,句子的指称就是作为世界中的“事实”对象,这样的情形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被特别地加以了说明,“语言与世界相对应,句子与事实相对应,句子之间的关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相对应”[1]155。结果,弗雷格的“句子—真值”对应就被转换成了“句子—事实”的对应。在我们拥有这样的转换结果时,我们会在一种字面意义上认定两者的不同,即认为弗雷格的句子指称对象不同于转换后的指称对象;其实,在两个“对应”里,它们的联系不可截然地分开,对于第一个“对应”的理解不能拒斥第二个“对应”的存在。一方面,在弗雷格的“句子—真值”里,我们面对的指称对象是真值,表面上看起来,真值似乎远不是“事实”的东西或“物”的对象,但这样的真值在弗雷格眼里并非某种主观臆想的对象,弗雷格的语义逻辑之真在原初的意义上应该属于世界之真、事实之真,即逻辑之真的必然性源自于它描述了事实的存在状态或事实的总汇,当然,它也要描述与客观实在相关的一类某些的非经验的事实(这里的“非经验事实”不同于理性存在的纯粹先验形式存在[7])。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实在论者,弗雷格相信概念、关系、对象,以及真值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在他看来,我们对于“真”或“事实”的认识只能是一种不创造被认识的事物而只是把握存在着的事物的活动。在这样的认识里,“事实”所表明的就是关于物质对象的存在,同时也包括抽象对象的存在;当我们在使用语言或语言的句子来描述了这样的“事实”时,我们也是在面对或指称语言或句子本身的真值存在,真与“事实”总是要保持联系而存在。另一方面,句子指称真值与句子指称事实的联系在弗雷格那里还可以具体到句子的构成成分来加以分析。弗雷格的句子真值总是不能缺少单称词(专名)和谓词的存在获取,特别是单称词对于谓词的填充,只有在句子的谓词被加以了填充饱和之时,句子才由此成为真正的句子,成为具有真值指称的句子,而那种使谓词变得完整和饱和的单称词则一定要指称事物或事态的存在;对于事物或事态的指称所必然联系的就是关于事实的存在,任何想要将单称词的指称对象同世界中的事实分离开来的想法都会是徒劳的,事实的存在一旦没有了事物对象的存在,事实本身是什么的问题就会变得无从谈起,所以,即使从填充谓词的单称词来看,句子的真值指称与句子的“事实”指称都是密切相关的。
总之,在今天的语言哲学研究领域,我们对于“指称”概念是如此的熟悉,以至于它本身都成为了一个常用的专名,但这样的专名应该作为弗雷格本意的“专名”而非语言词典上的专名而存在。遵循弗雷格本意的“专名”,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分析便会代之以现代分析哲学的方法,关于语言意义及其逻辑结构的分析就不再是应用自然语言所进行的过程。“指称”同弗雷格的“涵义”、“谓词”等概念一起建构了语言分析哲学的全新之路。重释弗雷格的“指称”理论就是重回弗雷格语言哲学思想,辨明语言形式化研究的函数逻辑道路,从而获取关于语义逻辑的数学源泉,并消除关于语义逻辑研究的繁琐。重释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思想就是分析他在洛克“语词-观念”论上的完全转向,就是再现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实在论”基础,所以,“指称”理论在弗雷格那里也表明了一种转变,一种从观念世界到“事实”世界的转变。在“指称”理论的意义构建里,语词和句子,以及句子之上的更大语言单位都脱离不了与世界“实在”的联系,世界的“实在”最终确立了关于语言之真值获取的标准与源泉,当然,弗雷格关于“真”的问题只是在句子的层面上展开。
参考文献:
[1] 王 路.逻辑与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25.
[2] 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王 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77.
[3] 王 路.逻辑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6.
[4] Frege,G..Nachgelassene Schriften[M].hg.Von Hermes,H.,kambartel,F.,Kaulbach,F..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1969:128.
[5] 弗雷格.算术基础[M].王 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前言.
[6] Frege G..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M].trans.Austin,J.L..Oxford:Blackwell,1980:X.
[7] 肖福平.理性主体的地位特征与语言存在形式的确立[J].广西社会科学,2011(10):121-125.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