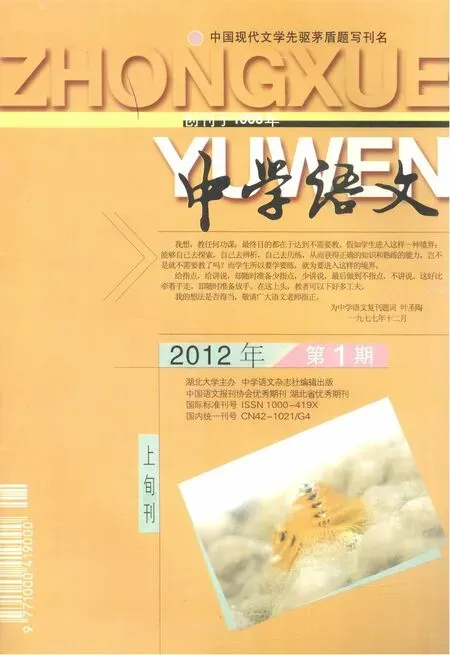多种形式点活诗词鉴赏课堂
董 霞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的诗词就是中国的文化,辉煌的唐宋诗词不仅是华夏民族美育和文学教育的经典材料,也是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①因此,课改之后的高中语文课程建设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典诗歌鉴赏作为一门选修课来开设;而许多求知若渴的中学生在众多选修课中,也把古典诗歌鉴赏作为首选科目之一。但是,再美的东西看多了也会出现审美疲劳,再精粹的诗歌连续学上一段时间,恐怕学生也会厌倦。所以,作为老师,就要努力创造多种形式,点活诗词鉴赏的课堂。
笔者所在的学校用的是语文版教材,语文版教材的古典诗歌鉴赏是单独的一本书——《唐宋诗词鉴赏》,由12课组成,其中唐宋诗7课、唐宋词5课,每课安排3首诗或词;每课后的“扩展阅读”又提供4首诗或词,这样下来,一共有诗歌87首,倘若加上课后练习、课文相关链接以及每课后的鉴赏知识里的诗歌,数量之巨、内容之繁、必然会使学生由爱生厌。因此,我在备课时特别注意创造课堂新形式,以下是我运用过并且效果显著的几种形式。
一、比较阅读形式
这是一种为人们所熟知的方法,在高考题中也早已采用,在课堂教学中,它也是非常奏效的。比如我在讲授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时,就与扩展阅读中岑参的另一首写于同时期、反映同一主题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进行比较阅读。为了教给学生这个方法,我限定了比较的角度,即从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进行比较,形式主要表现为诗歌的写作手法,不仅要比较不同处,还要比较相同处。
二、辩论赛的形式
辩论赛这个形式最适用于辨析诗歌中的字。把曾经有争议的字作为辩论赛的辩题预先告诉学生,给他们留出时间去查阅资料或者动脑筋思考,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辩论。在激烈的辩论中,学生的思维得到训炼,同时,某一字在某句诗中优劣好坏、恰当与否也就自然分明了。比如,我在讲授贾岛的《题李凝幽居》时,就以“僧敲月下门”中的“推敲”作为辩题开了场辩论赛。学生积极准备,赛场上气氛热烈。推敲的优劣辩明了,还意外地收获了更广阔的思路:有学生提出能不能用“叩”字,于是辩论赛的辩题发生变化,大家又开始辩论“叩”与“敲”的优劣。
三、改写诗歌的形式
选入教材的诗歌既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这就为改写诗歌提供了条件。抒情诗歌可以改写为抒情散文,叙事诗则可以改写为剧本或是小说。学生在改写过程中加深了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和对诗中情感的体会。比如《先向歌诗求讽刺——社会写真》这一课中《石壕吏》《卖炭翁》两首,原本是初中教材上的内容,虽然我的学生初中时用的是苏教版教材,没有学过这两首诗,但是诗歌内容本身不是难点。所以,我在不需讲解的情况下直接要求学生把它改写成剧本形式。
在改写剧本的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就发现 《石壕吏》这首诗歌按照时空的变化分为三个场次——老妇前致词、夜久泣幽咽和天明别老翁。其中以第一个场次戏份最多,出场人物最多,矛盾最为集中。原诗中的老妇致词在剧本中要通过对话才能表现出来,石壕吏的台词根据老妇的致词得以推测出来。在改写过程中,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加入了石壕吏的动作、表情等舞台说明,使得诗歌主旨更加显而易见。通过这次成功的改写,《石壕吏》一诗的艺术特色——寓褒贬于叙事、藏问于答,我只作简单点拨,学生就理解了。
四、朗诵说明形式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②张志公先生也说过:一篇文章,读出声音来,读出抑扬顿挫来,读出语调神情来,比单用眼睛看,所得的印象要深刻得多,对于文章的思想感情,领会得要透彻得多,从中受到的感染要强得多。诗歌本就是声音的文学,朗诵在诗歌学习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诗歌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朗诵的形式来教授诗歌。所以我运用朗诵说明的形式来学习诗歌。什么是朗诵说明形式?就是在朗诵的基础上加以说明,说明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首诗来朗诵,说明自己对这首诗的认识与理解。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一个读者大概就只有一个哈姆雷特了,所以仅仅是个人朗诵获取的感受认知是有限的,课堂上大家在一起就可以分享许多人的不同感受,众人的感受加在一起肯定比老师单纯的讲授要丰富得多。
综上所述,在诗歌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很多形式来点活课堂,避免因老师一个人讲述或是连续性的诗歌学习而带来的厌倦和懈怠。当然在运用各种形式时,教师并不是就可以袖手旁观了,什么诗歌适合采用什么形式,是必须要经过认真分析的。如果不加考虑草草运用,反倒会事倍功半,所以教师的备课仍然非常重要。其次,课堂上老师要适时点拨,随时引导,要因情况而制宜,决不能一劳永逸。我相信,只要教师用心,必然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领略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韵味。
注释:
①史习江:《语文版高中课标语文选修教材说道》,《语文建设》,2006年第9期。
②唐·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卷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