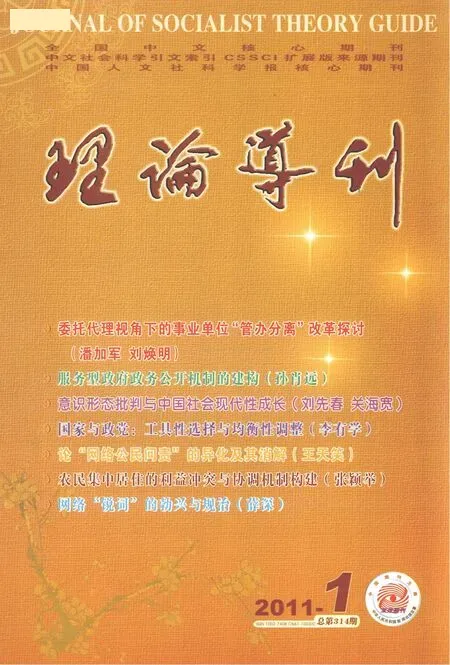刍论“网络时代”的阅读革命
宋新军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刍论“网络时代”的阅读革命
宋新军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当下已进入以“网络”为标志的“泛阅读”时代,电子阅读有迅速超过纸媒阅读之势。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人惊呼“文学的死亡”,这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电子阅读因种种原因,还难以取代纸媒阅读;电子阅读虽然可以造成文学的边缘化,但是,文学精神赋予人们的深阅读、深思考,毕竟成为人类超越“物化”社会的最后慰安。
网络;信息辨证;深阅读
在数字化时代,坐在传统的纸媒图书馆已经不再是阅读的唯一方式,点击网络、手机、阅读器都可以成为阅读的媒介。去年11月,美国最大的网络书店亚马逊推出第一代“电子书”,这是一个薄板似的电子装置,重量不到300克,可以下载数千本书籍。今年初,亚马逊又推出第二代电子书,这种比笔记本电脑轻、比手机屏幕大的新终端还在继续改进、出新,容量大、操作简化,使用方便,成为阅读器工艺改进的必然趋势。那么,在以“网络”为标志的“泛阅读”时代,我们如何看待现代阅读方式与传统阅读方式的冲突?如何才能在信息“嘈杂”的纷繁中保持平静的阅读心境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略作探讨。
一、网瘾与阅读的泛化
“我扑在书籍上,就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这句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言,描述在纸媒传播时代人们对于图书的亲密关系,如今已经转化为人们对于电子信息的迷恋;沉溺于电子阅读的“网虫儿”有日益增多之势。下面是周洁茹在《小妖的网》里描述的一个网络写手的自白:“我是一个狂热的电子邮件爱好者,我每天都要按五十次以上的接收键,即使我知道,它会自动接收,我还是要按。我渴望从中得到信息,每时每刻源源不断的信息。每次我旅行在外,而且没有带电脑,我就会睡不着,我念念不忘我的电子信箱,我会到处找网吧,如果那个城市连网吧也没有,我就会连夜赶回家。我认为我已经患了一种轻度的精神病,与网络有关。”[1]现在,已有数据证明,电子阅读已经超过了图书阅读。
而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的是,当下国民的总体阅读兴趣和阅读质量的趋低。根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2008年国民个人阅读评价是:很不满意为11.%,不太满意为50.%,比较满意为35.70%,非常满意为2.9%,总体呈“不太满意”趋势。而从阅读数量来看,阅读数量很少为35.6%,比较少为29.5%,一般为27.4%,比较多为6%,很多为1.4%,总体呈比较少趋势。[2]如果再具体分析,纸媒信息的阅读数量排行:报刊仍属第一位,图书次之。图书的阅读数量排行:消遣娱乐类为第一位,专业教学类为第二,经典审美类为第三。有趣的是,把书拿颠倒而搞笑的、只喜爱棒球、喜爱在农庄清马粪的美国前任总统布什,在任的2006年读了95本,2007年为51本,2008年也有40本。[3]以我国国民的每年平均阅读量和外国相比,更能看出期间的差距。据调查,中国国民年平均阅读量为0.7本,日本为4本,韩国为7本,法国11本。中国人有“读书习惯”的,从几年前的7%,降到2004年的5%;而英国有“读书习惯”的人,从1977年的54%,升到2002年65%。联合国在企业家中做读书调查,日本企业家一年读书50本,中国企业家一年读书半本,相差0倍。据美国N E A(全国教育协会)调查,美国人中有“读书习惯”的,全国平均为38%,而南美裔民中只有26.5%。而且有读书习惯的阶层,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参加体育运动的比例超出没有读书习惯的阶层两三倍。企鹅出版公司研究部调查了2000位女性,其中85%认为,聊天闲谈或正儿八经谈情说爱的男人,如果大谈读过的书,便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让他们“感到爱慕”。[4]可见,爱好读书,是网络时代中现代人的一种文明与高雅的表现;也说明纸媒图书阅读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只是一个过渡,而绝非总趋势。可以预测,在相当长的历史空间,纸媒图书仍有着坚挺的生命力。
然而,还不仅仅是所谓的纸媒图书与电子图书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另一种对于传统阅读方式来说更为严峻的威胁是:由于广泛而普及的视频图像信息的侵入,造成“很多人不仅纸本书不读,电子书也少有问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和网络上的各种类型的视频图像,加快了阅读的“泛化”,也称其为“快餐化”或“娱乐化”。这将使人们对报刊、对图书的阅读兴趣大大降低,“也将导致思维简单化、平面化,思考能力和创新、质疑能力减退;对网络信息传播缺乏辨别和处理能力,极易受暴力和色情信息的危害;有些孩子沉溺电子阅读和虚拟世界,从心理上排斥现实生活。虚拟和现实角色错位。长期如此容易形成心理疾病。”[5]这些“极端”,并非危言耸听。通过网络交流,人与人之间不仅没有变得亲密无间,反而更疏离了;人的情感来得多、快、急,反而显得轻泛,淡化并销蚀了人的最可贵的情感的保真度。稀释的情感,当然少不了包装与“炒作”。这样就使得网上阅读,也成了虚拟性的技术操作。有的学者提出在传播媒介历程中的基本矛盾,即传播的“自由度”,与“保真度”的双螺旋悖论。当然,这里所谓的“真”,不仅指信息本体之真,也指阅读信息过程的情感之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数据:当前55%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大学生则少于小时;结果造成这样的状况,1/3的年轻人(18-24岁)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52%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陈赛《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读者文摘》2009年22期)。这是由阅读信息的单向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是“量”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质”的规定。即对于阅读对象在质的选择上发生了一场悄悄的革命。
当代人的实用功利观,因被技术理性所操纵,显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突出。因而,往往最被大家趋鹜的“热点”,反而容易留下最容易被忽略的真空死角和“空白点”。这里面问题多多,但有一点是最为核心的,即你付出的时间,与你得到的信息,是否成比例?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矛盾就是:网络上信息的系统性、连贯性,与你阅读的非系统性、非连贯性恰好成反比。易言之,你上网的时间越长,获得的信息也就越多,同时也就越杂,是最典型的“杂多”。然而,“杂多”的信息是以“量”取胜,而不以“质”取胜。这样一来,你的阅读对象便以“断篇”的形式出现;“断篇”的文章很难构成思想的深度,所以被马尔库赛称为的“单面人”,也就出现了。
二、文学观念的危机
有人惊叹,当下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西方的文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的影响”。而一些解构主义理论家则把问题推向极致,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美国的希利斯·米勒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说:“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会长吉奥·伊亚则将这一巨变归咎于电子媒体的崛起。他指出:“我们看到了一种巨大的文化消费的转移潮流:美国人正从平面媒体,转向沉迷于电子媒体。”希利斯·米勒的一本专著,题目就叫《文学死了吗?》。书的一开始就说:“文学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但他接着又说:“文学虽然末日降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6]
以上对于当代文学的悲观心理,既体现了对世界范围内文学现状的忧虑,也预知文学不可能死亡的矛盾心理,这与“网络时代”的文学“泛化”有一定关系。文学走向边缘,传统的文学观,包括创作与阅读过程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权以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为例。所谓艺术构思,“就是作家在材料积累和艺术发现的基础上,在某种创作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回忆、想象、情感等心理活动,以各种艺术构思的方式,孕育出完整的呼之欲出的形象系列和中心意念的艺术思维过程。”[7]132比如叙事性作品中的体裁的选定、形象的熔铸、情节的提炼与安排、结构的设计与剪裁、表现角度的选择与切入、意念的渗透,以及情景交融、意境重现、节奏张弛、音韵协调等要素,都需要进行细密的艺术构思。在紧张而复杂的艺术构思中,从生活里蜂拥而来的一切刺激、信息都在此过程中不断融合、碰撞、解体又重新聚合,以往零碎得来的感受都在此受到检验、连缀、整合和升华。“千万个念头刚冒出来又倏而逝去,紧接着又涌来千万个新的想法。作家的大脑像风车一般旋转,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作家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也许毫无收获;但在绝望中刚一撒手,也许那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又突然浮现出来。这既是‘思接千载’的时刻,也是综合创造的良机。”[7]133这种紧张、复杂而细微的艺术构思过程,在面对键盘敲击的同时,因字码重组所带来的某种障碍,将会使构思的活力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衰减,使艺术构思过程不能够畅然进行。然而,根据近年来一些成功作家在网上写作的例子看来,面对显示屏而敲击键盘,并不会从实质上影响写作的正常运行。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说明全部。我们所说的“网络文学”,是在网上原创并利用“因特网”而在网民间大面积传播的文学,并不是指以电脑为工具,用敲击字符来进行电脑写作的文学。因为这类文学,最终是以纸媒出版为目的的,即使进行了部分或全部的电媒传播,也是实现某种运作目的的权宜之计。所以,纸媒出版的文本,已经成为网络文学的二度提升,不属于纯粹的网络文学的范畴。这样一来,网络文学就是不以通过“守门人”的编辑过程、不以纸媒样式出版为目的的网上的原创作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原创”的网络思维与以纸媒传播为目的的艺术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艺术构思在网上的原创活动中,就显得无足轻重;网民个体的随意性和自由精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一整套的艺术规范;在他们那里,艺术的真髓除了“虚构”之外,便一无所有。这样,从“大文学观”的视野放眼,“网络文学”处在“文学”与“文章”的边缘,与其用“文学”的视角,不如用“文章”的视角去阅读它、鉴赏它。
近年来,移动通信的普及几乎与计算机平分秋色。从原理来讲,它也是一种计算机,只需通过网络的方式,将接口终端与信息源连接,便可以运用自如地同样施行计算机的功能。比如“拇指文学”、“短信平台”,就能够在盈寸之地——手机显示屏上“打出一片新天地”来。虽然其是典型的“螺蛳壳里作道场”,却因形式繁多,五花八门,呈现着其他任何信息传播工具都难以替代的特殊功能。因此,网络阅读与鉴赏应包括名目繁多的“手机文章”。此中鉴赏的心境与过程,当与上述的电脑文章的阅读与鉴赏又有新的不同——它基本上是以一种休闲的娱乐方式进行阅读与鉴赏的。因为它的实用功能,较之计算机相对弱化了许多,所以休闲和娱乐的方式,更显现着一种即时性和随意性。这就决定了“手机文章”的阅读鉴赏,只是作为网络阅读的一个分支或一个补充。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提升及信息负载量的迅速延展扩大,其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可观的。
三、解读“深阅读”
有学者将崛起并迅疾风行的网络文学语言的特点概括为:超文本性、口语性、自创语符、语种混杂、幽默感等。可以看到网络文学依靠网络这个综合性媒体获得文本形式上最大限度的自由,键入、复制、移动、清除、插入、刷黑、斜体、链接、分段、分行、动画等等。而且,“在整整齐齐的复制文字组成的方块阵、淡入淡出的文字、漂移过屏幕的诗行、顽强地排列过三行以上的惊叹号、如一声叹息般漫长的空行甚至满篇的错别字,网络文学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文学的新时代来了”。[8]但这是否是我们所说的被称为给予我们思想慰藉的精神家园的“文学”呢?当然,这还需要由时间来判定。至少在网络文学的“成长期”,它只能是对传统文学观念与文学作品的补充,而不会是全部。
有学者把这种网络文学的超文本性,称为一种“碎片化”的阅读。把视听碎片化,把生活碎片化,正好满足了现代人快节奏工作中挤出的碎片化时间里的阅读和欣赏需求。然而这种种“碎片式”的浅阅读,能培养现代人的那种如孔子“不读诗,无以言”和苏东坡“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艺术人格与儒雅气质吗?回答是或然的、多向的。即传统的艺术人格与儒雅气质,需要从包括阅读经典在内的蕴蓄着优秀文化信息的历史传承中得来,也需要现代人格与各种文化积淀的契合,从而产生作用。孟子认为,“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9]意思是说:讨厌那些穿凿附会的小知识、小智慧,喜欢那些如大禹治水,顺水之性的大知识、大智慧。而“碎片化”的阅读难以成就大知识、大智慧。因此,传统的阅读与现代的阅读,也必须互融互补,才能保障人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日前,全世界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时,有人惊呼:肥胖、近视、成瘾,是人类作为物种进化的三大标志,而这三大标志都与包括不正确的阅读方式在内的不正确的生活方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数字化的“泛阅读”时代,纷繁与杂多的信息,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我们人体本身。一些学者发出由衷的质疑:屏幕阅读方式怎样影响了人们的视力和脊柱?怎样影响着人们的生理构造、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说得更严重一些,怎样影响着人类的进化?专家认为:电脑屏幕除了对视力的影响外,电脑辐射对皮肤也有很大伤害。同时,电子阅读带给人类的还有鼠标手、电脑脖等有形的病变。通过对患者脊柱的临床研究与治疗发现,人类形成的几个生理弯曲特别是颈椎正在变直,严重的有些出现了反弓。[5]有人把后工业社会称为“现代-后现代”社会,也更简捷地称为“信息”、“数字”或“读图”时代,后三种称谓都与我们的“泛阅读”有关。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生存,将更多地由简单的四肢劳动向“视觉-大脑”综合劳动转化。如果从宏观的视野分析,这或许不是一件好事,它既改变了人类的自身进化,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改变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如果人类还不以崇高的理性加以控制的话,泛滥的信息将造成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浅阅读”,分散乃至分裂我们人类必须的专注力与思辨力,使思想继续走向平面化、单一化和功利化。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难以回避的生存悖论: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贫乏,使得我们愈来愈感觉到生存的荒诞,从而不仅丢失了幸福感,也与安全感渐行渐远。如博尔赫斯所言“: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我来说,被图书重重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只到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挨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10]幸福是一种比短暂的愉悦要深刻的感受,“深阅读”也是比普泛的“浅阅读”要广远的阅读活动。浅阅读感受世界,深阅读思考世界;感受或许只能适应,而思考才有可能超越。当新的阅读革命到来之际,我们需要以坦然的胸怀,在直面“泛阅读”时代的同时,既不排除给人以娱乐的浅阅读,也不排除给人以思想的深阅读。这样,我们才能在超越物化世界的同时,也超越日益“物化”的自我。
[1]互联网,http://wenxue.0943.com.cn/wx/xw/xd/xiaoyao/1.html.
[2]人民日报[N].2009-04-23.
[3]李雾.小布什、奥巴马……都是爱书人[N].南方周末,2009-04-23.
[4]赵毅衡.“晕书综合症”[J].读者,2009,(14):6.
[5]倪光辉,王君平,杨健.电子时代,怎样品味书香[N].人民日报,2009-04-23.
[6]陈歆耕.当代文学及其变化趋势[N].文汇报,2009-07-04.
[7]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王先霈,王耀辉.文学欣赏导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6.
[9]刘伟.为官治政,读书为要[N].人民日报,2009-05-03.
[10]刘玉堂.读书的幸福[N].新华日报,2009-04-21.
G 2
A
02-7408(2011)01-04-03
宋新军(1959-),女,河南卫辉人,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伦理学。
[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