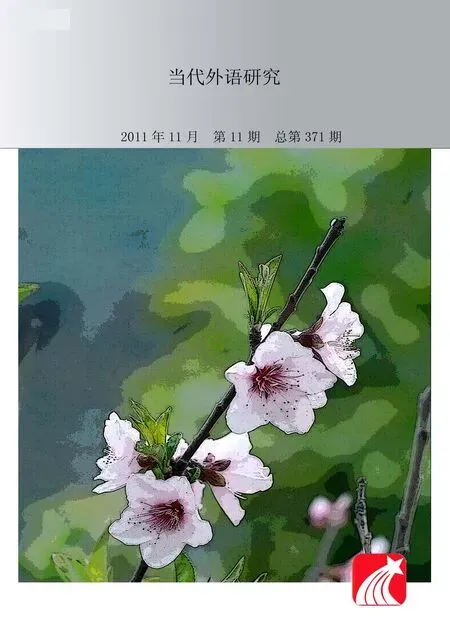工科博士生英语学习动机、技能需求调查及原因分析
马铁川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102206)
1.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二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下,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本、硕阶段改革成果层出不穷,但是针对如何培养博士生语言能力的实证研究却不多见,博士生的英语教学改革成果甚少。胡家英(2009)、从丛(2004)和张承平等(2003)在研究我国目前博士生英语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时指出,由于针对博士生这一少数高层次专门人才群体的英语学习动机、专业及年龄特点研究不够,使得博士生英语教学长期以来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与本、硕阶段重复,教学资源浪费,教学方法陈旧,重视以考试为导向的语言知识的输入,忽视以语言应用为导向的语言技能培养。
因此,为了促进博士生教育的发展,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提高培养质量,博士生的英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要想使改革取得满意的成果,对教学目标做出准确定位,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做出最佳选择,首先需要对博士生英语学习动机和技能需求进行调查研究。本文对带有工科专业特点的博士生群体的英语学习动机和英语技能需求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原因分析,藉此对博士生英语的教学改革提出建议。
2. 学习动机理论及问卷因子设计
2.1 动机理论概述
教学大纲中教学目标的制定要由需求分析来决定,需求分为社会需求和个体需求。个人需求受制、依托、服从于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是每一个个体需求的集合。无论是个体需求还是社会需求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反映在学习者个人身上就是一种学习动机。动机是为了满足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动力,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需求),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个人需求)要掌握的某种谋生手段而诱发的一种欲望。迄今,学者们已对语言学习动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理论观点。早期的有本能论学派的巴甫洛夫(Pavlov)的经典性条件反射学说,行为主义学派桑代克(Thorndike)的联结论以及斯金纳(Skinner)的操作学习论。后来心理语言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又提出了成就动机理论,人文主义学派的马斯洛(Maslow)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认知学派加涅(Gagne)的学习条件论,海德(Heider)和韦纳(Weiner)的归因理论。上个世纪末匈牙利学者Dornyei又提出了外语学习动机的三维框架理论等。除此之外,从社会心理语言学角度对语言学习动机理论与实践研究贡献最大的还是由Gardner和Lambert(1972)提出的动机理论,下面进行具体介绍。
2.2 二维度学习动机理论
Ellis(1997:117)指出,“在二语习得领域里对动机和态度作了最广泛深入研究的是语言学习社会心理学家Gardner和Lambert,许多研究都是他们开创的。”Gardner和Lambert在多年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典的动机二维度概念,包括融入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和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前者指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有真正的兴趣,期望参与或融入该社团的社会生活,后者指学习者学习目的语具有工具性目的,希望通过学习该目的语获得某种实际的或具体的东西,如通过某种考试、获得某种职位或职称、阅读专业文章等(Gardner & Lambert 1972;Lambert 1974;Gardner 1985)。他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语境条件下,这两个动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一观点后来继续被Lukmani(1972)的研究证实。而给出这两个动机的具体差异解释的是Oxford和Shearin(1994:14),他们认为“这种差异可以由目的语在语言学习者所处的环境中扮演的角色来解释。当目的语的功能是‘外语’,即除了课堂以外,学习者没有机会在课堂以外使用目的语与讲目的语的本国人进行交流时,工具型动机在目的语学习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当目的语的功能是‘第二语言’,即学习者处在一个典型的以目的语为主要日常交际工具的环境中来学习目的语时,融入型动机起主导作用。”
另一对经典的动机二维度概念是Deci和Ryan(1985,1995)在自我决定理论里提出的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该理论认为,当采取某种行为纯粹是为了获得该行为以外的某种东西时,如通过考试或获得经济报酬,这种动机就是外部动机;如果个体对学习过程本身产生兴趣,学习就是为了在该行为中得到满足,那么这种动机就是内部动机(Deci & Ryan 1985)。Deci和Ryan当时的研究发现内部动机的作用远远优于外部动机,但随后有研究证明两种动机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在学习中也具有不同的作用,而且当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结合在一起时,更有助于内部动机的提高(Deci & Ryan 1995)。
“当今的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对应的”,即融合型动机属于内在动机,工具型动机则属于外在动机,“学生的学习一般都是由内外动机或工具型与融入型动机的合力所致”(Chambers1999:52)。我们将会在这些理论基础上进行本研究调查问卷的设计。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对象
本研究以华北电力大学在读博士生为调查对象。该校是一所电力专业学科特点的工科院校,所招博士生为清一色电力专业。按照国家《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大纲》(研招办1992)的培养要求,博士生英语的教学应该是“英语+专业”,教学目的是能够以英语为工具,熟练地进行本专业的研究并能进行本专业的学术交流。针对华北电力大学的专业特点,“英语+专业”中的“专业”应该定位在与电力行业相关的工科专业。但是“英语”的定位是什么?即以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英语学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本研究调查对象,即该校博士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做出定位。
该校是一所教育部重点大学,博士生生源质量高,从学生档案资料和入学英语测试成绩得知,绝大部分已经通过英语六级,基本都已具备很强的阅读能力,较强的听力能力和一般性题材的写作能力。总体上英语水平较高,基础阶段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与电力行业相关的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应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尤其是口语和写作能力。但是,带有工科专业特点的该校博士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是什么?与别的学习者有什么不同?他们英语技能需求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的考察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在对他们的专业和英语水平定位的基础上,我们采用问卷的方法进行实证调查。
3.2 问卷因子设计
从Oxford和Shearin(1994)的研究结论来分析,在国内高校课堂语境条件下已具备较高英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工科博士生英语学习的主导动机应该是工具型动机。他们学习英语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提高个人的竞争力和社会地位,更好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工作的强烈愿望和态度。因此本研究调查问卷的因子1命名为“学术研究和专业发展”,代表工具型动机或外部动机。因子1包括4个题项:题项1观测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动机程度,题项2观测与工作发展相关的动机程度;题项3、4是前两个题项的负选项,总体上表达了学习目的语与提高个人的竞争力和社会地位,学术研究和工作发展之间的关系。
因子2用于调查融入型动机或外部动机,命名为“内在兴趣”。Vallerand(2000)在上述Deci和Ryan(1985,1995)的自我决定论的基础上按层次高低把内部动机(融入型动机)分为三种类型:(1)了解刺激型,指个体为了获得新知识,了解周围事物,探索世界,满足个人好奇心或兴趣的动机类型;(2)取得成就型,指与个体试图达到某一目标或完成某项任务相关的动机类型。与了解刺激型比较,它具有更多的自我决定成分;(3)体验刺激型,是最具有自主性的内部动机形式,个体把行为完全接纳为自我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从事某种活动是为了行为本身内在的快乐和愉悦。因子2中的题项5用来观测类型(1)。题项6则观测类型(1)和(2),因为方便上网、读报而学英语既是兴趣驱动,与题项5的了解文化、风土人情相比又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题项7用于观测类型(2),提高英语思维能力是主要学习目的。题项8观测类型(3)。因为事实表明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个人魅力对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兴趣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即使一开始学生对英语可能没什么兴趣,但教师流利生动的讲授和互动交流吸引了学生,学生在享受听课和互动交流的过程,英语的学习自然地进行。题项5、6、7、8在本研究中定义为“完全融入型动机”,代表着融入型动机或内部动机的3个类型,将和工具型动机作对比分析。因子2中的题项9和10在本研究中定义为“非完全性融入型动机”,因为其中也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工具型动机。无论是Gardner和Lambert,还是Deci和Ryan在对两个维度的研究中都强调两种动机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题项9和10用于了解博士生英语学习的整体感受,即感觉学习英语与个人关系很重大,还是令人厌烦的负担,这种感受在整个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对他们的内在学习兴趣发挥着隐型作用。
动机源于需求,又驱动行为的实施。动机更多的是心理层面的东西,它的体现从源头上看是个体的需求,从目标指向上看是个体的具体行为。在英语课堂上学习者学习动机的具体体现就是反应学习者英语需求的英语学习行为表现,对于已具备较高英语水平工科博士生来说就是对各项英语应用技能的需求和学习行为。各项技能需求程度的差异体现着不同个体英语学习动机的差异,对于英语教学工作者来说,该差异是制定教学计划和获取最佳教学效果校准点和标度尺。因此,以改革博士生英语课堂教学为目标的学习动机调查只有纲要式的融合型动机和工具型动机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博士生对英语各项技能的需求进行调查。为此调查问卷中设立了因子3、4、5。因子3命名“技能需求”,有6个题项(11-16),用于了解英语听、说、读、写技能需求比例。由于口语交际和写作技能通常是博士生最弱的两个环节,为了对他们课堂口语训练和写作训练的内容及形式的选择提供依据,问卷中设立因子4和5。因子4命名“口语交际需求”,含6个题项(17-22);因子5命名“写作交际需求”含4个题项(23-26)。
问卷设计采用李克特式五级量表,每个题项后设有5个选项来鉴别学生阅读选题后的反映:1=完全同意、2=同意、3=不确定、4=不同意、5=完全不同意。
问卷最初设定了30个题项,从2009级博士生中随机选取了30名学生做了预测。内在一致性检验显示问卷中有4个题项设计不理想,造成了相关因子信度系数a值偏低。从问卷中剔除了这4个题项后,问卷的内在一致性很好(a>0.8)。最终正式问卷确定为6个因子,26个题项①。
4. 数据统计
我们于2009年12月对同年入学的华北电力大学141名工科博士生发放问卷调查表,收回有效卷135份。所有数据统一录入SPSS16.0。结果显示a值大于0.7,信度可靠。接着,我们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各题项均值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各题项平均值统计
注:表中带字母“r”的题项(如题项4r)表示该题项在调查表中为负选项,统计时做了重新编码,即1→5(完全不同意)、5→1(完全同意)、2→4(不同意)、4→2(同意)。
4.1 工具型、融入型动机统计结果
学术研究和专业发展动机的4个题项的平均值均在2以内,显示学生英语学习的工具型动机强(见表1)。内在兴趣中“完全性融入型动机”的4个题项(5、6、7、8r)的均值(3.9、2.07、3.88、2.51)显示学生的融入型动机不如工具型动机强。题项7均值3.88,题项8r均值2.51,表明提高英语思维能力不是学习者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教师的讲课魅力对他们的学习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题项9的1.73均值和题项10的1.76均值表明学生对英语学习有着强烈的主观愿望,而非专业课学习的负担。
融入型动机数据统计显示博士生英语学习的内在兴趣在一般性英语文化娱乐兴趣和以英语为工具来方便上网、阅读报刊文献获取所需的知识的兴趣之间有明显差别。
题项5和6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指向的兴趣,它们的均值配对样本t检验(t=13.2,p=0.008)说明在融入型动机里博士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更多的是来自为了方便地上网、读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新闻资料等,而不是为了解西方文化、社会生活、娱乐等。
因子1工具型动机的4个题项总平均值为1.7,因子2完全融入型动机的4个题项总平均值为3.09(见表1)。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t=21.45,p=.004),工具型与完全融入型动机的均值具有显著差别,这进一步表明博士生英语学习的工具型动机要远远大于融入型动机。
4.2 技能训练需求统计结果
本研究设计的因子3(技能需求)用于调查博士生对英语听、说、读、写技能及词汇语法训练需求的差异。因为在实际的博士生英语教学中,听、说、读、写技能的训练及扩大词汇、巩固语法等内容通常混在一起,虽然在课程设置和学时分配上有所考虑,但都缺少统计数据的依据。按照需求统计数据,制定技能训练重点和合理的学时分配均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因此因子3中题项11和12设计用来区别博士生对听、说、写的技能与阅读技能和词汇、语法增加巩固需求之间的差异,题项13和14检验听说训练与写作训练需求差异,题项15和16检验学生听与说技能训练需求的差异。对表1中的以上3对题项的均值做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题项11-12、13-14、15-16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其中,题项11-12,题项13-14,以及题项15-16的均值差都存在显著差异(分别:t=-22.63,p=0.00;后者:t=-20.68,p=0.003;t=2.75,p=0.01),这些结果分别表明:(1)博士生对英语听、说、写技能训练的需求大大高于对阅读技能训练和词汇语法掌握的需求;(2)听、说训练与写作训练相比,听、说训练对他们来说要重于写作训练;(3)说与听相比,对说的训练需求大大高于对听的训练需求。
4.3 口语交际需求统计结果
为了对因子4口语交际技能需求的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分别对题项17-18、19-20、21-22的均值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题项17-18、19-20、21-22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从表3可知,题项17-18、19-20、21-22的均值差均存在显著差异(分别:t=-12.24,p=0.007;t=9.86,p=0.011;t=7.83,p=0.015)。这一检验结果表明博士生:(1)练习学术会议发言和交流口语的迫切性要远大于练习日常口语的迫切性,(2)课上更愿意练习与学术会议发言、交流相关的口语,而非一般性的口语,(3)同班上发言相比,参加对话和小组活动更适合他们练习口语。
4.4 写作交际需求统计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博士生写作交际需要的情况,我们分别对题项23和题项24r负选项调整后的均值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题项之间存在显著差异(t=-16.23,p=0.005),这表明博士生对写作训练的需求是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和摘要写作能力大于提高信件、电子邮件的英语写作能力。同时,对题项25和题项26r负选项调整后的均值进行配对样本t,结果也表明两者存在显著差异(t=-12.13,p=0.007)。可见教师多进行实用的英文写作格式、规范、技巧等的传授对提高博士生的写作能力有很大帮助,而仅靠多读、多写、多背对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帮助则作用不大。
5. 讨论
5.1 动机构成及原因分析
依据前面统计结果(表1)可得出博士生英语学习动机成分的图示1。表1和图1中题项5命名为“欣赏”,代表对英语国家文化、习俗、影视、音乐等的兴趣;题项6“阅览”,代表通过互联网、报刊杂志等获取信息;题项7“换位”,代表转换英语思维方式;题项8“吸引”,代表教师的个人素质和讲课魅力对学生的影响。

图1 动机成分比例
5.1.1 工具型动机凸显的原因
从图1可知,博士生学习英语的工具型动机(69%)要远远大于融入型动机(31%),这一结果表明他们的英语学习以实用为导向,带有很强的目的性,而非来自个人的兴趣。个人专业的发展,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在未来的工作中取得成绩是他们学习英语的强大动力,而与专业发展无关的英语学习兴趣已退到次要位置。该动机特点与本、硕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区别凸显在两点上:年龄和社会角色定位。本、硕生阶段的英语学习趣味性和应考性相对来讲较为突出,因为这两个阶段的学生在年龄上还没有完全进入成年期,社会角色定位还不明确,考试任务较重,同时还面临升学和就业的压力。
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已经有了工作经验,因此在专业和社会角色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英语对他们来说已由一门课程、升学就业的门槛和接触西方文化的媒介转化为服务于专业发展的工具。他们对英语的需求受专业语境制约,任何英语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都带有完成某项研究或工作任务的目的性,而非专业需求的个人兴趣较弱,甚至可说是淡漠。博士期间基础英语学习已经完成,没有四、六级英语考试、考研、硕士学位英语考试等硬性任务的压力,学习时间相对较紧,因此提高英语应用能力的学习目标非常明确。这些特点决定着他们很难把学习兴趣投放在与本、硕阶段相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上。某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后,或出国访学回来后,或提笔撰写英语论文和摘要时,他们就可能重新认识自己英语学习的目的,以专业研究课题为对象的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对他们来说变得更为重要。
5.1.2 融入型动机的隐性作用
图1显示在融入型动机中“阅览”和“吸引”占有很高的比例,分别为38%和33%,“换位”、“欣赏”占得比例很小,分别为15%和14%。这说明博士生英语学习的内在兴趣主要来自于更方便地获取信息和教师个人魅力。由于成人化的心理和专业的定位,诸如欣赏西方文化、风土人情等的一般性兴趣已经淡出他们心理需求,“阅览”占38%、与“欣赏”占14%的差别,以及前面的题项5和题项6均值的显著差异性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换位”占15%、“吸引”占33%及前面题项7和题项8r均值的显著差异证明了另外两个事实:其一是博士生学习英语不再像本科生那样带有虚幻的转化英语思维的想法,也不会因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对英语学习的态度,他们对英语学习的需求更具有实际性和目的性,从学术研究和工作发展的角度来融入英语文化是他们对英语学习的理性认识和努力方向。其二是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了,但同本、硕生一样,教师的个人素质、英语水平和讲课艺术依然是激发他们学习兴趣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社会属性与人际关系密不可分,对教师素质、能力的欣赏必然会引起对其语言的欣赏,从而产生拉近交际距离、主动增加互动的欲望,在这一心理欲望的满足过程中,英语学习动力得到了增强。
相对于均值较高的题项5、6、7、8r,题项9和10r的均值仅为1.73和1.96。这表明博士生在心理层面对英语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和较强的情感寄托,没有视英语学习为额外负担,产生逆反心理,而将其视为对自身心理需求的满足。这种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的愿望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如互联网、文献资料等含有大量的英文信息,要想便捷、大量的获取就需要直接用英语来阅读和交际。该事实在他们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隐性的作用,即在博士生们潜意识里会形成一种共识:学好英语无论是对自己专业发展,还是对个人和社会生活范围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都非常重要,不因眼前学习和研究任务的轻重而区别待之。
5.2 技能需求原因分析
从表1以及上述相关统计结果可概括出博士生对各项具体英语技能不同需求的比例表,口语交际需求比例表以及写作需求比例表,分别为图2、3、4。

图2 技能需求比例

图3 口语交际需求比例

图4 写作交际需求比例
图2、3、4十分清楚地标明博士生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需求中,听、说、写要大于阅读;在听、说、写需求中,听、说要大于写;而在听说需求中,说要大于听;在口语会话训练需求中,与学术会议发言、交流相关的口语需求要大于日常口语需求;在口语训练方式选择中,更愿意在会话和小组活动中练习口语,而不大愿意在班上发言来训练;在书面语训练需求中迫切需要的是学术论文和摘要写作能力的提高,而不是日常写作能力,他们更需要获得写作规范和技巧上的指导和帮助,而不太情愿通过大量的读、写、背来提高写作能力。
探究造成这些差别的缘由需要追溯到博士生英语学习工具型动机远远大于融入型动机这一基本特征,该特征又与博士生的年龄和专业特点密不可分。经历了常年的英语学习,博士生的英语阅读已不是问题,语法、词汇知识的积累也较为扎实雄厚,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受传统教法和考试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他们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还较为薄弱。到了博士学习阶段,有的学生已经有工作经历,参加过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或做过短期的出国访问、考察等。这些在课堂上无法体验过的珍贵经历会让他们对自己以往的英语学习进行反思,向自己提出诸如什么是英语,什么是自己的弱项,在涉外交际的场合中让自己感觉尴尬时最懊恼的是哪项技能等问题。
由于专业的定位和学术研究任务的加重,以及对未来学术研究和工作发展的期待,即使没有工作或出国经历的博士生也会对英语学习的需求抱有明确的认识。继续沿用本、硕生阶段学习内容和教法会让他们产生逆反和茫然,与期望相去甚远。已经经历过的和必须经历英语应用的语境会让他们更加清楚英语学习的语言技能定位。流利的会话交流,高质量的论文和摘要的写作成为他们迫切需要,关系到他们未来发展,是走向国际化的根本保证。英语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训练都要经由这两个渠道向外展示,都要在这两个语言交际的领域转化为实际的活动和行为。在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写作英语论文变得不可回避,国际会议上出现的交流问题以及英语论文写作中的困难等都会驱使他们工具型学习动机得到增强,融入型动机受到削弱,进而与工具型动机相关密切的英语知识和技能必然会提到学习日程上来,占据主要需求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在技能需求问卷调查中,学生选择听说和写技能需求的比例占到了绝对优势的78%,而阅读需求仅占22%。
相对于写作技能需求的19%,听说需求占到了81%。这反映出博士生对提高会话技能的渴望远大于写作。这可以从两种语境的交际情境中找到答案。写作语境是学生独立交际的语境,不需要另一个交谈对象的存在,学生可以借助参考资料和工具书来完成。多年学习英语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使得他们具备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自信心,即使遇到困难,大多也能自己独立解决。同会话相比,他们对靠自身努力来渐进提高写作水平更有信心。而会话的语境则不同,需要说和听者共同参与,需要相互交流的情景,学生无法个人实现。因此,同写作相比,他们对自己的英语会话更没有信心。然而,以专业和工作发展为导向的工具型动机又更多地驱使他们尽快提高英语会话能力,以适应交际的需要。在他们自我学习英语过程中很难有机会和人练习会话,所以渴望能在正规的英语课堂上找到机会和交流情景,得到教师的及时引导和帮助,以提高靠自己无法实现的英语会话能力。
统计分析得出的听(35%)、说(65%)比重表明,在他们的学习以及语言交际应用的过程中这些工科类型的博士英语学习者已经较为深切地感悟到这两项技能的重要性。专业的发展离不开用英语与同行交流,听与说能力的训练因此仍然非常重要。与班上发言相比,他们对对话和小组活动的训练更为偏爱,学术会议交流的情景则是他们更加重视的会话语境。面子问题与实际应用的需求使得他们更愿意接受较小规模的自由交谈和语言互动。课堂的口语训练有效地和国际会议的语境结合自然成为他们最期待的内容。
工具型动机对博士生写作训练需求的选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需要的是与专业发展相关的学术论文及摘要的写作训练(73%)以及写作规范及技巧的指导(66%),而非一般的写作训练(27%)和大量的写作练习(34%)。本、硕阶段的英语写作练习不涉及到学术性的东西,而到博士阶段,学术英语写作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写作能力的提高也自然成为他们语言学习的迫切任务。课堂上他们对做大量的读、写、背的练习兴趣不高,教师更多地需要在撰写英文学术论文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
可见,作为成年的语言学习者,受年龄特点、社会角色定位等因素的决定,特别是专业发展的驱使,工科博士生对英语学习的工具型动机凸显,进而导致了对以国际性学术会议为语境的英语会话技能训练和学术性英语论文写作技能训练的迫切需求。
6. 博士英语教改的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博士生英语的教学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学习者的角度理清了工科博士生对英语教学的期待和要求:培养以国际性学术会议为主要语境的流利的英语会话交流能力和学术性英语论文及摘要写作能力应该是博士生英语课堂的主要教学任务,而前一个任务的重要性又高于后一个。通常仅有一个学期的博士生英语课教学如果能在这两个能力的提高上取得明显的教学效果就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博士生英语的教学是成功的,否则不得不说是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与学生们的期待相悖。随着高校博士生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博士生英语教学如果继续遵循传统的本、硕阶段英语教学的途径肯定行不通,从他们英语学习的动机出发来研究制定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选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会使博士生英语的教学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取得理想的改革成果。
附注:
① 限于篇幅,这里不附问卷表;需要者请与作者联系。
Deci, E.L. & R. Ryan. 1985.IntrinsicMotivationandSelf-determinationinHumanBehavior[M]. New York: Plenum.
Deci, E. L. & R. M. Ryan. 1995. Human autonomy: the basis for true self- esteem [A]. In M. H. Kernis (ed.).Efficacy,Agency,andSelf-esteem[C]. New York: Plenum.
Chambers, G. N. 1999.MotivatingLanguageLearner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Ellis, R. 1997.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dner, R.C.& W.E. Lambert. 1972.AttitudesandMotivationinSecondLanguageLearning[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Gardner, R.C. 1985.SocialPsycholog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RoleofAttitudesandMotivation[M]. London: Edward Arnold.
Lambert, W. E. 1974. Culture and language as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 In F. E. Aboud & R. D. Meade (eds.).CulturalFactorsinLearningandEducation[C]. Bellingham, Washington: Fifth Western Washington Symposium of Learning.
Lukmani, Y. M. 1972 .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J].LanguageLearning22: 261-273.
Oxford, R. & J. Shearin. 1994.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J].ModernLanguageJournal78: 12-28.
Spolsky, B. 1969. Attitudinal aspect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LanguageLearning19:271-285.
Vallerand, R. J. 2000. Deci and Ryan’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 view from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 [J].PsychologicalInquiry11(4): 312-319.
从丛.2004.博士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6):48-50.
胡家英.2009.博士生英语教学改革的探讨与实践[J].黑龙江高教研究(2):60-62.
张承平、谭雪梅、万伟珊.2003.输出性活动在博士生英语教学中的实践研究[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8(4):116-119.
——王永平教授
——陈桂蓉教授
——拜根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