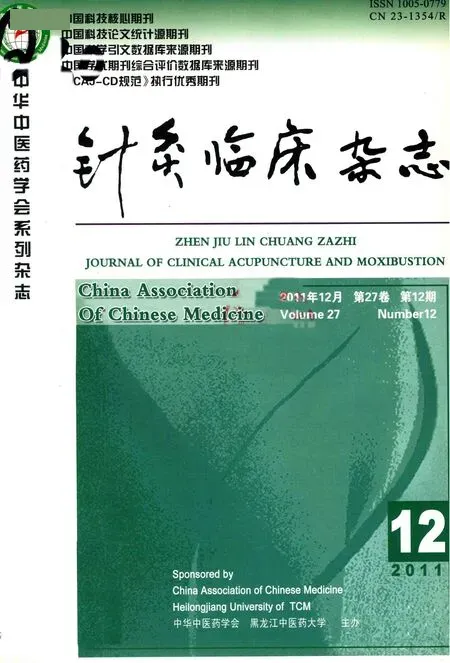《内经》古典针法初探
陈冬冬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济南250014)
所言经者,必是言简意宏而又饱含智慧之作,《内经》以其古朴的文字奠定了中医针刺学的理论基础。其有关针刺方法的内容得到了后世医家长期不懈的发掘与发展,出现了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很多理论、观念甚至出现了相互抵牾的情况,妨碍了针灸理论与临床的进步。大乱纷至,求之与经,在这种情况下溯本求源,从经典中探求针刺之道,探索《内经》古典针刺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1 通经络基本手法
《灵枢》古又称《九卷》,最初应是九篇文章,是为远古先圣所做,也应是现有版本中价值最大的九章。然历史久远,最初的九章已很难确定,但观其文意、文风,《九针十二原》应是开篇之作,《终始》应是最后一篇。这两篇应是研习《内经》古典针法的基础篇章。
《九针十二原》开篇即言微针之用“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指的是开关决渎、补虚泻实、调畅气机层次的针法,对此后世已有大量论述。而通经脉一直被认为是针刺的基本作用,但是其基本操作往往被忽视,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是针入孔穴便是通经络,观先圣《九针十二原》,这是不恰当的。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针各有所易,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是说临证之时要根据病情不同,取九针之长来祛疾。毫针之用便是“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仔细体会这句话就可以明白通经脉之手法:“如蚊虻喙”(蚊子、虻虫的嘴[1])、“静”、“徐”、“微”,《灵枢》作者反复强调其手法要至柔至缓,不可捻转频率太快,亦不可幅度太大,施术者要达到一种静意视义、慎守勿失,手中之针若有若无、若存若亡的状态。
1.1 补泻二义
纵观《灵》、《素》,补泻应有两层截然不同的含义,不把这两层含义分开,就很难明白补泻真义,更不要妄谈补泻之操作。这在一些篇章中已明确说明,只是往往被忽视。《离合真邪论》载:“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荥输,余知之矣。此皆营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这是关于补泻两层含义的明确论述。其一,言具体邪正之气(“邪气从外入于经”),所谓“谷气来也虚而和,邪气来也紧而急”;其二,但言经气之盈衰偏倾,不言具体经气的邪正,是说某一经的经气偏胜(虚)导致的气机不调、阴阳不和。这时的补泻是将偏盛之经气调至偏虚之经(可以是同一经络不同部位也可以是不同经络之间互调),所谓“凡刺之道,气调而止,补阴泻阳,音气益彰”。这就是补泻的两层含义。
1.2 补泻手法
补泻层次不同,操作手法也必然不同。对于上述两个意义的补泻手法《内经》均有说明:对于具体的邪正之气的补泻强调的是医者的针下感觉,正气来时追而济之,邪气已至迎而泻之;对于经气偏倾之补泻的目的是将偏盛之经的经气散开调至偏虚之经脉,已达到气调而止,所谓“上工平气,中工乱气,下工绝气危生”。前一层次的补泻对施术者的手法要求极高。首先便是得气,得气更主要的是医者的针下感觉,并不是患者的酸麻胀,这应该是明确区分的,现存文献中清代以前的医家没有一人言酸麻胀是得气。其次,要分清正邪之气。这都需要医者灵敏的指感。针灸大家承淡安[2]曾假托紫云上人之名详谈练针之法,悬纸于壁,日钻千孔而不辍,以此练习指感;针灸名家张善忱[3]主张将正气及风寒暑湿燥火六淫邪气一一辨明,才能补泻有据。
《内经》补泻经后世发展形成诸多争议,理论越来越多,其结果往往是“不可以言诊,足可以乱经”。先圣著《内经》是为了“传之后世”,其基本要求是“易用难忘”,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来阐述形而下的操作,用心良苦:“道”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哪怕是不能传之以道,也要授之以术。《素问》反复阐述补泻的操作,“泻曰必持内之,放而出之,排阳得针……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泻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吸而徐引针……复以吸排针也”。言及补泻操作之具体可谓苦口婆心。后世补泻论述极多,需要强调的是呼吸补泻。
《内经》重视气机的出入升降,“根于中者名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名曰气立,气止则化绝”,而呼吸是唯一可以具体操作的。《伤寒论》述例:“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天年》曰:“呼吸虚微,气以度行”,呼吸直接决定内外虚实,应是补泻中最重要的一步,可惜对于呼吸补泻今人大多已轻视不用。
补法操作要求意若忘之,手持针,似行似静,似提似按,取其静意;泻法操作“放”、“排”、“转”,突出其动。转,《说文》云:“运也”。那么,泻法很可能是一种单向的旋转,而不是双向的,此与后世泻法拇指后转用力重前转用力轻是有相通之处的,此问题值得思考。
2 明于脉诊,补泻有据
《终始》明确提出了脉诊诊断的方法:“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三盛而躁,在手太阴。”这也是后世气口人迎脉法的起源。
《内经》中,《六节藏象论》、《终始》、《经脉》、《禁服》、《五色》、《论疾诊尺》等篇章中均有人迎气口脉法的论述,内容虽多有异同,但根据上文的论述,应以《终始》为准。人迎气口脉的定位古今争议颇大。《脉经》云:“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左为人迎,右为气口。”《千金方》[4]引用《脉经》云:“左为人迎,右为气口。”李杲在《内外伤辨惑论》[5]中论到:“人迎脉大于气口为外伤,气口脉大于人迎为内伤。”李时珍在《濒湖脉学》[6]中亦说:“左为人迎,右为气口。”李梴《医学入门》[7]云:“气口,右手关前一分,以侯七情及房劳、工作勤苦与饮食无节……人迎,左手关前一分……皆为外感有余之症。”均将人迎气口脉位分别定为左右手寸口脉之关前一分处。民国医家王雨三著《治病法规》[8]将人迎脉定位为左手之关脉,气口定位于右手之关脉,并将此脉法作为一生治病之根基。张介宾《类经》[9]曰:“而且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以致后世惑乱,遂并阴阳表里大义尽皆失之。”显然不赞同上面的观念,他认为人迎脉即是足阳明之人迎穴处动脉,气口脉即是双手寸口太阴脉。
综合各家观点,将人迎定位为人迎穴所在的颈动脉是牵强的。《脉经》关前一分左为人迎,右为气口甚合古意。“盛”,《说文》云:“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很明显是作名词用,而有大小多少的概念。放在《终始》篇中说的是脉势的大小,多大是“一盛”需要理论与临床的积累求得。但就其脉法本身而言这是一种反应气机出入升降的脉法。临床大家黄元御、彭子益理论重视气机升降,其脉诊亦然,在其著作《四圣心源》[10]、《圆运动的古中医学》[11]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与他们的理论相参,尺经关化寸,寸由关化尺,结合临床可粗略的将关前一分与关脉的比较来定一盛二盛三盛:最强脉势(“盛”),关前一分小于关脉为一盛,等同为二盛,大于为三盛。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补泻祛疾:“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补一泻,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躁取之上,气和乃止……太阴主胃,大富于谷气,故可日二取之也。”
如此,需补泻之经已由脉诊明确。
3 选穴与取穴
关于选穴,《九针十二原》强调五输穴与原穴的使用,《终始》篇作为古《九卷》的总结性文章已无需再提选用何穴,基于此,结合《内经》其他篇章,用五输穴、原穴治病应是先圣所施行的。
《内经》论脏腑有两个系统,藏象系统与脏器系统,藏象系统《内经》虽只在《六节藏象论》一篇明言,但是古典的中医更重视这种近乎“道”的合于天地的系统。将两个系统混淆很难明了《内经》,而两种系统并存必然导致诊断治疗的两面性。涉及到脉法,《脉要精微论》中“尺内两傍则季邪也,尺外以候肾……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胫足中事也”是脏器系统的脉法;《平人气象论》、《玉机真脏论》、《三部九候论》等篇讲的主要是藏象系统的脉法。这两个系统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在脏器系统中言心肺不足、脾肾不足或者心肺脾肾俱虚是可以的,因为针对的是具体脏器,脏器系统可以是多个脏腑同时出现疾病;但在藏象系统中这是不对的,是“童子所知”的错误。藏象诊疾必是一人对应一象(春夏秋冬土),一脉对应一象,用药方之气味对应一象。《示从容论》云:“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针灸、砭石、汤药,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长而问之少,余真问以自谬也……此皆工之所时乱也……此童子之所知,问之何也……一人之气,病在一脏也。若言三脏俱行,不在法也。”
藏象系统脉法最基本的内容就是将天人感应的四季五时象对应春弦夏钩秋毛冬石长夏濡(“如鸡践地”)五脉。《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黄帝曰:以主五输奈何?岐伯曰: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输;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由此可建立对应的关系如表1。

表1 五输穴与脉象对应表
通过表1,如何脉诊定经选穴已十分明确,如整体脉象以弦为主,则取荥穴。
取穴同样十分重要,《邪气脏腑病形》载:“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四时气》载:“黄帝问于岐伯曰: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定?岐伯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都强调了取穴的重要性。《杂病》载:“心痛,当九节刺之,以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背输》载:“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输也。”《卫气》载:“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乃刺而予之。”则指出了取穴的具体方法,以手按之,上下求所,乃得其穴。王执中《针灸资生经》[12],重视此法,并名之曰“针灸受病处”。此外,有些篇章则直接指出了一些穴位的特殊取穴方法,如《邪气脏腑病形》云:“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取诸外经者,揄申而得之”,《针解》篇也有类似论述。
4 进针深度与留针时间
《内经》用针倾向“稀而疏之”。《九针十二原》治病所选范围不过“五脏五输,六腑六输”,《终始》治病排除需要“宛陈则除之”的放血通络,所用针仅仅三针。
《内经》论述针刺深度与留针时间有其灵活性,如《邪气脏腑病形》云:“是故刺急者,深内而就留之。刺缓者,浅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根结》云:“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剽悍滑利也。”《逆顺肥瘦》则指出刺瘦人者,浅而疾之;刺常人者,无失常数;壮士气涩血浊宜深而留之,气滑血清宜浅而疾之;刺婴儿浅而疾发针。然虽有变化,终有“常数”准绳。
《经水》篇明确的说明“常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泻也。足阳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阳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阳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阴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阴深两分,留三呼。足厥阴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阴阳,其受气之道近,其气之来疾,其刺深者皆无过两分,其留皆无过一呼。”针刺最深者不过六分,留针最久者不过十呼。与《内经》时代较近的《针灸甲乙经》所载诸穴留针也不过数呼,也说明了这一点。《内经》重视诊疗的太过不及,失其度反变生它害。当然这是建立在准确辨经,准确定穴取穴的基础上的,定经取穴之法上文已明确说明。
5 典型医案
患者,男,27岁,4天前游泳后便觉左腿乏力,时痉挛不舒,经医针委中、承山、昆仑等穴效果不显。诊其脉,阴阳尚平和,此乃经络不通之小疾,遂取左昆仑穴,进针约五分,行通经络之手法,得气后留针七呼,行针时患者述左腿痒甚,此经络疏通之象。出针后,诸证皆失,左腿活动如常。
患者,女,54岁,生气后双耳暴聋1周,多方治疗无效,脉之,病在阳明(即“三盛”),脉中取滑数(夏象),取之输(见上文)先补太白,深约三分,留四呼;继泻陷谷、冲阳,深约六分,留十呼,泻完陷谷后患者已觉双耳豁然开朗。
6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内经》古典针法的基本脉路,对于仅仅是经络不通之小疾,只需取毫针之长用正确的手法通其经络;一旦出现阴阳偏颇,就要在脉诊的基础上取经选穴,把握正确的针刺深度与留针时间,补虚泻实,调其阴阳。此外,针下辨气,邪气至则泻,谷气至则补亦十分重要。“去圣远矣,针道之不存也久矣”,水平所限,一家之言,关于《内经》古典针法的一些问题,还有赖于同道一起探索。
[1]河北医学院.灵枢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9
[2]承淡安.承淡安针灸师承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31
[3]张善忱.论针下辨气[J].中医杂志,1959(11):62-63
[4]唐·孙思邈.千金方[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社,2006:607
[5]金·李杲.内外伤辨惑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4
[6]明·李时珍.濒湖脉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18
[7]明·李梴.医学入门[M].北京:人名卫生出版社,2006:174
[8]王雨三.治病法规[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4
[9]明·张介宾.类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65
[10]清·黄元御.四圣心源[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
[11]彭子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12]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