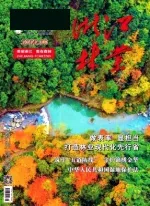最忆荷塘清韵
□撰文 /赵 畅

家乡荷塘
在老家,一塘荷花是我童年的梦呓。
孩提时,我被寄养在浙东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离家不远处有一口硕大的荷花塘,每至仲夏季节,那里便成为我和伙伴们玩赏的好地方。
老家所谓的荷花塘,充其量,不过半塘而已。虽不是满塘锦绣,但已足够生香增色的了。站在塘边赏荷,但见其枝条袅娜,纤细而不柔弱;其叶亭亭如盖,舒卷而不轻佻;其花盈盈如贝,香远而益清。正是大暑天的中午,瞒着家人偷偷下塘戏水的我们,一直在荷花的间隙里穿插游玩,却始终未敢惊扰她,更不敢攀枝摘叶掐花而去。尽管未敢惊扰荷花姑娘,但我们终究满心生就暗恋之情。“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燃高烛照红妆”,不远不近的凝望,距离产生的分明是一种朦胧之美。
或许,是因为生活在小山村,那见惯了的山林于我们不再是风景,倒是对荷花塘里的丛丛荷花宠爱有加。下雨的时候,我甚至会戴上斗笠,一个人痴痴地看雨中荷花。雨不大,细雨落去,如蚕食桑叶,若石击深潭……每一柄荷叶都像一把神奇的乐器,弹奏出悠远清脆而让人沉醉的音乐。滴翠的荷叶,像打了蜡一般,油光闪亮的,待落上雨丝,但见团团荷叶上瞬间即凝聚出清亮的水珠,密密麻麻,恰如清风吹拂着一池湖水;又恍如串串佛珠,让人悟到,原来喜乐悲愁全在一念之间。盛开的莲花,委实如精灵般迷人,又如婴儿般笑绽的粉靥。裸露在外的莲子,壮润得如少女般丰盈之乳。光亮亮、鲜嫩嫩,高高矮矮,肥肥瘦瘦,浓浓淡淡的荷花,在雨中的神态更是各尽其妙——如成群的仙女或提水洗浴,或抿嘴羞涩,或笑脸半藏,或聚首细语……恰如一幅幅巧夺天工的水彩画,一首首意境朦胧的抒情诗。风停雨歇后,便有蜻蜓翩翩而至,一俟停定于荷花之上,便让人油然吟诵起杨万里的诗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原来,荷花植根于诗中,她曾经在李白诗中徜徉,在杜甫诗中踌躇,在王维诗中禅定,在李商隐诗中啜泣。那飞舞着的“蜻蜓”,不就是唐诗宋词么?是的,荷塘中的每一枝清荷,她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每一个含苞待放的蓓蕾,都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她们都有自己的日日夜夜、朝朝暮暮,她们都有自己的霜痕和雨迹、风节和情愫。
山村除了有真正的青山绿水,更有大自然各种奇妙的声音。在家乡的荷花塘,我就听闻过这种大自然神奇的天籁。一天晚上,我在荷花塘边游走。突然,塘里的蛙声像一首音乐的主旋律,远远近近飘忽而来,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出声音最大的蛙声来自何处,低沉的蛙声源于哪里。让人惊异的是,蛙声高亢时声遏行云,舒缓时绕树三匝。那清亮亮的声音,让人恨不得扑进清凉凉的池塘里。此时此刻,蝉在蛙声停歇时竟也展开了“歌喉”,于是,蛙声、蝉声彼此交错、互相铺垫。刹地,我竟不知自己是置身于大自然美妙的天籁里,还是融合在众多熟悉或陌生的生命中?
这样的夜晚,假若有月色,那是巴不得的一件好事。月光恰到好处地点缀在祖父家的青瓦屋顶上,清晰地勾勒出俏媚的飞檐和黑白相间的马头墙。那半掩着的木窗,在月光下影影绰绰,让人心生许多向往。虽说有月色,但月亮似乎显得躲躲闪闪、羞羞答答。我与祖父走出家门,回眸凝望,月亮在屋脊上,半遮半掩,露出大半个脸。待来到荷塘边,月亮已落到塘中,令荷塘熠熠生辉。不知是哪只青蛙调皮,一跃而起,竟将这满池的清晖搅了个碎,碎成银亮的光点,迷离闪烁。簇拥着月色,蛙声、蝉声连同微风过处令荷花形成的一道道“凝碧的波痕”,丝丝缕缕地流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仿佛要拴住我们一般。突然觉得,这荷塘是一个梦,小山村是一个梦。幽幽清梦,被星光微照,被蛙声拉长,被突然而至的蝉歌提到杨柳的梢头。
曲院风荷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在《杭州花事·陌上花开》一文中写到曲院风荷:“夏日访花,自然是访荷。有曲院风荷在,池内种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又有叶径一米多的大王莲和几厘米的碗莲。访荷池也是有秘诀的,宜在清晨,因荷花天微明时放,待大亮,它倒又复合了。从前花迷,常行舟于放鹤亭,于岸上藤椅躺下,尝藕粉,品新茶,以作早餐,再补睡一觉,那可真是晨风徐来,荷香欲醉了。”因为种种原因,我至今无缘于仲夏时节去那里赏荷,更无缘于晨间去品酽酽农的荷香,但我想象得出,仲夏是荷花的花样年华,整个湖面蓬蓬勃勃地盛开着荷的青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浩荡盎然的青春,由清水烘托,与蓝天相拥,艳丽夺目,无边无际,在太阳的映照下,争奇斗艳,荷池早已变成了一片燃烧的彩霞……这是怎样的一道清雅唯美的风景呀!
真正看到曲院风荷,那是在去年冬季了。雪后的一个下午,也许是因为不太情愿欣赏残枝败荷,游客明显少于往日,场面自是显得有些冷清。可不知为何,当我看到金色的荷茎上依然高高擎着的莲蓬,看着它在雪中构建出的那些孤高姿影,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特有的美,一种常常容易被人忽视但却依然在灵魂中坚守的那种超俗之美和超美之美。从盛开的荷到凋零的荷,它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展示自己的美——从外形的美升华到精神的美。这样的荷塘,不仅仅是一个荷塘,荷塘里的荷花也不仅仅是一池荷花,其中还蕴藏着某些等待人们去发现去领悟的东西。
我国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荷花,似无据可考。但早在3000年前的《诗经》中已经有对荷花的记载。“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彼泽之陡,有蒲与荷”。她从诗经的河流中崭露头角,一路上袅袅娜娜、羞羞涩涩,至遇上屈原,便大放异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第一次将荷高高举过世俗的目光。之后,荷便卓尔不群,大写于我们的精神星空。
春晖荷塘
真正让我心仪的,则是上虞市白马湖畔春晖中学校园内的一个荷塘。尽管现时的荷塘已非上个世纪的那个荷塘,但在我看来,两者有着必然的渊源。这所上个世纪20年代创建于白马湖畔的乡间中学,由经亨颐为第一任校长。因他冲破当时的国家教育制度,贯彻“与时俱进”的教育主张和革新思想,故吸引和聚拢了一大批名师硕彦前去执教、考察、讲学。学校被经营得风生水起,于是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我相信,与春晖中学有关的故事一定像当年那个荷花塘里的水生植物一样茎蔓无数。巨商陈春澜的捐资助学,思想进步、行动维新的“举人老爷”王佐的“撮合”办学,夏丏尊在“平屋”中翻译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丰子恺在“小杨柳屋”创作并发表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弘一法师在“晚晴山房”念佛不忘爱国……正是他们,给后来的春晖师生演绎了无数芳香长留人世的动人故事。于是,油然想及,过去乃至现时的荷花塘里的荷花,肯定就是这些春晖先贤们品行的一种化身。否则,这荷花塘也就不会有这样的袭人清香、神逸风骨了;否则,这许多先贤故事也就不会顺着白马湖的水流淌近百年了。
每每去春晖中学参观,我都会有意无意地去看看荷花塘。虽然我心里无数次地对自己说,这早已不是当年的荷花塘了,但却无法说服自己,有时哪怕瞟上一眼,似乎心里便得到莫大的慰藉。这个情结,不啻缘于自己曾经在春晖中学就读的经历,更缘于散文大家朱自清先生曾在春晖中学执教的一段历史。我笃信,朱自清先生执教春晖时,定然已有了这一片荷塘。他也一定在月夜时独自走过这片荷塘。月色下的荷塘,荷塘里的月色,早已久久地酿在其心里,深深地印在其心间。朱自清先生1927年7月任教于清华大学时写下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无非是借着清华的荷塘一吐为快罢了。
我始终认为,春晖的荷花塘已经不仅仅是一处美丽的风景,还是一种意象,一种品格,一种春晖师生对赓续“健康向上,与时俱进”的春晖精神与白马湖风格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