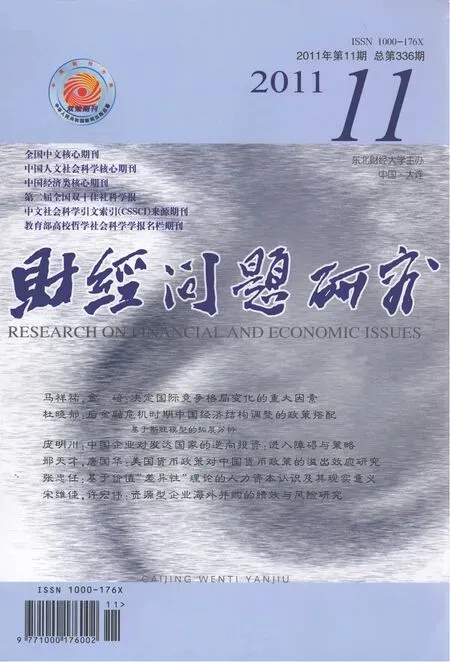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进入障碍与策略*
庞明川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025)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被称为逆向投资,明显区别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投资”,这种逆向投资对于后起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优势是一种更有战略意义的对外直接投资。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化战略型投资和创业活动,被称为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另一条路线[1-2-3]。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的逆向投资就开始萌芽;50—60年代,以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和亚洲的印度、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70—8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逆向投资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长,而且其跨国公司除了在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 (Greenfield FDI)以外,还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公司进行跨国并购 (AM&A)。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逆向投资更是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不仅对发达国家进行的跨国并购案大幅增加,而且在投资动因、投资方式和策略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客观上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逆向投资的并购良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逆向投资又掀起了新一轮热潮。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的统计,截至2005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占到全球FDI数据的17%,而其中20%是投向发达国家;到2009年,前者已上升到20.8%,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比重也大幅增加了[4]。
中国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历程,但发展缓慢。21世纪以来,中国的逆向投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许多行业领先企业开始将目光瞄准发达国家市场,采取投资建厂、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开展跨国经营,特别是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当然,近年来中国的逆向投资也存在为数不少的跨国并购失败案例,造成了巨大的投资损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市场存在诸多进入障碍等不利因素影响,对此,国内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张纪康是国内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他认为促成跨国直接投资经营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试图绕过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现实中,特定行业市场的产业国际化程度越低,直接投资进入该行业市场的阻力或障碍往往便越大、越多,且所引致的综合经营成本也越高,甚至可能高过此种商品在国际贸易情况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说,这些进入障碍包括:投资资本筹措中的较高资本费用、规模非经济障碍,具体表现就是直接投资进入企业的成本竞争劣势和创新竞争劣势、跨国经营环境上的差异障碍、直接生产经营中投入要素资源的约束障碍、直接投资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管理障碍、由东道国先入企业的阻截性定价策略所构成的进入障碍[5]。江勇和余海丰从中国跨国企业的自身障碍、中国政府参与方面的障碍、东道国的进入障碍等几个角度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障碍进行了分析[6]。韩世坤和陈继勇分别从并购主体缺位、并购主体错位、政策支持乏力、法律约束乏力、资本市场依旧脆弱以及中介联结松散等方面对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并购的障碍因素进行了探讨[7]。李优树则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性障碍、中国政府宏观管理制度障碍、东道国投资环境制度障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8]。覃晓雪和李灵稚认为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政策法规不健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企业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认识不足、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具有自身的劣势等[9]。赵燕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障碍包括:技术障碍、体制障碍、资金障碍、人才障碍[10]。朱玉林认为,从微观层面上看,存在的障碍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与国际大企业实力差距明显;企业产权边界模糊,主体难以确认,影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积极性;缺乏跨国并购经验。从宏观上看,存在的障碍包括:审批制度僵化,体制尚不完善;法律残缺,增加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金融信贷体制对企业筹资、融资等方面的限制和约束仍然较多;缺乏中介机构支持等[1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学者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障碍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但并未涉及到对发达国家市场的系统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所面临的障碍与问题也缺乏深入研究,这样,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逆向投资的顺利开展。因此,系统研究影响中国企业开展逆向投资的因素和进入障碍,有助于提高对发达国家市场与政府的认识,从而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促进中国逆向投资的健康发展。
一、进入障碍及其测量: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
从一般意义上说,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必然要面临一个对不同产业和区位的进入问题。从产业上说,企业决定是否进入一个产业,主要是着眼于利润的追逐和市场的成长性;从区位上说,企业在面对不同区位市场时也存在一个选择问题。一般说来,发达国家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对新进企业来说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遇到的进入障碍就要比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大得多。新进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是选择投资于发达国家市场还是周边相邻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其考量的因素也不一样。因此,进入障碍体现出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在产业上的进入障碍,一是不同区位市场上的进入障碍,而前者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后者则是本文需要系统探讨的问题。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使潜在的进入者进入一个产业变困难的因素即为进入障碍。然而,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Bain最早提出进入障碍概念之后,定义为“一个产业中原有企业相对于潜在进入企业的优势。这些优势体现在原有企业可以持续地使价格高于竞争水平之上而又不会吸引新的企业加入该产业”[12]。而Stigler则认为进入障碍是“一种生产的成本,这必然是产生寻求进入该产业的企业身上,而已经在该产业的企业则不会产生”[13]。弗格森定义为“是使进入者不能获利的因素,而却允许原有企业设置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维持获取垄断利润”。Caves和Porter认为进入障碍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耐用资产的专用性[14]。Bork认为任何阻止进入的因素都是进入障碍[15]。Brozen曾定义进入障碍是一种计划的或人为的障碍,这些障碍是政府为了提高效率或福利等“良好”的愿望而设置的[16]。Weizsacker定义进入障碍是一种生产成本,是在位企业不需支付,而由新进入者承担的成本[17]。我们认为,进入障碍就是阻止新企业进入的所有因素的集合。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进入障碍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测算。一种是通过比较新进入企业与原有企业利润函数件的差别来反映。假设进入前原有企业的产量水平为x*,可获利润的贴现值为π1(x0);进入后新企业的最佳产量水平为x*,它可获利润流的贴现值为π2(x*),如果下式成立则说明存在进入障碍:

即使新进入企业很想进入,但进入后无利可图。π1(x0)与π2(x*)之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

上式第一项是在同样的均衡产量水平条件下新进入企业与原有企业利润函数的比较,而第二项是新进入企业在不同产量水平下的比较。由于利润是收入R(x)减成本C(x),因此上式右端第一项,即按进入前均衡产量x0计算的利润π1与π2之差,在下面两式中任一式成立时都会出现:

前者代表成本差异,后者代表绝对成本优势,它们同时意味着原有企业需求曲线无论在任何水平上,都位于新进入企业所对应的需求曲线之上,或者说原有企业的成本曲线总是位于新进入企业的成本曲线之下。但是企业必须分享进入后的市场,因而进入后各个企业 (包括原有企业和新进入企业)的产量可能比进入前原有企业要少,即x0>x*[18]。
另一种测算方法可以通过价格的扭曲度可以用来衡量进入障碍的程度。因为某一产业的进入障碍越高,新企业进入也就越困难,产业内的企业也就越少,从而越容易形成垄断,而垄断的普遍意义是对供给的控制,控制供给也就控制了价格[19]。即垄断使价格和价值偏离,产生垄断利润,所以价格的扭曲度可以用来衡量进入障碍的程度。用R表示垄断价格与竞争价格差额同竞争价格的比率R=其中,p0是不存在进入障碍条件下的价格 (充分竞争),p是垄断价格,在撑起的情况下,垄断者能够接受的竞争价格以上的溢价来度量进入障碍,R值越大,价格的扭曲度越高,进入障碍也就越高。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也可以用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比率来度量由垄断产生的市场力量[20]。
此外,进入障碍还可以用产业超额利润来度量。设p为产业的价格,为产业的平均成本,是社会平均利润率,Δp'为产业的超额利润率,则越大,则超额垄断利润越多,进入障碍也就越高。进入障碍还也可以用该产业最高阻止进入价格高于该产业平均成本的百分比的大小来测定。所谓最高阻止价格是指能阻止新企业进入的价格的最高值。当企业把价格定在完全垄断下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水平 (MC=MR)时,新企业还是无能或无意进入这一市场,说明这一产业的进入障碍较高;如果企业把价格定在略高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竞争价格水平,就能有效地阻止新企业进入,那么这一产业的进入障碍就较低。此外,进入障碍还可以用一些描述性指标如经济规模与市场总规模的比例、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异化程度、绝对费用、产业和企业的专利特许权数量、交易和批准等各方面的制度规定等来衡量。
上述分析表明,市场本身会对新企业的进入带来进入障碍。而Demsetz则从政府的角度更为关注由政府限制带来的进入障碍,这一思想根植于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斯密认为进入障碍仅限于政府制定的进入限制条件,即只有政府干预才能产生进入障碍[21]。然而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限制进入障碍也会存在。如Rice认为真正的进入障碍是使价格能够超过社会最优价格而不引起进入的在位者拥有的一种资产,而且其社会价值是零的或负的。Vicker证明了即使在进入障碍为零的情况下,进入者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面临负的进入外部性[22]。这种外部效应为:

其中,p0和p分别为进入者进入前和进入后的价格,H0和H分别为进入前和进入后的赫芬达指数 (Herfindahl Index),π为进入者的利润。如果厂商的分布是均衡的,则进入的外部性是:

对于具体的行业来说,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农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服务业是容易进出的,而在一些制造业、采矿业和某些受限制的行业进入就困难多了[23]。
二、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及行业分布:实证分析
前已述及,虽然中国企业在20世纪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在总量上增长较慢,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取得了爆发式的增长。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对欧洲、北美洲投资快速增长,其中对欧洲投资33.5亿美元,增长282.8%;对北美投资15.2亿美元,增长3.2倍;2010年我国对澳大利亚29.3亿美元,同比增长20.5%;欧盟21.3亿美元,中国对除卢森堡外欧盟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97%;美国13.93亿美元,同比增长81.4%;日本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20%。从存量上看,2010年中国对发达国家 (地区)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9.4%,比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 (参见表1和表2所示)。

表1 2003—2009年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 (地区)直接投资情况 单位:万美元

表2 2006—2010年中国对主要发达国家 (地区)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的变化趋势 单位:亿美元
从中国逆向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对欧盟和美国逆向投资的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别。从欧盟来看,2007年的行业分布从高到低排列为金融业 (39.4%)、采矿业 (19.2%)、批发和零售业(11.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6%)等,美国则为制造业 (53.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6.2%)、批发和零售业 (1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1.9%)等;2008年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为制造业 (35.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7.4%)、金融业 (18.2%)等,而美国则为金融业 (46.1%)、制造业 (17%)、批发和零售业 (14.6)等;而2009年对欧盟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8%)、制造业 (7.4%)、金融业 (7.1%)等,美国则为制造业(41.7%)、金融业 (15.5%)、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探业 (13.8%)、批发和零售业(13.7%)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中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建筑业的投资虽然所占份额不大,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8.8%、3.6%和2.2%、1.2%,但在对欧盟的投资中则未能在这两个行业进行直接投资。由此可见,中国逆向投资的行业分布不仅在不同的国家 (地区)不尽一致,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年份也有变化。

表3 中国企业对主要发达国家 (地区)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单位:万美元
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有以下显著特点:第一,起步较晚,发展迅速。从1979年11月中国企业在日本合资开办第一个合资公司“京和股份有限公司”算起,仅仅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中国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前苏联、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21世纪以来,中国企业的逆向投资发展迅猛,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势而上。第二,跨国并购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逆向投资方式。毕马威发布的2009年度《新兴市场跨国并购交易研究》(EMIAT)显示,中国首次超越印度,在收购发达经济体资产的活动中表现最活跃。澳大利亚最受中国企业青睐,共达成35宗并购交易,占总量的18%;其次是美国,完成交易16宗,占总数的8%。在并购金额方面,大部分中国投资流向澳大利亚,总计达到280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1/5,而且并购交易绝大多数集中在金属和采矿业 (占总数的69%)。在中国企业的十大并购目的地中,七个为发达国家,吸纳了交易总额中81%的资金。2010年中国以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3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40.3%,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第三,中国逆向投资在不同的国家 (地区)和年份行业分布不均衡。这既受到中国企业既有的竞争优势的限制,也受到东道国政策变化的影响。
三、中国逆向投资面临的障碍分析
在中国逆向投资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失败的案例,如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公司、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联手收购3COM公司、中铝与澳大利亚力拓的“世纪大交易”、腾讯竞购ICQ、中化集团与新加坡淡马锡联手收购加拿大钾肥、华为竞购摩托罗拉、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上海光明食品收购美国健安喜股权和法国优诺公司股权案等。据英国《经济学人》数据,2004—2009年,5 000万美元以上的中企并购案中,共有22宗收购失败案,其中21宗发生在发达国家。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 (指已宣布的跨境交易被撤回、拒绝或听任其过期失效的比率)全球最高,达到12%;2010年,这一比率虽降至11%,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而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企业。
在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高的失败率?这其中既有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也有发达国家市场本身存在的进入障碍与发达国家政府人为的因素。
从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引人瞩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占一半,其中25家来自中国香港,15家来自中国台湾省,10家来自内地;在1995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中国只有3家企业上榜,2000年增加到了10家,2010年达到了46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达到了世界第三,并有3家中国内地企业进入了前10位。但在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过程中,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企业自身实力较弱、国际化经营与管理经验不足、国际化人才短缺、并购后的整合 (PMI)能力欠缺、海外发展战略规划缺失以及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横向沟通与合作,单兵作战,甚至相互拆台等先天不足问题。从中国政府层面,存在着多头管理、对外投资服务功能不完善、境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缺失、投融资与财税政策等配套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从发达国家市场本身存在的进入障碍来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表明,贝恩的定义中进入障碍包括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别化优势、融资方面的优势等。后来的学者将进入障碍的内涵大大扩展,包括专利的保护、政府对进入的限制、广告的效应、稀缺资源的控制和信息流动的速度等。另外,最近的研究更强调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作为增强先动者的市场防御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微观领域或企业水平层次上强调进入障碍是在位企业比潜在进入者所具有的内在竞争优势,如波特区分了六种不同的进入障碍: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消费者转换成本、必要资本量、政府政策和进入分配渠道。[24]就发达国家市场来说,发达国家市场明显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因为发达国家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市场容量大,机制健全,产业或行业成熟度高,市场集中度也高。对于发达国家市场上现存企业来说,都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机制而生存下来的,本身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因此,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一个发达国家的市场时,它不但需要面对与在本国时全然不同的经营环境、制度规则和文化习俗,而且要面对比在本国时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其他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企业相比将面临着一种明显不利的竞争地位。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企业要想进入,自然会面临比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更多的困难和障碍。这些障碍包括:(1)结构性进入障碍,这是一个行业自然存在的进入障碍,包括: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障碍、必要资本量障碍和产品差异障碍等;(2)行为性进入障碍,这是由原有企业为阻止新企业进入而主动采取的相应策略性行为而形成的,包括:扩张生产能力、产品扩散、掠夺性定价等;(3)政府有关法律和政策限制。这些法律与行政管制可分为常规性的和临时性的两大类。常规性的法律与行政管制是指发达国家政府对于某些行业的政策优惠和补贴,出于产业布局、经济发展规划、环境保护和安全等角度政府对有些行业的进入限制等;而临时性的法律与行政管制包括近年来发达国家出于政治利益考量人为设置的一些临时性障碍,如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这一正常的商业行为政治化,纷纷采取知识产权诉讼、反倾销、贸易壁垒、国家安全审查等法律和行政手段人为地阻止,特别是近期美国参议院通过人民币汇率法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又一个新动向。
应该说,结构性进入障碍是行业自身存在的障碍,行为性进入障碍是行业内存在的企业的一种自发性行为,这两者都是新进企业在进入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而对于发达国家人为设置的法律与行政管制特别是一些临时性的障碍,既需要政府间双边与多边谈判甚至仲裁来解决,也是企业开展逆向投资需要考虑和规避的问题。
四、促进中国企业逆向投资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提高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战略意义的认识
前已述及,逆向投资对于后起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优势是一种更有战略意义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来说,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战略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在企业层面,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有助于充分了解和熟悉国际规则、迅速赶超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增强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力,有助于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企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企业必须经历发达国家市场的“历练”才能最终成长为跨国企业。在国家层面,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拉近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最终实现由技术的“追随”到技术的“赶超”;通过对不同产业或行业的学习与追赶,进而形成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竞争力,最后形成国家的竞争优势。特别是,通过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还可以实现战略性资产的寻求与储备。
(二)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企业逆向投资中的重要作用
政府在促进逆向投资中的作为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健全机构,加强管理。目前中国仅设立了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制度,尚未包括对中国企业重大对外投资活动以及入境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其功能类似于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以及加拿大和德国的相应监管机构等。二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管,加强政策扶持和信息服务。包括建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体系等,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优先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逆向投资。三是为企业的逆向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国家在财税、信贷、投融资、外汇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为了进一步增强对外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应尽快设立对外投资发展基金、重点产业对外投资基金等,构建和完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基金支持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来说,政策环境的改善显得尤为重要,必将进一步促进逆向投资的发展。
(三)加深对发达国家市场与政府的认识,完善并购模式,规避投资风险
1.加强对发达国家市场环境的认识,有效规避市场以外的进入障碍。首先,前已述及,发达国家市场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市场而言比较成熟,市场容量大,机制健全,行业成熟度与市场集中度高。从技术水平上讲,发达国家市场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学习型”FDI。其次,不同区域的发达国家市场也存在区别。典型的区域如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其市场本身与产业、政策环境也明显不同。比如,相比美国,欧洲的传统产业比较壮大,新企业容易进入,但工会力量强大;而美国政府支持在新能源和环保等领域合作,可占政策红利,但优势行业如航空、军事等很难向中国企业开放,另一些行业则比较尴尬,比如钢铁业、制造业、汽车业等,基本都是黄昏产业。再次,正确认识不同发达国家的法律、文化和政治环境。比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也很强,而英国虽然历史一样悠久,但是包容性不如其他国家;而美国是法律潜规则最大的国家,并购的法律成本最高,且美国的地方法规也不尽一致,并购时应还要遵守各个州的法律法规。
2.充分认识发达国家市场存在的投资风险,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与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相比较,是一种高成本、高风险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而言,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就小得多。从近年来部分开展逆向投资企业屡屡受挫的情形来看,目前对发达国家的跨境并购所面临的风险除正常的进入障碍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类似于“国家安全审查”之类的政治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风险。对于这些风险和障碍,中国企业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并采取灵活的措施予以应对。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境外逆向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1)重视逆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通过科学决策规避投资风险;(2)完善开展逆向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加强投资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3)构建对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4)完善对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的功能等。二是完善并购模式,灵活应对风险。比如,采取联合投资的方式进行海外并购可以弱化政治背景强化商业目的,利用优势进行互补并平衡风险,而这种特点的跨境并购投资联盟相对于以往的单独企业投资,并购成功的机率更高。这种“抱团出击”的好处除上述几个方面外,还可以有效降低并购成本。
(四)充分发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在逆向投资中的作用
企业最终是市场的主体。在中国企业的逆向投资过程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企业自身。因此,中国企业能否顺利地开展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活动,最为关键的环节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能否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主要包括:(1)制定符合企业特点的国际化战略。近年来一些企业逆向投资失败的案例表明,一个明确并切实可行的国际化战略尤为重要。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决定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发展态势。一般说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海外设厂,生产本地化,如海尔;第二种是自有产品直接出口,如华为和中兴;第三种是并购国外企业,如联想;第四种是产品贴牌出口,这类企业以浙江温州企业为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展了跨国并购活动,既有成功的案例,而失败的案例中多数与企业采取了不符合自身特点的国际化战略相关。(2)大力开展研发活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国际经验表明,跨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除了依靠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与精湛的工艺设备提升外,更主要是依靠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的。相对而言,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应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机制,大力增加对跨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投入,还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培育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3)增强国际经营管理经验,加速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在中国企业的逆向投资活动中,主要的障碍还来自于企业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的不足与缺乏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因此,中国企业应通过多种方式,下大力气开展国际化经营,一方面可以不断积累和增加国际化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可以发掘和培养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才,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1]Oviatt,B.M.,McDougall,P.P.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5,36(1).
[2]Zhou,K.Z.,Tse,D.K.,Li,J.J.Organizational Changes in Merging Economies:Drivers and Consequen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6,37(2).
[3]Yamakawa,Y.,Peng,M.W.,Deeds,D.L.What Drives New Ventures to Internationalize from Emerging to Developed E-conomies?[J].Entrepreneurship:Theory & Practice,2008,32(1).
[4]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R].
[5]张纪康.论跨国直接投资中的行业进入障碍及其对策[J].世界经济,1992,(9).
[6]江勇,余海丰.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障碍分析[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6).
[7]韩世坤,陈继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障碍因素分析[J].改革,2001,(4)
[8]李优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性障碍与制度创新[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2,(3).
[9]覃晓雪,李灵稚.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及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03,(7).
[10]赵燕.对如何跨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障碍的探讨[J].国际贸易问题,2003,(12).
[11]朱玉林.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障碍及对策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5).
[12]Bain,J.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13]Stigler,G.J.The Organization of Industry[M].Homewood,Ⅲ:Richard D.Irwin,1968.
[14]Caves,R.E.,Porter,M.E.From Entry Barriers to Mobility Barrier:Conjectural Decisions and Contrived Deterrence to New Competi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91(2).
[15]Bork,R.H.The Legislative Intent and the Policy of the Sherman Ac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7,(9).
[16]Brozen,Y.Entry Barriers:Advertising and Product Differentiation[A].Goldsmith,Mann Weston.Industrial Concentration:The New Learning[C].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4.115 -137.
[17]Von Weizsacker,C.A Welfare Analysis of Barrier to Entry[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11(2).
[18]Geroski,P.A.Market Dynamics and Entry[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19]张伯伦.垄断竞争论(中文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20]Koch,V.J.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Price[M].Prentice - hall,1980.62.
[21]Demsetz,H.Industry Structure,Market Rivalry and Public Policy[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3,16(1).
[22]Vicker,J.Concepts of Competition[R].Oxford: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5.
[23]丹尼斯·W.卡尔顿,等.现代产业组织(中文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4]Porter,M.E.Competitive Strategy[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