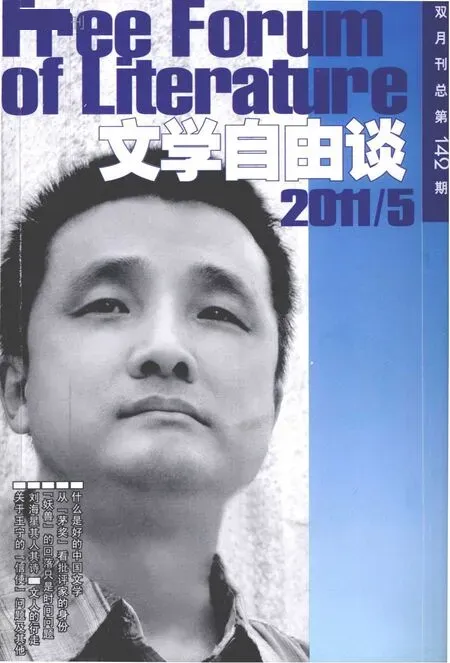文人的行走
●文 李国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来都是中国文人的雄心抱负。但做到者,很少很少。
古之文人,读万卷书易,行万里路难,今之文人,随便拉出一个,行过万里路者,甚至行过十万里路者,不算稀奇。但读过万卷书者,或退一步,读过千卷书者,恐怕要像孔乙己数碗里茴香豆那样,发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感喟了。
现代人还有读书的欲望吗?今年8月份,英国伦敦的骚乱,打砸抢烧,一片狼藉,商铺住宅,无一幸免,惟有书店却无暴徒光临,完好无损,这倒不是什么英国绅士精神文明的体现,而是说明书籍阅读的式微,不肯读书,不屑读书,已是具有全球性质的风气。同样也是今年8月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盅,第一名为张炜的《心在高原》,因其全书长度,超过法国作家普罗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两倍还多(说实在话,至今我也未能读完这部太长的外国文学名著)。按照时下的厌倦读书的习惯,读者质疑评委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否读完这部刚刚出炉不久,还带有油墨气味的长篇巨著,遂而有所发难,似乎也不应责怪。因为纸媒的传统阅读方式,曾经有过如饥似渴的热衷年代,早已是翻过去的旧黄历了。读者以当下浮躁的普遍心态,加诸茅奖评委头上,正如伦敦的骚乱群众,什么店面都砸,什么东西都抢,独独不砸书店,独独不抢书籍那样,认为评委也许难能免俗,会在阅读参选作品时,产生审美疲劳,产生厌烦反应,产生缺氧眩晕,产生逃学情绪,这当然可能是等而下之的人,对等而上之的人的误解了。
纸媒的阅读逐渐成为负担,实在令人悲观,有朝一日,当手机阅读,网络视听,电子传媒,IT事业,更加物美价廉,更加普及广泛以后,出版社是否会停业?图书馆是否会关门?人们捧着厚若城砖的大部头,一页一页翻阅起来,会不会被看作很冬烘的事情?也许到了那时,谁还读长篇小说,谁还订文学刊物,如同满清晚年的八旗子弟,溜鸟笼子,闻鼻烟壶,闭着眼睛听戏,捏着嗓子唱曲那样,恐怕是相当没落的贵族,才会干得出来的无聊消遣。
长此下去,我想,总会有笑不起来的这一天。
不过,文学是常青树,有人类在,就有文学在,就文人而言,只要文学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概是废止不了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平心而论,所谓“十年寒窗”,“手不释卷”;所谓“行走江湖”,“浪迹天涯”,古之文人,做这两项事,比之今之文人,不知要艰难多少倍?
第一,古人读万卷书,谈何容易?印刷术未普及前,书籍是以手抄本形式流通在少数人手中,线装书出现以后,一般读者方敢稍稍问津。但是,雕版刻印,成本过高,书价昂贵,想读书的人未必能买得起想读的书。而且,民国以前,可供借阅的公共图书馆,极其罕见。所以,拥有万卷书的古人,或者,虽不拥有,却可能读到万卷书的古人,为数极少。
第二,古人行万里路,那就更不容易了。除非前呼后拥的达官贵人,可以做到乘车骑马,足不履地,除非腰缠巨金的豪商巨富,可以做到轿抬船载,自由自在,天下再大,路途再远,对他们来讲,都是不在话下的事。而那些一无力气,二无银两,三无跟班,四无帮衬的清寒文士,端的十分可怜了。胼手胝足,翻山越岭,天寒地冻,涉水渡河。靠两条腿,走崎岖陡峭之路,赖一双脚,经蛮荒不毛之地,能够长年累月,坚持不懈,而不变初衷者,也是为数极少。
正是这两个“极少”,所以,对旧时大多数文人而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景,难以实现的奢望而已。
但是,自有文学以来,从最原始的,最稚拙的“杭唷杭唷”派,到后来神驰八极,心游万仞,云蒸雾蔚,龙蛇变化的古代,而后近代,现代,而后当代的文学,推溯其产生的本源,无非三,一曰读万卷书,获得的间接知识,二曰行万里路,体验的直接感受,三曰上帝恩赐给这个作家或多一点,或少一点的美学天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才华。千古以来,关于文学的产生,说法多端,理论繁复,解释各异,侧重不同,但这三合一的文学构成方式,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所以,古代文人之中的有出息者,都是把读可能读到的书,行可能行及的路,列为自己的人生指南。也许读不到那么多书,可坚持要读,也许行不到那么多路,可坚持要行,这是绝不动摇的。因为,不读万卷书,不可能有大见识,不行万里路,不可能有大胸怀,已成大家的共识。恃方寸之地,守株待兔,写不出气势磅礴的文章,持一己之见,戴盆望天,成不了厚积薄发的学问,更是历史的定论。所以,尽可能的读书,尽可能的行路,遂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精神。这其中,更有一些极具开创精神的先行者,始终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视作与生命等同,并且终生追求的事业,而造就中国文学的辉煌。在这支勇敢者的队伍里,汉代的司马迁同志,毫无疑义是排在最前列的先行者。
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写家”的地位,迄今为止,尚无一个中国文人超越。虽然我国盛产文学自大狂,但迄今为止,还无一个傻帽,跳出来说我比太史公强。虽然在他以前,有过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说法,但这些远古时期的宏大典籍,也只是说法而已。在这些说法没有坐实之前,他所写的这部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总三千余年史事,计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余字的《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开创意义的“第一大书”。
这位“第一写家”,这部“第一大书”,对于后人的启示意义,莫过于他一生从来不曾停歇的行走了。文学始自脚下,真正的文学则更是作家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他的《史记》,就是一部走出来的书。司马迁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读书,壮游,写作。而他的壮游,从20岁起直到60多岁告别人世,始终没有停止过。
他的壮游,可分三类,按当下旅游行业的习惯用语,一是个人游,二是出差游,三是随团游。可我们都知道,他个人游的时候,他不是大款;他出差游的时候,他不是巡按;他随团游的时候,更可怜,则是跟头把式,鞠躬尽瘁,伺候主子,戴罪立功,属于留用察看,以观后效,帽子拿在手中,不老实就给你扣上的随从人员。想到这里,你就会了解司马迁的行走,其实,快乐很少,苦痛更多。尽管如此,他的使命感使他不能停下他的脚步,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要走遍他能走到的所有地方。我们读《史记》,字里行间,时不时能见到他行走匆匆的身影,行文走笔,断不了能听到他有感而发的声音。
说实在的,读《史记》时,给你留下最强烈印象者,就是这位同志。姓司马,名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约生于公元前145年,约死于公元前90年,或再后一点。因为这个深刻的读书感受,我相信他是一位极自尊,极自重,极自信,也极自负的文人。凡这类把自己当人,而不当狗,当人很痛苦,他也要当人,当狗很快活,他也不当狗。所以,若仅止于山呼万岁,侍从听喝,讨好巴结,努力表现,凡人臣都具有的那一套马屁哲学,他也不是不可以弯腰屈背。但将他诬陷成一个罪人,很残忍地将他阉割成一个很难堪的“刑余之人”,“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在“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的处境下,一方面,“佴之蚕室”,一方面,“闟茸之中”,一方面,“待罪辇毂”,一方面,“尊宠任职”,这个汉武帝刘彻简直像耍猴似的玩弄了他,折腾了他。
“尊宠任职”,语出班固《汉书》,他在《自序》里只字未提,很显然,这使他更痛苦。如果说这部大书,是他走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他忍辱负重,备受熬煎,磨炼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含辛茹苦,为什么要这样忍气吞声,为什么要这样受王八蛋折磨,听王八蛋摆布,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了,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到底,他为了自己的这部大书,或者,为了文学,才“就极刑而无愠色”的被腐,用老百姓的话,这个汉武帝既劁了他,让他无地自容,还要他来担任要职,现身朝廷,而受到“重为天下观笑”的耻辱,对他发自心底的“悲夫悲夫”的哀叹,能不一掬同情之泪么?
我也曾经做过共和国的三等公民,但属于等而下之那一拨的。在那些年头里,持绝对颓废姿态,抱死狗一条之心,不思振作,不求进步。阿Q说过,你骂我是虫豸,我比虫豸还虫豸,总行了吧!所以,对司马迁逆境中的自强,磨难中的奋斗,坚决不做虫豸,不但不做虫豸,还要当圣人,实在令我五体投地的佩服。为什么佩服?因为我做不到。不过,我也为这位中国第一写家设想,同志哥啊,人家都不爱你了,你还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所为何来?割掉你的卵子,让你无法做人,你还含垢忍辱继续你自己的事业,所为何来?浅薄如我,很难理解,你干嘛这么执着呢?庸俗如我,从来抱着不让我做人,我做狗行不行?不让我做狗,我做虫豸行不行的哲学,求生图存,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思考。曾经写过一篇《司马迁之死》,表示过这层意思,去你妈的刘彻,老子不干了,又如何?后来,一些明公颇不以为然,这就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如果,你的卵子被割,如果,你的卵子虽未被割,但精神上的卵子给割掉了,就会懂得历史固然不多你一个,怕也不少你一个。你把你当盘菜,人家不伸筷子。其实,想开一点,即使没有司马迁,没有《史记》,中国不照样是中国,地球不照样转下去。
也许,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伟人的行止,不能按常人的逻辑理解。使命感这东西,了不起,但使命感这东西,也很害人,老百姓是玩不起的。我们从《太史公自序》里,读到其父司马谈对他的临终交待:“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同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接下来,便是《史记》特有风格的“太史公曰”,在这篇《自序》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同志对于自己的期勉,就把“第一写家”架到了痛苦的高度上。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矣。”看起来,为了家族荣誉,为了承祧史业,为了兴灭继绝,为了立身立德,“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就应该是他司马迁了。圣人是好当的嘛,周公旦从政治上奠定了统一的中国,孔夫子从精神上巩固了文化的中国,那么,司马迁赋以自己的使命,就要从历史上弘扬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以为史鉴。你想过吗?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英主,我们的领袖,往哪里摆?
上大夫壶遂和他讨论过:“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他回答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这就是中国文人热土难舍的苦恋情结了,尽管他被宫、被腐,被劁,但他为了这份承诺,以及为此承诺必须体现出的一个男子汉的担当,以及为此担当必须付出的自我牺牲,成为他一直走下去,走到这部大书的完成,走到最后他这个人的不知所终的全部动力。
赞叹的同时,也不禁惭愧,当代中国文人,若有司马迁精神之万一,当代中国之文学,将不知达到如何辉煌的地步?住高级宾馆,乘豪华轿车,吃中西大餐,有美女为伴,风花雪月是可以的,游戏文字是可以的,骗稿费,捞奖金,混世界,闯江湖,也是可以的,但是,想写出生活之真实,或真实之生活,也难。
司马迁的个人游,为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这年他20岁。他在《自序》里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一直到次年,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元朔四年),这年他21岁。他才“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因为绕了圈子,走了弯路的缘故,估计用了两年时间,走了不亚于红军长征的两万五千里路。
汉代的太史令,六百石的下大夫,不是什么肥缺,估计司马谈不可能资助儿子太多旅费,汉代用五铢钱,分量要比秦半两轻,但司马迁也背不了许多,因为古代人外出,首先要带足干粮。所以,这次绝对自费的旅行,必然也是一次寒酸的旅行。很多研究者弄不清楚这位从长安出发的旅行者,为什么不顺河而下,径驱齐、鲁,顺路江、淮,然后,由浙而湘,由鄂而豫,再回长安?而是先南后北,转了一圈,再回山东朝圣,最后经河南,湖北,绕回长安。是司马迁失去方向感,还是他的指南针被消了磁?窃以为司马迁这种既费时,又费力的旅行安排,恐怕其中有更多的经济考虑,是不是因为有搭顺风车的可能,才不得不随人家更改路线。
从下面摘录出来的部分“太史公曰”,我们知道他足迹所至。譬如: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也!”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适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孔子世家》:“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也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之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留侯世家》:“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公子列传》:“吾过大梁之城,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若失矣。”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丧,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姓,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游侠列传》:“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
……
从以上只言片语之中,可以看到司马迁为了写这部大书,搜集资料,采访事主,实地考察,务求确证,真是下了大本钱,用了大力气。那时没有高铁,没有动车,没有民航,也没有A6或是A8,先是溯江而南而西,再是沿河而东而南,走了不少冤枉路,费了不少旅游鞋,但对真正的作家来讲,吃苦头的同时,也带来甜头。他走州过县,查访探询,登高望远,思今抚昔,不但亲历其地,亲访其人,亲触其物,亲证其说,而且,依据实际,核对史料,修正错谬,纠偏传闻,这两年或两年稍多一点的行走,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其日后的著书立说,夯实了最牢固的基础。
司马迁的出差游,那就快活得多,公款消费,出手阔绰,随扈众多,高干待遇。一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时年35岁;一是次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时年36岁。因为他得到一次升迁机会,由宫廷侍卫的郎中,提拔为郎中将,秩比两千石,相当于中央警卫团的正师级领导干部,遂属于具有军事行动的外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称得上风光的日子。司马迁在《自序》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朔方)报命。”看他用字措词的“西征”,“南略”,一洗穷酸文人的瘪三相,可以想象,骑着高头大马,前面警卫开道,头载金绦头盔,肩扛两杠三豆,那是何等威风的了。
正如明人黎遂球《莲须阁文集》序中说过的:“文章以气骨为主,而词采音吐,犹夫人之依体质以行者。史称司马子长文,有名山大川之气。”胸中有千丘万壑,笔下有滚滚风雷,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认识深度,视野广度,就不是那些功夫在嘴巴,成就在炒作,名声在吹牛,地位在哄抬的文人,所能企及的了。司马迁的文学人格,由于有这样一个走得更开阔,看得更全面的机会,其品味,其境界,其情操,其趣识,也在大大提升,他的高瞻远瞩的胸怀,高屋建瓴的大气,综览全局的能量,统盘驾驭的魄力,已非太史令那样一个只知唯唯诺诺的官员,所能荷载,而是孔子五百年后“高山仰止,景行行至”的又一人,才具有的襟怀。
从《河渠书》中,我们读到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关爱:“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高中化学教学并非是盲目开展的,每个课时都是有对应的教学目标的,但是过去在明确教学目标时,目标的构建十分混乱和零散,这便致使了化学教学工作无法有序开展.该种状况在运用系统思维理论得到了有效改善.基于系统思维理论下,教师在构建教学目标时,会从教学整体着手,通过细致分析教学内容与任务,找出课时间的联系,随后依据该联系构建教学目标,这样一来,每个课时的教学目标间存在内在关联,全部教学目标都能融合到一起汇聚成一个整体,如此教师在具体教学中便能够保证教学效果达到最佳.
从《蒙恬列传》中,我们读了他对历史的思考:“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
在中国文学界,有的作家,只能小打小闹,有的作家,敢于大开大合。小打小闹的作家,写不来大场面,因而捉襟见肘。大开大合的作家,往往失于粗疏,有欠精致。但在司马迁笔下,就以《项羽本纪》里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为例,场面之大,人物之多,故事之复杂,情节之起伏,结局之惊心动魄,生死之瞬息变化,至少司马迁死后两千年来,尚无人能出其右。而他对于文字的运用,对于语言的发挥,也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地步。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过:“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也。’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又说:“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接下来,就是司马迁随着汉武帝的巡幸游,在他未受到宫刑前,曾经以马崽身份,马前鞍后,共11次,随刘彻出巡的大队伍行幸各地。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时年33岁。至雍,至汾阴,立后土祠,由荥阳、洛阳回长安。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时年34岁。至陇西,至崆峒,至甘泉。《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崆峒。”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时年36岁。平定西南夷后至朔方报命,后随帝至北河、桥山、缑氏、泰山、碣石、辽西、九原。
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元封四年),时年39岁。至雍,北出萧关,至代,复渡黄河至河东,祠后土。《五帝本记》曰:“余北过涿鹿。”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时年42岁。至泰山,东临渤海。
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二年),时年43岁。由夏阳渡河至河东。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时年44岁。至海上还,随封泰山。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时年45岁。冬至回中。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天汉元年),时年46岁。至甘泉。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时年47岁。至东海,还至回中。随后,因李陵案起,“遂下于理”,被坐牢法办了。
受到残忍的宫刑,密闭于不透风的蚕室中养伤结痂以后,晚年的刘彻实质上已心理变态,接近于精神崩溃,对其文章,不得不敬畏,对其所为,不能不切齿,所以,表面上以示尊宠,继续任用,实际上让其出丑,丢尽脸面,先后共5次,坚持要让这个被腐的司马迁与之同行,任人哂笑。
公元前95年(汉武帝太始二年),时年51岁。复至回中。
公元前94年(汉武帝太始三年),时年52岁。至东海、琅邪,登之罘,浮大海。
公元前93年(汉武帝太始四年),时年53岁。至雍,至安定、北地。
公元前92年(汉武帝征和元年),时年54岁。随帝还至建章宫。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时年55岁。至甘泉。(以上均据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
在这以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写家,便无影无踪地从人间蒸发了。一说,濒危的刘彻害怕司马迁千秋万代的文字,使他成为永远不得翻身的唾骂对象,遂将他秘密处决了。一说,写完了这部大书的司马迁,将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后,便消失于深山老林之中,开始纯属于个人的,自由的,与任何王八蛋都无关的文学行走。
在中国,读万卷书,没有一个文人能比得上司马迁,在中国,行万里路,也没有一个文人能比得上司马迁。所以,对这位“第一写家”的最好纪念,莫过于再一次,或再再一次重读他的“第一大书 ”了。
不读《史记》,你有脸称自己为中国文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