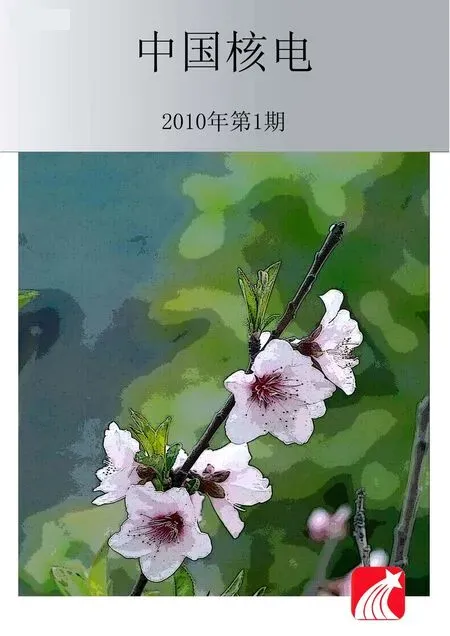核电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侯惠群,吴 瑾,白云生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北京100048)
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其实质是争取和维护国家的发展空间与竞争优势。国际气候变化斗争正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核电能够有效减排温室气体,伴随着我国核电的快速发展,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作用和意义也逐渐增强。
1 国际气候变化的斗争
1.1 国际气候谈判主要历程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多年艰苦谈判,形成了3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即《气候公约》(1992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和“巴厘路线图”(2007年)。
《气候公约》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公平的基础上,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尽各自能力承担义务,它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应率先采取行动。《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为实施《气候公约》迈出的重要一步,它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00年之后的减排义务及时间表,并提出了3种境外减排的灵活机制,同时决定不为发展中国家引入除《气候公约》义务外的任何新义务。“巴厘路线图”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中一座新的里程碑,它强调国际合作,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承担减排义务的范围,但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作了区分。
2009年12月7日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主要议题是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在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上。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虽然维护了《气候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做出了安排,但参会各方代表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基础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
1.2 主要国家的减排立场
参与气候谈判的诸多国家,因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利益而拥有不同的减排立场。
美国一直以来回避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不仅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且坚持以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承担义务作为其承担义务的先决条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
除美国外,欧盟作为气候变化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要求其他工业化国家承担与欧盟具有可比性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一定程度的减、限排行动。欧盟在2007年3月承诺,到202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20%。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国虽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但对实现承诺目标却持消极态度。印度、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样努力争取未来发展空间,但在近中期面临的国际压力较小。马尔代夫等全球气候变化中11个“最脆弱”的岛国组成联盟并发出联合呼吁,希望发达国家承诺2020年的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45%。
1.3 核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地位
在《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各种减排机制中,核电并不属于可行的减排选择。这是因为过去核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核电存在经济性、安全性、废物处理和防扩散问题,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首的支持者则指出,核电已经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安全性,废物处理和扩散问题也是可以解决和有效控制的,可以将核能作为候选能源技术,给予核电技术更多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全球变暖日益明显,减排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社会对减排进程缓慢普遍感到不满,强烈呼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此外,化石燃料价格快速上涨,而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持续上升,传统能源产业受到很大压力。同时,核电技术的不断发展,其清洁、经济和安全性能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核电的竞争力进一步显现,受到世界各国和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更多的关注。2000年,《气候公约》缔约方第六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表示,是否选择利用核能是各国自己的权利。2007年欧盟通过法案,将核电纳入控制气候变化的可行途径中。可以看出,核电在气候变化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
2 我国气候变化面临的压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能源消费引起的CO2排放。2007年,我国化石燃料燃烧的CO2排放量约为61.6亿吨,人均4.66吨;同年美国的排放量约为59.7亿吨,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为4.28吨。2007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5倍①数据来源:能源规划数据手册2009(国家能源局)。GDP为2000年不变价美元,采用汇率计算。。这意味着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人均排放低的优势也已丧失。不仅如此,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需求还将持续增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一直以来,我国在发展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1990—2005年,我国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下降46%。2009年9月22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目标。
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伴随着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高速增长。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被提升到全球安全的战略高度,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的重要因素,也将成为发达国家牵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正处于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必须争取必需的发展空间,包括必需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
3 发展核电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作用和意义
核电是技术成熟的可大规模提供电力的清洁能源,是我国未来能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电可以有效减少二氧化硫、烟尘、灰渣、氮氧化合物等污染,尤其在减排CO2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发展核电对我国改善能源结构、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就最有意义的减排CO2量对核电和煤电进行比较。
3.1 发电环节比较
核电站本身不排放C O2等温室气体。2008年,我国发电平均煤耗为325克/千瓦时,考虑到技术进步,预计到2020年我国平均发电煤耗为300克/千瓦时。由此计算,煤电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为946等效CO2克/千瓦时。
根据我国已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发展到4000万千瓦,按85%的容量因子计算(即年发电7500小时),届时核电的年发电量为3000亿千瓦时,同等电量的煤电要排放2.84亿吨CO2。仅考虑发电环节,发展4000万千瓦核电替代煤电,一年可以减排CO22.84亿吨。按照国家拟定的减排目标,2020年总排放量预计约为85亿吨②按照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949美元)翻两番,人口预计为14亿,单位GDP排放强度比2005年(1608克CO2/美元)下降40%测算。。由此,核电当年减排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3.3%。
如果进一步加快核电的发展,到2020年如果建成7000万千瓦核电,年发电量为5250亿千瓦时,同等电量的煤电要排放4.97亿吨CO2。仅考虑发电环节,发展7000万千瓦核电替代煤电,一年可以减排CO24.97亿吨,占2020年全国排放总量的5.8%(见表1和图1)。
3.2 全发电链比较
据有关单位研究计算,我国煤电链温室气体的排放系数约为1302.3等效CO2克/千瓦时;核电链排放系数为13.7等效CO2克/千瓦时③潘自强,等. 我国煤电链和核电链对健康、环境和气候影响和比较,《辐射防护》2001年3期。,核电链的温室气体排放只是同等规模煤电链的百分之一左右。

表1 只考虑发电环节,核电相对煤电的减排作用Table1 Only considering the sector of power generation,the emission reduction of nuclear power in contrast to coal power

图1 只考虑发电环节,核电相对煤电的减排CO2 作用Fig.1 Only considering the sector of power generation, the CO2 emission reduction of nuclear power in contrast to coal power
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将发展到400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3000亿千瓦时,核电链年排放CO20.04亿吨,而同等电量的煤电链要排放3.9亿吨CO2。发展4000万千瓦核电替代煤电,一年可以减排CO23.86亿吨,占2020年全国排放总量的4.5%。
如果到2020年建成7000万千瓦核电,年发电量为5250亿千瓦时,核电链年排放CO20.07亿吨,同等电量的煤电链要排放6.8亿吨CO2。发展7000万千瓦核电替代煤电,一年可以减排CO26.73亿吨,占2020年全国排放总量的7.9%(见表2和图2)。

表2 核电链相对煤电链的减排作用Table2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nuclear chain as compared to coal chain

图2 核电链相对煤电链的减排CO2 作用Fig.2 The CO2 reduction effect of nuclear chain as compared to coal chain
可以看出,规模发展核电可以为减排作出积极的贡献,到2030年、2040年乃至2050年,我国核电还会进一步大规模发展,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益处将会更多的显现出来。
4 措施建议
(1)积极推动核能纳入国际气候谈判的可行减排选择。
在目前的国际气候谈判中,核能一直被排除在可行的减排选择之外。但随着减排压力的日益增大,核能作为目前可大规模利用的清洁能源,逐渐显现出其发展优势和竞争力。我国是一个核大国,已经在核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储备方面拥有较好的基础,积极推动核能纳入国际气候谈判的可行减排选择,有利于增加我国在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也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澳等国对相关国际协议的参与。
(2)不断加强核能技术的自主创新,创建自己的民族核电品牌。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温室气体的核心是先进的能源技术。因此,围绕气候变化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能源技术的斗争。为了使我国在新一轮的技术竞争中保持前列,必须不断加强核能技术的自主创新,利用引进三代技术的契机加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创建自己的民族核电品牌。这样不仅可以为我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提供核心技术,为国民经济发展预留更大的空间;还可以向一些发展中国家输出核能技术和产品,维护和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
(3)建立和完善核能法律体系,巩固核能的地位和发展前景。
我国虽然已经提出“积极发展核电”的方针,又制定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却一直未能出台核能的根本大法《原子能法》,因此,核能的发展还是以政府指令为主,缺乏法律支撑。有必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核能法律体系,以法律的形式将核能在我国能源中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确定下来,为核能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4)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营造促进核能发展的政策环境。
将核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国家行为。国家必须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发达国家在用政策促进核能发展上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应积极学习和借鉴这些宝贵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开展促进核能发展相关政策的研究,为核能发展提供更加有益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