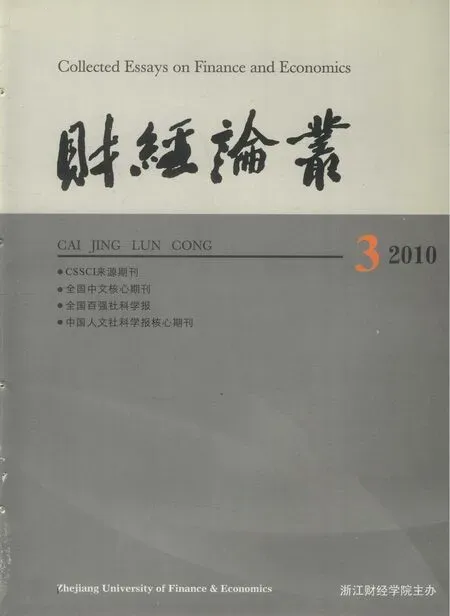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抑或分歧——以浙江为例
王跃梅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演进,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原本 “鱼米之乡”的粮食产区 (如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已转变为粮食主销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甚至出现了弃耕和抛荒现象。2010年中央 “一号文件”主题仍围绕持续七年关注的 “三农”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和稳定粮食安全。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一致抑或分歧?如何实现二者的协同?怎样界定政府适当管制?等等,这些是完成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过程中所需解决和研究的公共管理问题[1]。
粮食主销区人多地少、耕地稀缺,而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因此粮食生产并不是主销区的比较优势。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通过国内 (区际)贸易为主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更有利于改进土地资源配置。但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粮食的产需矛盾转变为供需矛盾,主销区粮食安全问题由自然风险向市场风险转化。粮食安全问题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溢出效应,主销区应确定粮食安全自给底线,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伴随的粮食问题。
一、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结合研究的专题文献虽不多,但细心研读一些经典文献仍会发现他们在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粮食问题,并且隐含着 “一致”和 “冲突”两种观点。李嘉图较早指出在农业停滞不前的情况下推动工业化会遇到粮食问题。刘易斯(Lewis,1954)、费景汉和拉尼斯 (Fei H.&RanisG.,1964)认为,农业部门存在 “零值劳动力”时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会造成农业总产出减少或粮食短缺[2][3]。舒尔茨 (Schulz,1964)、托达罗(Todaro,1970)以及乔根森 (Jorgenson,1967)等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对现有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不存在 “零值劳动力”,但从农业退出会导致农业 (粮食)生产的下降。到了 “拉-费模型(Ranis-Fei)”的第二阶段,农业部门存在 “隐性失业”,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农业产出水平将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下降,粮食安全问题将不可避免,即可能出现 “粮食短缺点”[4][5][6]。Rozelle等 (1999)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向且显著的[7]。而速水佑次郎 (2003)则认为,随着收入提高后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对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的反应程度变得越来越弱时,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要素应尽快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8]。Williamson(1988)认为劳动力迁移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9]。D.盖尔◦约翰逊 (2005)指出,中国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已经不低,但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存在 “内卷化”①20世纪50年代,政府为确保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劳动投入以应对粮食消费需求,将中国农业推向了 “内卷化”或 “高水平均衡”状态 (帕金斯,1984;黄宗智,1986)。或过密型增长的现象,因而要将农业劳动力降到总就业人口的10%甚至更少[1]。
以上文献中刘易斯模型等是建立在劳动力 “同质性”假定基础上的,本研究将基于劳动力的“异质性”假定。拉尼斯-费模型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与土地、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在乔根森模型中粮食只是整个农产品的代名词,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目前,即使在最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粮食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没有下降到零。托达罗模型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始终是正数,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不符。这些文献和论点为我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国内多数研究的视角是沿着两条平行线索展开的。一条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经历了总体描述阶段和专题深入阶段。蔡、都阳和王美艳 (2003)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曾做过很好的文献综述[10]。姚先国 (2007)精辟论述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演化问题[11]。林毅夫 (2004)指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长期、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将农业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12]。李实 (1997)研究了农村流动劳动力对城市产生的就业替代率仅为0.1左右[13]。赖存理 (2000)认为劳动力转移缓和了农村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增加了农民收入,反哺了农业[14]。白南生 (2008)和盛来运 (2007)认为劳动力外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不仅不会导致农业萎缩,而且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15]。另一条是对粮食安全问题的专题研究。马九杰等(2002)强调家庭与个人的粮食获取能力,即微观粮食安全[16]。王雅鹏 (2005)指出农民对收入增长速度和经营收入的预期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及粮食安全[17]。朱镜德 (2003)认为劳动力转移会引起耕地资源稀缺与利用不足 (粗放型经营甚至撂荒)并存,进而引发粮食安全问题[18]。周异和胡靖 (2008)指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19]。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无论从定量刻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定性研究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粮食安全问题,都为本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文献多是总体的研究描述,没有分粮食主销区和主产区来专题研究,对粮食安全的研究侧重于国家宏观层面。而从粮食主销区角度思考农村劳动力外流问题以及重视 “获得能力”的粮食微观安全层面正是本文的重点研究。
二、命题与实证分析
(一)“一致”和 “分歧”的命题
本文界定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是从农业劳动到非农业劳动,指 “居住在本乡 (农村户口),户口登记地在外乡 (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更多的是留在本地。我国粮食主销区的八省、市有人口二亿九千一百万,经济比较发达而耕地少,粮食种植机会成本高。2001年主销区实行粮食市场化后,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在面临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务农,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
1.分歧命题: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会产生粮食安全问题。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得粮食主产区的播种面积减少,粮食自给底线下降,主销区粮食对外依赖性很大,粮食市场呈典型的供求 “蛛网周期 (Cobweb Cycle)——发散型波动”和 “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决策困境。
2.一致命题: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会提高粮食安全度。由于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在耕地稀缺的粮食主销区,发展耕地密集的粮食生产并不是比较优势所在。因此,根据资源禀赋理论,为发挥比较优势,主销区农户会选择抛弃耕地而从事非农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要实现粮食自给,粮食获得能力的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是一致的。
(二)实证分析

图1 2000-2008年部分主销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单位:千公顷)① 根据浙江、福建、广东2009年的统计年鉴整理而得。粮食作物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广东数据中自2004年起含豆类,2006-2007年数据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后的调整数。
1.比较利益下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粮食生产自给底线。本研究的粮食主销区是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海南、广东、福建等7个省 (市)。1984年我国开始允许农民在自筹资金、自理口粮的条件下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破除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政策限制后,农村劳动力外流数量日益加大。2001年粮食主销区浙江等地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在放开粮食市场的同时,也取消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转而成为在流通的 “暗处”补贴,地方财政相应地减轻了负担。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受挫,加上当时的政策鼓励主销区少生产粮食,导致主销区种粮面积锐减,粮食大幅减产,自给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浙江、福建和广东是我国较早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沿海省市,粮食自给率均在50%以下,近年来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减少(见图1所示)。

图2 浙江省农村从业人员的变化情况② 根据2009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来强制性地配置资源,致使粮食生产和其他产业的比较收益差异没有凸现出来。实行粮食市场化后,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种植机会成本高,在发挥主销区的比较优势时,农户会选择抛弃耕地而从事非农生产,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以浙江为例,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2000年的2233.33千公顷下降为1271.63千公顷,减少了961.7千公顷,年均净减少120.21千公顷。从浙江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看,2006年粮食主销区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251.76万人,农村常住户 (在本普查区内居住一年以上)中外出从业劳动力为413.42万人,其中农业户籍外出劳动力390.18万人。
从图2可见,2001年前后的浙江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尤其显著,原因在于浙江率先实行粮食市场化后,取消粮食订购任务,农民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受比较利益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者急剧减少,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由于在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户间的土地流转还未有效进行,大多数农户选择了 “边打工、边种粮”的兼业型粮食生产方式,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下调,甚至出现了土地 “撂荒”情况。1998年,浙江粮食自给率高达82%,而目前已降至41.7%,原来的 “鱼米之乡”成了我国的粮食第二主销区。
与此同时,主销区粮食需求继续呈刚性增长。(1)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增加。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务工经商,浙江人口每年约增25万人,相应的口粮需求增加1.25亿斤。(2)农村非农产业仍是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258元,比2007年增加993元,名义增长率为12.0%,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外,实际收入增长6.2%,而全年纯收入的72.2%来自于非农产业。(3)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较大。2008年浙江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4%和38.0%,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比1978年的59.11%下降了近20多个百分点。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将带来粮食间接消费的较大增长,1998年浙江粮食自给率高达82%,而目前已降至41.7%,不到需求的一半。2008年浙江产需缺口依然在100亿公斤左右,粮食缺口大,对市场的依存度增加。因此,区域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需依靠全国乃至世界粮食大市场的供给来保障。
2.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经济增长和粮食获得能力的增加做出了贡献。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特殊产业,同非农产业相比,其生产成本递增较快,盈利能力较小,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粮食主销区一般经济较发达、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其粮食劳动生产率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就更大。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将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来自非农的收入 (农村劳动力外流效应)对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农村劳动力外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迁移者家庭的汇款①罗高斯等(Rozelle et al,1999)的研究发现,迁移对农作物产出的直接影响虽然是负向的,但这种负向影响一定程度上被迁移者给家中的汇款带来的家庭资金增加所抵消,每增加一元的汇款会使得每亩产出增加0.44斤。,提高了 “全部收入”即家庭与个人粮食获取能力,可实现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提出的粮食安全观②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1947、1974、1983年先后对粮食安全进行过界定和调查,提出粮食安全的目标是 “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主销区浙江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有1200万人,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36.11%(按当时中国政府制定的年人均收入200元的贫困标准计算),到2008年时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258元(远高于全国其他各省份),其中来自第二、三产业收入占80%以上。
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以主销区浙江为例来测算主销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假定以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则经济增长函数可表示为:


式 (1)中,G为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它是一个逆向指标,G的值越小,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越快。根据前面的分析,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比例的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向生产效率更高部门的重新配置,从而促进产出的增加,故可以预先假设G对Y增长的弹性系数γ为负值。式 (1)两边取对数后可改写成:

其中,C为方程估计的截距,Ui为统计误差,α、β、γ分别是K、L、G的增长对Y增长的估计弹性。样本期为2001年浙江粮食率先市场化改革实施至今,即2000-2008年且以2000年为基期。Y、L、G的数据来自 《浙江统计年鉴 (2009)》,Y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为亿元,L、G的单位分别是万人、%,资本K是一个存量概念。回归结果如下表1所示。

表1 模型 (2)的估计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见,模型 (2)拟合良好,G的系数符合预期,即G对Y增长的系数表现为负值,表示农村劳动力外流不仅对经济增长有贡献,而且对总产出的影响比技术进步和资本的作用更明显 (资本和劳动的系数为正值)。
2008年,浙江农村居民在本地企业中从业或外出从事各种劳务以及在非企业组织中从业得到的工资性收入人均为4713元,与2000年的2001元相比增长了一倍多,年均递增16.9%。工资性收入增加额已占全部收入增加额的62.4%,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村劳动力从比较效益低的第一产业转移到比较效益高的第二、三产业,直接促进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外出或转移的劳动力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带回的资金为加大农业投入、促进本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保障。目前,浙江省农村每个劳动力的承包耕地规模只有0.077公顷左右,投入效果和劳动效益很难再度提高。可见,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出去,才能提高浙江农村农民土地经营的规模和效益;只有增加农民收入,反哺农业发展,才能确保粮食安全。
四、基本结论
主销区实行粮食市场化后,农民的理性选择是粮食生产还是非农就业,主要是以收益最大化来决定的。计量结果表明,耕地稀少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经济增长和粮食获得能力的增加做出了贡献。主销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只要预期的非农收入或外流后实际收入大于种粮实际收入,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因此,需要着手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从低附加值、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生产转向高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非粮生产;加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把耕地转包给种养能手和扩大规模种植;加速土地合理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效益。在农业生产率持续提高后,实现费和拉尼斯 (Fei H.&Rains G.,1964)在刘易斯模式基础的 “粮食短缺点”向 “商业化点”的过渡和重合。在此过程中,尤其要防止对耕地的劣耕弃耕甚至非农使用等现象。主销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产生的福利损失,可以从粮食主产区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得以消除,并提高社会的总福利。
[1][美]D.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Lewis 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May,1954.
[3]Fei J.C.H.and Rains G.Development of Labor Surplus Economy[M].Homewood:Irwin,1964.
[4]Schultz 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5]Harris J.and Todaro M.P.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Two-sectors Analysi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60,No.11,1970,pp.116-142.
[6]Jorgenson D.W.Surplus Agriculture Lab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M].Oxford Economic Papers,19(3),1967,pp.288-312.
[7]Roselle S.,Taylor J.E.and De Brauw A.Migration,Remittanc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China[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89),pp.287-291.
[8][日]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著,沈金虎,周应恒等译.农业经济论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9]Williamson Jeffrey G.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M].Chapter 11,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8,Vo1.1,eds.H.
[11]姚先国.中国劳动力市场演化与政府行为[J].公共管理学报,2007,(3):13-21.
[12]林毅夫.入世与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4,(1).
[13]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14]赖存理.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浙江为例的分析 [J].浙江学刊,2000,(5).
[15]白南生.制度因素造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J].比较,2008,(35).
[16]马九杰,张传宗.中国粮食储备规模模拟优化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2002,(9).
[17]王雅鹏.粮食安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18]朱镜德.中国农业非剩余劳动力转移决策机制及其对农业的影响[J].南方人口,2003,(2).
[19]周异,胡靖.广东农村的劳动力流动、补贴与农地流转[J].南方农村,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