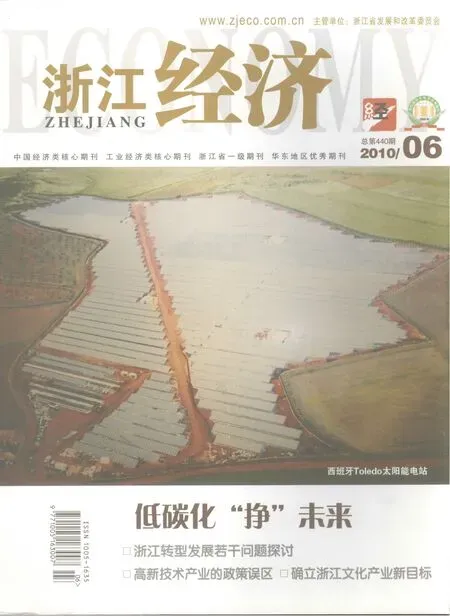宏观经济政策因时而动
文/邓聿文
“两会”已经结束。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今年经济工作的主线是如何在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无疑涉及怎样处理去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对此,从温总理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相关表述中,可以窥视到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简言之,就是因时而动,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
之所以强调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会是因时而动,动静不失其时,原因当然在于今年经济形势的复杂性。正如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所指出的,从外部经济体来看,虽然世界经济出现整体复苏的趋势,但一些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暴露,大宗商品和主要货币的汇率不稳定,由于通胀的预期而使一些国家在政策的选择上产生困扰,这些都有可能使经济复苏的形势出现反复,甚至二次探底。
从中国内部的经济局势来看,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虽然出现了企稳回升,但许多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主要靠政策在支撑。二是去年实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剧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本已存在的扭曲和失衡。三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在导致楼市和股市等资产价格飞涨的同时,也引致通胀预期。不久前公布的2月CPI涨幅达到2.7%,尽管这有春节的因素,但它离3%这一多数学者公认的通胀指数非常接近,可以说通胀预期已经很明显地摆在国人面前。四是还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问题还在于,上述四个方面并不是单个发生作用,而是相互支撑强化;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也互相传递。这无疑为政策的抉择增加了许多难度。如果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握不好,有可能使经济回升向好的形势发生震荡,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在短暂恢复甚至两位数飙升后再次下滑。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保持适当的谨慎和灵活。

复苏的经济形势要求我们在处理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保持适当的谨慎和灵活
上述诸关系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即如何来认识结构调整的问题和通胀预期的问题。对中国来说,结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中国的结构问题不只是产业结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贫富差异等在内的总体性结构问题。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不仅仅指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调整其实就是发展方式的再造。这一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当然,由于在过去发展中形成的利益刚性,要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这要求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必须和长期的调整结构相结合,否则,僵硬的退出将导致中国经济再次放缓前进的脚步。
同样,通胀预期问题也决不能轻视。如何管理好通胀,一般是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的主要难题。本轮通胀预期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具有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特点。如果放任通胀预期强化,社会公众将据此调整经济行为,迟早会变成现实的通胀。而从经济史来看,历次危机之后大都经历资产被稀释、物价上涨的阶段。尤其在中国,通胀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通胀处理不好,足以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温总理才会说,这是一个让他非常感到担心的问题。
有鉴于此,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即货币政策要保持货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和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时要管好通胀预期;高度重视农业,千方百计使农业有一个好收成;保持宏观政策的连性和稳定性,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和效果。这三个方面清晰地勾画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即因时而动,时进则进,时退则退,动静不失其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保证了国家政策的可预期性。至于具体的政策动静时点把握,则是一个技术判断的问题。当然,为了判断准确,需要我们随时观察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