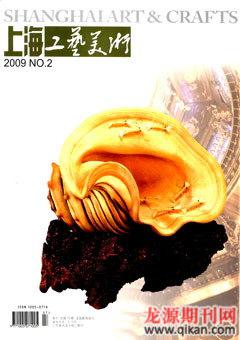湖田古窑畔成长的“世纪娃”
斯 文
传统是一种社会仪式,是对集体精神的认同,同样也是艺术家对于这种社会仪式的认同。中国的艺术精神总是联系着本土的根基和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中国的艺术家也不由自主地将这种对于根基的情感灌注于作品中。中国的绘画如此,雕塑如此,作为具有工艺魅力的陶瓷艺术更是如此,姚永康老师的陶瓷雕塑带着对传统精神的感悟和对现代雕塑语言的反叛,用具有传统魅力的湖田窑影青釉抒发着一位艺术家沉淀的心灵,瓷土在他的手下被赋予了中国式娃娃的生命,泥性得到了张扬,生出了一个个形态百异可以称之为“艺术丑”的并且带有着灵动诗意的陶瓷雕塑——“世纪娃”。
如果仅仅说是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这种观念来诠释“世纪娃”的精神魅力,那还远远不够。用姚永康老师自己的话来讲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着西方艺术思潮创新的精神,以一种不脱离本土的情怀在创作”。诚然,这种中国人的思维与本土的情怀正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但是这种继承并没有一味地去模仿前人,而是将民间艺术的灵动与自由带到了现代艺术思潮中,为日趋西化的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或者说是本土的土壤上,带着叛逆的气息与姚老师的陶瓷雕塑融在了一起。也许是创作者的灵魂与泥土一拍即合,“世纪娃”的灵魂被泥性的自由所释放,抛开“世纪娃”陶瓷雕塑本身所带有的工艺性,就现代陶艺本身而言,“世纪娃”带着中国传统精神的根基,成为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本土语言。中国许多现代陶艺的创作者在外来艺术的冲击中玩味着一种观念,或是对现实的一种叛逆与嘲讽,但是这种观念往往却丧失了对传统的继承或者说是本土精神的回归、以及中国式的语言与情感符号。“世纪娃”的语言游走在对现代西方艺术思潮的叛逆与对中国绝对的传统精神的反叛之间,这种对本土精神的传承与对雕塑传统的反叛,脱离了固有的造型,进行了一次打破常规的重组,是矛盾的结合体还是作者心态自然的流露,这种扎根于中国传统雕塑而又叛逆于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作品,这种吸收了西方艺术思潮而又反叛于西方艺术思潮的精神都在“世纪娃”中得到了体现,这种体现是复杂的,蕴藏在泥土具像的形式与抽象的精神表现之中。姚永康老师在用泥土追求一种心灵的真实,一种叛逆性的真实。这种叛逆是精神的叛逆,意象表现的叛逆与对现实和理想对立之间的叛逆,这样的叛逆精神超越理智,打破逻辑与现实的限制,任情感的指使,把现实世界的事理情态看成了他手中的泥土,任其搬弄糅合,造成了一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意象世界。
在与姚永康老师的谈话中,姚老师多次强调“人各有体”的概念,“世纪娃”成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带有中国绘画意韵的风格,包含着姚老师对中国绘画元素的吸收,中国青铜器时期与汉代雕塑风格的吸收以及对湖田古窑沉淀的民间艺术的吸收,这些吸收经过人生磨砺的积累和岁月的痕迹,形成了姚老师雕塑艺术的“诗意之体”。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凡是艺术家都须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固然不能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灵性,手腕则可得于模仿。”不仅仅是“世纪娃”身上诗意性的叛逆,包括姚老师早期的作品《自喻》、《母柱》以及其他带有中国本土情感的人体雕塑,这种“放荡形骸”的泥性或者诗意性的雕塑之美在观者与作者之间发出了共鸣。泥性的灵动蕴藏着对沃土的眷恋,恰如他自名为“土人”,在作品中永远追求着一种回归自然的气息,泥土在他的手中被赋予了生命,他将自己的灵魂与精神附注于泥土之中,在窑火的煅烧中得到了蜕变,让诗意与工艺得到了统一,让人眷恋,让人感动。
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的缺陷的,不知道“世纪娃”代表了一个创作者沉淀与孤独的灵魂,还是一个艺术家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冲动,也许是两者之间的交织罢!景德镇的湖田古窑在时间的洗礼中继续沉淀着它特有的历史,姚永康老师在东西文化艺术相互碰撞的浪潮中继续宁静地摆弄着他手中的泥土,依然扎根在他内心深厚的本土土壤,依然保持着他的叛逆之心,他的心灵已经与泥土合为一体,在中国的雕塑与陶艺界中形成了姚式的语言与境界,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德国文学家歌德,将他的文学立足于本国的传统;列宾的油画,将他祖国的风景真实地再现给了世界“本土性的中国语言,叛逆的思维精神”在姚老师的艺术中凝固,本土的就是世界的,但愿“世纪娃”带着中国的情感,姚式的语言在世界性的雕塑或现代陶艺中成为一种永恒的符号,让西方了解东方的现代艺术,让东方的现代艺术回归自然,回归本土。就像朱光潜先生在《星光》中说:“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随着星光一起找寻或去照耀和过去一样漆黑的未来。